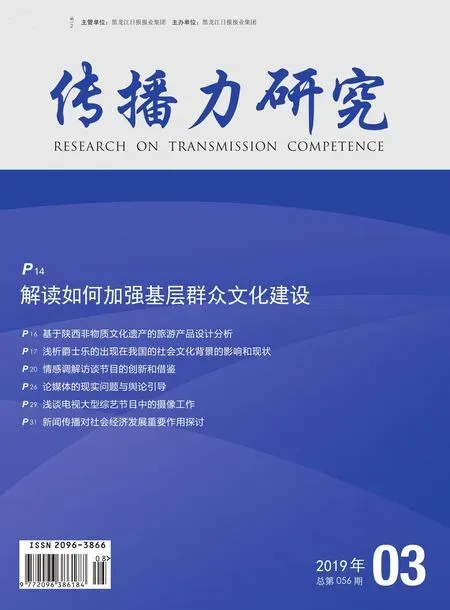所有付出終將不被辜負
——駐外工作經驗總結和交流
徐群 新華社參考消息報社
2005-2006年,我被派駐阿富汗喀布爾分社擔任一年的文字記者,后期也兼職攝影工作,是新華社常駐喀布爾分社的第一名女記者,也是中國常駐喀布爾的第一名女記者。在阿富汗常駐的13 個月的時間里,我走遍了除了最南部坎大哈和赫爾曼德省之外所有的省份,采訪過總統,也走訪過偏遠地區的罌粟種植家庭;去過無數次爆炸現場,也參加過只有女生才能參與的婚禮女賓部的慶祝活動;報道了阿富汗第一屆議會投票選舉,也報道過他的國民運動會等活動……
生活在安定祥和的當下回憶這些過往,有點恍若隔世的感覺,但看到照片又能感受到當初的點滴細節。想起當時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困難、危險和收獲,雖然很難用語言形容,但仍忍不住用筆記下來,勉勵自己無論生活在哪里,條件如何,都要不忘初心。
阿富汗國土面積約65 萬平方公里,人口大概3000 萬,國民文盲率超過70%。經濟支柱是農牧業,耕地不到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0%,而占GDP 大約三分之一的是罌粟種植和鴉片貿易。阿富汗是個純內陸國家,無出海口,連年戰爭造成國家積貧積弱,物資匱乏,大量依賴外援、農業以及和周邊國家的貿易。
苦:
自然條件之苦:
記得我當初從飛機上往下看,打量這個我除了北京以外第一個要長期生活的地方時,第一感覺就是荒涼,已進入5月的首都喀布爾從上空幾乎看不到綠色,建筑也寥寥無幾,有的只是大片的黃土地。進入到這個城市里,更是讓我不禁涌起一股悲涼之情,黃沙漫天、基建破敗,腦海當中閃現的詞語就是“悲催”。
在經歷了1979年蘇聯入侵,以及2001年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發動的所謂反恐戰爭之后,阿富汗備受折磨,元氣大傷,從當年一個美麗如畫的國家淪為千瘡百孔、百廢待興之地。2018年根據聯合國貿發會的報告,阿富汗,也門、孟加拉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又窮又破是阿富汗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阿富汗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一點沒比自然條件優越,大部分房子都千瘡百孔,電力極度短缺,家家戶戶都用發電機供電,分社的小院子里就有一個巨大的發電機。夏天由于雨水相對充沛,市政供電還能保證一半時間,一到雨水不足的其他季節,就必須時時依靠發電機。每天工作時發出轟隆隆的響聲,幾乎成了我努力工作的鞭策曲。
連年戰爭造成阿富汗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大部分人都掙扎在貧困線以下。作為“有錢的”外國人,我們還能狠下心來買菜吃,但比國內高出數倍的菜價還是讓人心疼。至于女生都愛的逛街,在阿富汗就徹底成了空白選項,因為根本沒商場可逛,偶爾有一個半個也都是賣當地的長袍。所以在那里一年的時間,對繁華已經沒了概念,頭腦中只剩下素淡。
百廢待興的阿富汗,人們的溫飽都成問題,娛樂活動就更是幾乎為零。生活的地方就是分社的房子和巴掌大的小院子,出于安全考慮,分社規定出門能坐車就坐車,不能隨意在馬路上走,每天的日子都是兩點一線。在那段時間里我才發現能自由自在地在路上行走也成了一種奢侈,我曾經對生活在一個如此局促的地方會不會讓人抑郁產生懷疑,但是所幸阿富汗可寫的新聞太多了,醒著的時間全用來寫稿子也寫不完,所以減少了我放松下來之后無聊的胡思亂想的機會。
工作不便之苦:
身為一名戰地記者,出門采訪禁忌頗多,首先安全毫無保障,塔利班發動的爆炸襲擊隨時發生,從最開始的路邊炸彈到后來的人彈,發生的不分時間和地點。以至于到后來,哪天不發生爆炸,我們都會覺得格外清凈。連我們去聯合國超市或北約超市進行采購,路上都會讓司機格外小心,因為去超市的路上經常也會發生針對北約士兵的爆炸。
但既然已經去了,就不能天天當“坐家”,所以我盡量保證不缺席任何一場重要的新聞發布會,也盡量每周都安排專題采訪,但這樣就要時刻做好準備面臨外國部隊的檢查,美軍和北約士兵在重要路口和場所都會設卡檢查。碰到友善者只要拿出證件就可以,不友善的就只能乖乖下車,等著士兵把汽車里外翻個通通透透,再加上一通盤問,才能放行。
由于當地嚴格信奉伊斯蘭教,對女性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出門在外必須長袍加身,而且必須有家人陪同。我作為一個外國人,雖信仰不同,但習俗必須遵守。最初到達那里,我按照使館的朋友和一些“前輩”的指點,都是長衣長褲出行,但發現這還遠遠不夠,當地人仍然會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你。后來才發現,只有長頭巾才是出門標配,而且外衣需要足夠長,不用及踝,但需及膝。
而約見采訪對象也是有利有弊,政府官員還算“見多不怪”,但去地方采訪遇到一些比較傳統保守的地方“大佬”,連握手禮都會被拒絕,要想采訪更是難如登天。在和雇員商議之后,我曾經有一次披上當地的長袍,只留眼睛在外面進行了一次艱難的采訪,取得了寶貴的采訪資料。有利也有弊,就是我身為女性,在采訪女性方面則是有了男性無法企及的便利。
樂:
工作繁忙無極限:
凡是有過駐外工作經歷的同事應該都有一個感覺,那就是駐外工作無極限。國外工作的強度之大,內容之繁瑣,實在是國內無法想象的。雖然出國前就聽“前輩”說起,但是真到了國外,才發現辛苦程度比自己想的還要嚴重。
每天都有寫不完的稿子,上午是聯合國、美軍、北約軍隊等各個國際機構的發布會,中午回分社寫稿子,下午要安排各種采訪活動,或者抓緊時間寫分析類的稿件,有重大事件發生就要隨時去參加突然宣布的某個通氣會,期間經常被雇員得到的爆炸信息打亂,到時就不得不扔下手里的活,趕緊奔到爆炸現場去。爆炸現場的血腥不言而喻,有些場景讓我好幾天都睡不好覺,那種慘烈一方面令我深感不適和難過,同時更讓我體會到了和平的不易,安寧的珍貴,和在遠方的祖國能平靜快樂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在阿富汗的一年里,我先后采訪過上至國家領導,下至自焚女性,見識到了以前從未見識,也幾乎沒想到會見識到的事物。我抓住機會采訪了很多很有特點的當地女性,既有第一名女機長、也有女子學校的學生,還有自焚女性的家屬,采寫的報道刊出后收到熱烈反響,轉載率也非常高,多篇稿件獲得社級優秀作品,并獲得北京市女記協的嘉獎。
2005年10月,巴基斯坦發生里氏7.8 級強震,造成3.9 萬人死亡,6.5 萬人受傷,330 萬人無家可歸。震中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山區,震時連喀布爾都有明顯震感,分社的房子搖晃的厲害。當時我們作為鄰居分社,被要求臨時趕往災區和亞太總分社的人一起支援報道,我毫不猶豫地主動請纓飛赴伊斯蘭堡。到達巴基斯坦震區,我們迅速投入緊張的工作中,到震區、醫院、簡易房等各個地方采訪、拍照,并及時發回來自震區的第一手材料,后續的救援和醫治工作我們也一直跟進,毫不松懈。此次報道工作組織及時、行動迅速、報道充分,不僅向全世界介紹了巴基斯坦大地震的情況,也從一方面起到了協助當地政府迅速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慰問和援助的效果。
增長見識會友人:
我在阿富汗時,美軍和北約部隊還有大量人員駐扎在當地,阿富汗大街上隨處可見外國軍車和士兵;此外,大批聯合國機構和人員也都在阿富汗設立常駐機構;因為新聞熱點眾多,當地也吸引了各國派駐記者;阿富汗物資奇缺,百廢待興,各國基建公司也紛紛參與援助項目;此外,也不乏一些私人開店的各國老板。可以說,匯聚在阿富汗的人無所不包,而我也因各種機緣巧合見識到了形形色色的外國人。
由于采訪的原因,我也有機會了解到外國駐軍的樣子。以北約維和部隊為例,他們在喀布爾和其他重要城市都有軍事基地,基地外很遠就開始嚴防死守,有混凝土建筑和沙袋堆成的軍事防御,越往里開路線越曲折。到了基地周圍更是防御措施充分,高企的圍墻,遍布的鐵絲網,以及各種防御工事,遠遠看著就有種不寒而栗的感覺。即便如此,仍能不時發生塔利班對外國軍隊及軍營的爆炸事件,確實感覺戰亂之國,無處安定。
軍營內的生活非常枯燥而且對外保密,士兵們每天面對的都是無休止的訓練和外出巡視任務。但是士兵們也偶爾會有“不插電”時間,周末晚上會不定期的舉行party,比如在巨大的營房里舉行舞會,可以喝酒可以跳舞,神經一直緊繃的士兵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放松一下。那些平時在軍車里全副武裝,不茍言笑的士兵在此時才露出本色,他們有的聚在一起低語,有的肆意狂歡,盡情揮灑著自己對家人的思念或者是對枯燥生活的無奈。
“同是天涯淪落人”,由于身處一個戰亂危險的國家,在其中的所有外國人都顯得格外親近。媒體人之間都會互相幫忙,得到一些活動通知都會相互轉告,偶爾有時沒辦法參加也會從同行那里拿到活動資料或者新聞稿之類的。而其他一些工作沒有交集的外國公司的人則會在娛樂生活方面,想方設法讓生活過的充實。
雖然生活在“素淡的”阿富汗,但世界各國的到訪者們也都挖空心思、各出奇招,為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比如分社附近曾經有一家土耳其建筑公司,這個公司的老板讓我對外國人自娛自樂的精神充滿了無限欽佩。他的房子也有一塊巴掌大點的院子,他竟然在周末時間把他認識的各國友人請到他家,把不大的院子弄成一個足球場,舉行2 對2 的超小型足球賽,其他人就坐在旁邊一邊給場上的隊員助威加油,一邊品嘗他的廚師烹制的土耳其小點心。看到那個場景,你絕對可以忘記自己身處阿富汗,那里帶來的快樂和心靈上的安慰是在正常情況下無法體會的。
總的來說,駐外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正是這份辛苦,讓我發現自己的無窮潛力;采訪中遇到的艱難和危險,讓我體會到記者這份工作的辛苦和神圣;采訪中見到的痛苦和無奈,讓我為生長于繁榮穩定的中國感到無比慶幸和自豪。和這樣的收獲相比,那些辛苦又顯得尤為值得。當年因為條件所限,通訊和技術都不發達,無論報道還是留資都遠不像今天這般輕松,如今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報道形式的豐富早已超越以往,正是我們所有人擼起袖子加油干的好時機。何不爭分奪秒、努力創新,相信所有付出終將不被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