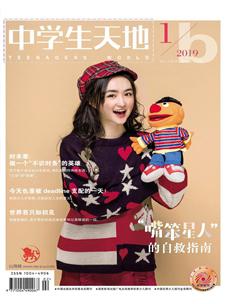今天也是被deadline支配的一天!
白雪 馮姝
編者按:
在瞬息萬變、信息爆炸的時代里,值得公眾追逐的除了新鮮的話題和事件,還有它背后所蘊含的真知。培根說:“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善于思考的人,才能在這個社會辨明真相,少走彎路。
2019 年,“思想實驗室”正式開啟,郁喆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一位集專業深度與大眾普及于一身的“哲學小王子”將帶領我們一起化解困惑,學會深度思考,建立更成熟的認知體系。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給自己打個氣。今天又是被deadline 支配的一天!”大到考試周、學期末,小到每周末、各種活動前,打開朋友圈,總能看到一片“哀嚎”。時間變成了“看得見的死神”,每個人似乎都在被一個接一個的deadline 追趕。截止日期成為“第一生產力”,卻也令人漸漸喪失了享受過程的能力。
你是否想過,到底什么才是deadline?時間不會停止,可為什么我們現在被迫活在deadline 里,時間究竟應該去享受還是去追趕?如果沒有deadline,生活會怎樣?deadline可以折射出對時間的哪些理解和誤解呢?不如讓我們一起來聊聊deadline 這件事。
你最討厭的deadline 是什么?
沈卓文:當然是作業、考試的deadline!如果要說一個終極的,那最討厭的deadline 肯定是死亡。
王一凡:最討厭的是父母到家時間。父母到家前,我必須要把所有東西都整理好。“兒子,今天晚上我5點到家”,結果他們4點就到了。我得連忙把手機塞到床墊里,假裝沒用過。
陳鵬之:我最討厭的是“假死線”,就是過了之后不會“死”可還是要趕的死線。本來假期趕作業就趕得“頭禿”了,書法社暑假還要求交四、五幅作品。更可氣的是,寫好之后,社長并不看,還說:“你居然寫了?”
黨伊萱:我認為deadline 是“完成任務的最后期限”,怎么對待deadline就看你怎么安排時間。
郁教授:從大家的討論中可以看出,deadline不是時間本身,而是我們每個人對時間的理解和設定。絕大多數讓人感到討厭的deadline來自外界,最擔心的就是總活在別人安排的deadline里,自己逐漸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了。別人給你的時間設了一道坎,讓你感到疲憊、痛苦。有很多時候,我們希望dealine徹底消失,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但是沒有deadline的生活會是怎么樣,你想象過嗎?
如果沒有deadline,你會干什么?
戚鑫杰:我喜歡慢慢做事情,如果沒有deadline,我會更享受每個環節,會把一件事做得更好。如果考試沒有死線的話,我會把每道題認認真真做一遍,考出更好的成績。
王昊天:如果沒有deadline,就沒有目標倒逼了。我會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比如學習,不必想著要在幾年后達成什么目標,就慢慢學,學習只是為了讓自己高興。學習一整天,就快樂一整天。
吳晶:沒有deadline 的設定想都不敢想。我們習慣了每天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deadline 一旦消失,我會完全不知道現在該去做什么。
張凱:康德說,我們每一個行為都有一個目標和一個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沒有deadline,就缺少一個有明確時間的目標;沒有目標,行為就會靜止,也就不會有手段。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為了deadline而活著。如果人的生命是無限的,那就無所謂了。
章浩然:其實deadline也可以叫lifeline。失去了它,沒有了需要即時去做的事情,人就會變得萎靡不振,對吧?最后就感覺人生失去了意義。
郁教授:其實deadline讓我們意識到一個悖論,我們每個人總是希望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使用盡可能多的時間,但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間是不可能無限多的。反過來,雖然很多人都追求永生,但是永生會使得人陷入無限的無聊。一個人時間的總和就是生命,也就是一輩子。因此,lifeline 是一個很好的說法,那么,你的人生有終極目標了嗎?
沒有人給你定deadline時,你會為自己設一個嗎?
王一凡:有啊,其實還挺多的,比如周六上完課,我會先定個小目標,用一個小時把卷子做完,然后放松一下聽聽歌。可一打開手機,半小時就過去了。
陳鵬之:我會告訴自己周日下午4點前一定要把數學作業寫完,然后到晚上就可以看大家趕作業,會很爽!但是仔細一想,這樣自己寫的答案就會被大家看到……半個班的希望將寄托在我身上。
高昕彤:我只會設很遠的deadline,比如在幾年之內達成XX 目標。我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因為來自別的地方的壓力已經很大了,最近的deadline就是考上大學。我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的deadline 是嫁給明星王鶴棣,這個算嗎?哈哈。
吳晶:如果說一件事情到了要給自己設定deadline的地步的話,那這件事情肯定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很多情況下給自己定deadline,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的效率。到最后肯定是完不成的,但是對效率的提升還是有用的。
郁教授:效率是deadline 之母。現代人都不自覺地認為,提高效率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也就是想在單位時間里,盡可能多地產出,例如多做幾道題目,多生產一些商品。但是,我們要反過來想,難道沒有別的什么比效率更重要的事情嗎?例如個人內心的安寧,以及和家人、世界的和諧關系。
你有沒有經歷過“物我兩忘”的時刻,特別專注地做一件事情時,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自己?
周靖哲:踢球。獨自找一片球場踢球,踢之前先給自己定個目標,比如要踢一個很棒的弧線球。然后就開始不停地練,一直踢三四個小時。
陳鵬之:練書法的時候。當我對這個字有感情的時候,就可以很順地寫下去,和平時的狀態很不一樣。但這種狀態很容易被打斷,比如老師說你寫得很好,有個比賽去參加一下,然后deadline就來了。
王昊天:我覺得deadline 讓人覺得不舒服是因為這個deadline 是別人定的,實際上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其實這個時候只要不去依賴別人就好了。所以這次期中考,我打算不花大量時間去背歷史政治,就想著反正考幾分都無所謂,成績只是給老師看的,直接無視會比較輕松。
郎朗子:大家都聽過西西弗的故事,他必然存在于苦役之中,但他可以賦予苦役更高的意義去超越它。這也是我對這個題目的看法,我們必然存在于時間之中,但我們可以超越它。所以我覺得存在deadline 和享受時間并不矛盾。它既然已經存在了,那我們就要去享受它。
郁教授:踢球、練書法和練琴都是很難得的“沉浸”體驗。那一刻,做一件事情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為了它的結果,也就是拉丁語諺語“把握當下”(carpe diem)的含義。“享受deadline”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如何享受卻是難題。當你的心緒不是放在當下,總是想著一件事的前因或者后果,可能會非常煩躁。大概只有當把一件事情當作“目的本身”,才能真正沉浸其中,找到安寧。
跨越“死線”,尋找“心流”
Deadline是時間中的一道坎,有時候過得去,有時候過不去。那什么是時間呢?如果你問一個普通人,他會指一個時鐘給你看,說鐘表就是時間;如果你問一位物理學家,他會告訴你,時間和空間都起源于宇宙大爆炸(The Big Bang)。哲學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里說,我們都覺得時間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但是一旦問起,卻反而模糊起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時間的度量和時間并不是一件事情。鐘表是用來度量時間的。即便世界上所有的鐘表都沒有了,時間依然還在流逝。另外,對時間的感受也不同于時間本身。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在《創造進化論》中提出,用鐘表度量的時間是“空間時間”,而我們每個人體驗到的時間是“心理時間”,即“綿延”。綿延的每一段都是不同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在陷入回憶,或者聆聽音樂的時候,就能很好地體驗到這種綿延。相反,空間時間的每一段都是相同的,而且是可以被分割的。這就是deadline讓我們感到不舒服的根本原因———我們天然地喜歡綿延,而討厭空間時間。古代人更多地活在綿延當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現代人因為工業化和分工協作的關系不得不活在空間時間當中。綿延的時間如同不停頓的流水,而deadline 像抽刀斷水。很多人專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能夠體驗到一種“物我兩忘”的狀態,也就是心理學上說的“心流”———雖然可能很短暫,但這是一種對deadline的超越。
即便沒有了別人設定的deadline,我們每個人卻最終面臨一個終極的deadline,即自己的死亡。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點,才會要么醉生夢死,要么過于執迷于一些瑣碎的事情,到頭來發現自己虛度一生。時間也是人生意義的來源。
20 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就說,人是“向死而生”。他說,如果沒有了死亡這個大限,人生就是沒有意義的。恰恰是因為有死亡,我們才會知道去籌劃自己的生活,并賦予它意義。假設你可以長生不老,你會干什么呢?有人說,我要去環球旅行,我要學習100 種語言,我要嘗遍世界美食……做這些事情需要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十年、幾十年,至多幾百年都可以完成了。然后呢?人會陷入重復或者無聊。西西弗就是這樣一個隱喻———他推球上山,然后滾落,以此重復不止。這樣的永生有意思嗎?
恰因為人生有限,才能談論人生的意義。所以,不能簡單地說要惜時如金。只有在明了了自己人生的意義,設定了自己的終極目標之后,惜時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會變成另外一種“守財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