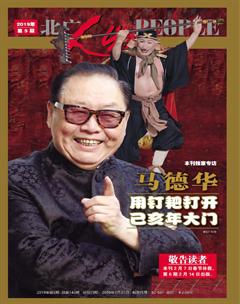鬃人傳人白大成:人生何似“盤中戲”(上)
夯石(張琳)
最早知道鬃人,自然是從冰心先生的那篇散文:“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后扎著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鬃子。這些戲裝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個個鬃人都旋轉(zhuǎn)起來,刀來傖往,煞是好看。”冰心這篇《我到了北京》中特意提到的這種鬃人表演,到今天也只有白大成一家還在傳承著。
白大成的家在一個街口的把角,儼然一個地標,又仿佛一座戲曲和民宿博物館。多年前的一個上午,白老指點著柜中的一件件藏品,眼中閃爍著靈動的光。凡是有戲曲人物形象和故事圖案的,白大成都收藏。自然,這與鬃人“業(yè)務(wù)”分不開。白大成的鬃人藝術(shù)既從各類藏品中汲取養(yǎng)分,又能反哺傳統(tǒng)民俗文化。屋里一溜兒排開的木柜里擺滿了風(fēng)格各異的面人、泥人、皮影、兔爺、臉譜以及繪有戲曲圖案的備類瓷器……當(dāng)然,白老最為珍視的還是他在不同時期親手制作的數(shù)十款鬃人。
白老說:“我一輩子靠手藝吃飯,沒正經(jīng)上過班。”其實這里的苦并非常人能想象。傳承似乎要付出某種特殊的代價,甚至要做好某種特殊的準備。
癡迷“盤中戲”
白大成,1939年生于北京,滿族,1979年,白大成參加在中國美術(shù)館舉辦的“首屆全國工藝美術(shù)展”。1991年其作品參加在中國美術(shù)館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藝術(shù)節(jié)”。1992年作品參加在民族文化宮舉辦的“首屆全國民間藝術(shù)精品展”。1994年在大觀園舉辦個人作品及戲曲藝術(shù)收藏展。1996年、l997年連續(xù)兩年應(yīng)邀參加以色列耶路撒冷手工藝博覽會。1997年應(yīng)邀赴法國五城市展覽訪問。1999年在新東安市場創(chuàng)辦“老北京一條街”,組織民間藝人表演及經(jīng)營民間藝術(shù)品。2004年被北京市西城區(qū)文委掛牌“家庭藝術(shù)館”。
我第一次去白大成家采訪恰是在西城區(qū)文委掛牌之后。白老驕傲地說:我這是政府特批的,也算是個旅游點兒。
白大成說自己還是趕上了好時候。過去他想的是把鬃人這門手藝保護好、傳下去,同時能夠養(yǎng)家糊口,“出口創(chuàng)匯的活兒我干多了,畫過扇面,山水一毛五到兩毛,人物兩毛到三毛。鬃人,老外很喜歡,迷上就不能自拔。”后來他明白這是文化,于是也自覺地向文化靠攏。“在過去,都知道鬃人,這銅盤也沒什么特殊,老北京人家里頭,甭管窮富,都有。把上面的茶壺茶碗拿走,就可以把鬃人擺上去敲著玩,會唱的還能跟著唱上一出,‘盤中戲的別稱就是打這兒來的。”
史料記載:北京的鬃人手工藝品,是受皮影和京劇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具有濃郁的民間色彩,已有1oo多年的歷史,創(chuàng)始人是清末時期的北京老藝人王春佩。他的鬃人作品曾在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銀質(zhì)獎?wù)隆W兹耸⑿杏谇迥┟癯酰?dāng)時,護國寺、隆福寺、白塔寺等廟會上常有表演、出售。普通鬃人高3寸左右,大的6寸有余,用泥做頭面,高梁稈、紙絹做身子,下端粘一圈幾毫米長的豬鬃,按京戲做成生、旦、凈、末、丑,擺于銅茶盤中,用木棒擊打銅盤,產(chǎn)生共振使小戲人在盤中轉(zhuǎn)動,模擬演戲效果。鬃人是昕有中國民間藝術(shù)品中唯一有動態(tài)的。泥人、面人、毛猴等屬于靜止欣賞的。鬃人既可以靜觀,又可以拿過來作玩具來玩。
拿小木槌“當(dāng)當(dāng)當(dāng)”一敲銅盤,盤中手持丈八蛇矛的張飛便抬著腳,朝緊握方天畫戟的呂布追打過去……為了讓鬃人活泛、靈動,白大成可謂煞費苦心。其實奧妙就在鬃人底下這一圈鬃毛,豬鬃彈性好,能支撐,敲打銅盤的時候,鬃毛會跟著振動,帶動鬃人轉(zhuǎn)動。傾斜方向不同,也就相應(yīng)有了對打、追擊的效果。白大成說其中最要緊的就是鬃毛必須排得密實均勻,角度也很有講究,大了小了都不行。轉(zhuǎn)起來要想保證不倒,還得把握好平衡,這就用到了我之前在航佼學(xué)過的力學(xué)知識。”敲敲打打中,文臣武將,古今鏡鑒,—起涌上心頭。人生要是“盤中戲”那可就好了,而往往我們卻是被命運操縱的“戲中人”。
從“鬃人王”到“鬃人白”
1959年,白大成因為身體緣故從航空工業(yè)學(xué)校休學(xué),在家養(yǎng)病期間,由街坊介紹認識了鬃人愛好者李老先生,“我從小受家里影響,喜歡京劇,國畫油畫書法都懂,手也比較巧。李老先生教我制作鬃人,前后大概一個多月。后來李老得了青光眼,做不了了,我又通過親戚介紹認識了李寸松先生,他在中國美術(shù)館工作,1955年為挖掘北京民間藝術(shù),曾找過‘鬃人王第二代傳人王漢青制作鬃人。就這樣我經(jīng)李寸松先生介紹認識了王漢青先生。經(jīng)常拜訪他,向他請教鬃人的制作方法,同時也就繼承了王氏鬃人的制作特點。以前的老藝人賣這些玩意都是在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廟等廟會,但那會兒受戰(zhàn)爭影響,換不回錢來,王老先生就不做了,改行修理無線電收音機,以此為生。因此解放初期,鬃人的制作已經(jīng)‘后繼無人了。”
王漢青雖然靠修理無線電為生,但也將自己零星制作的鬃人擺出來賣,他的兒子去了西北……當(dāng)白大成提出想跟他學(xué)做鬃人時,王漢青打心底里高興,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絕活悉數(shù)相教,這一場師徒之緣等于把鬃人從瀕臨失傳的懸崖邊兒給生拉了回來。上世紀60年代初,白大成還給市政府寫了封信,申請鬃人的營業(yè)執(zhí)照,最終在王府井的美術(shù)服務(wù)部白大成有了自己的柜臺。
可好景不長,“文革”開始后,白大成的手藝成了“四舊”,營業(yè)執(zhí)照被收回,家里剩下的鬃人也只能毀掉。為了養(yǎng)家糊口,白大成在工地上搬過磚、和過泥,跟著老師傅學(xué)了木工活,還到廠子里做臨時工,后來又去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地質(zhì)博物館和北京科學(xué)教育電影制片廠從事制景工作……
改革開放后,白大成的鬃人制作很快獲得新生。從他參與籌備的地壇廟會開始,工藝精巧的白派鬃人成了國內(nèi)外游客的搶手貨,“鬃人白”的名號也逐漸傳開。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