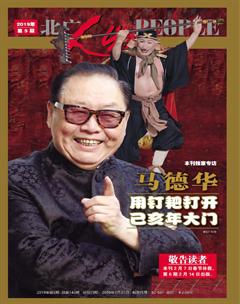年輕的老極地38歲的他八赴南北極
他去過1次南極、7次北極,是一位年輕的“老極地”。不久前剛結束的我國第九次北極科考中,他就在科考隊里擔任冰站隊隊長。
雷瑞波是我國第九次北極科學考察冰站隊隊長,也是自然資源部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最年輕的研究員。他去過1次南極、7次北極,發表的多篇論文,為我們揭示了極地潛藏的奧秘。
那次遭遇北極熊的經歷
“熊來了!熊來了!3只,10點鐘方向,快撤!”這是2018年的一次北極科考中,雷瑞波和同事遭遇的“熊來了”!
38歲的雷瑞波,是自然資源部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最年輕的研究員,也是歷次北極考察最年輕的首席科學家助理。他去過1次南極、7次北極,是一位年輕的“老極地”。不久前剛結束的我國第九次北極科考中,他就在科考隊里擔任冰站隊隊長。
“在廣袤的北極無人區,我們只是匆匆的客人,對極端惡劣的作業環境還知之甚少”膚色黝黑,說一口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聊起天來,記者得知,雷瑞波是南方人,成長于溫暖如春的廣東,卻選擇了與冰天雪地為伴。
說起那次遭遇北極熊的經歷,雷瑞波依然心與余悸。當時,雷瑞波等人剛到浮冰不久,就聽到對講機上傳來駕駛臺總指揮的呼叫。
雷瑞波感到大事不妙,因為并不是冰站上所有人都帶著對講機,他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組織全部隊員撤離,“北極熊在極度饑餓的情況下,是有可能攻擊人的,它在冰面跑起來的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50至60公里,人是跑不過的”。7人一組、女性和外國隊友先上,設備一件都不能攜帶——他立刻招呼冰上所有的作業點,保證每個人都明白所處境地的危險,命令所有隊員向吊籠上奔跑。整個撤離過程,用了不到10分鐘。
待北極熊離開夠遠后,冰站隊又以最快的速度將科考物資收拾回船。“這個過程也不到10分鐘。下冰后,誰都沒說話,基本靠默契配合。沒人知道熊什么時候會再回來,大家部是跑著完成了所有撤離。”雷瑞波說。
浮冰開裂是另一大威脅
帶領隊員進行冰站作業,觀測和研究海冰,是雷瑞波在科考中的主要工作。聊起海冰,雷瑞波似乎有說不完的話。盡管遭遇過北極熊、浮冰開裂等危險,在他眼里,那片危機四伏的冰天雪地仍然充滿誘惑。
冰站作業是什么概念?冰站作業期間,科考隊員需要離開“雪龍”號母船,在海冰表面開展冰基浮標布放、冰雪樣品采集以及冰面觀測等工作。
冰站考察成為北冰洋考察的主旋律,這也是我國北冰洋考察與其他大洋考察的最大區別。“南大洋考察現在也沒有冰站考察,因為南極的海冰和北極的不一樣,南極的海冰是一年冰,比較脆弱,不適合做冰站。而其他大洋沒有海冰。”雷瑞波說。 “2018年是我第七次去北極了。對于海冰的性質、科考環節心中部基本有數,但仍然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在廣袤的北極無人區,我們只是匆匆的客人,對極端惡劣的作業環境還知之甚少,我只能要求自己再多一點耐心和細心。”雷瑞波說。
浮冰開裂是另一大威脅。雷瑞波說,第九次北極考察中就遭遇過險情。當時,受風力拉伸和其他浮冰的碰觸,長期冰站所在的浮冰作業第三天就裂開了。考察隊認為人員完成必要工作后必須撤離。即使布放的設備受到裂縫潛在影響,也必須撤離。當冰縫裂開后,冰站隊冒著危險開展了一次實地觀察,發現布放的設備受影響不大,才將設備留下作為無人值守觀測峻備。
在極地開展冰站作業,最主要的工具是冰鉆。有些冰鉆的延長桿有正負之分,正負交替才能延長到適合的長度。有一次在北極,考察隊發現只帶了正向的連接桿,沒有帶負向的。“必須自己想辦法。”雷瑞波回憶,他們在船上自己開車床現改,把正向的螺紋打掉,鉆出負向的螺孔。船上的車床不像加工J‘那樣完善,花了足足一天的工夫才完成。
差點凍傷了兩根手指
雷瑞波是學港口工程專業出身,在大連理工大學讀博士期間,接觸到渤海海冰的工程學問題。后來因為導師承擔了極地的項目,他獲得了一次去南極的機會,“當時只是想去極地看一看,沒想到這一看就是15年”。
第一次去南極越冬,雷瑞波就待了長達14個月,日日和海冰為伴,“第一次去沒經驗,作為南方人,我看起來好像比北方人還扛凍,其實是因為從小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嚴寒,當時缺少防范意識,差點凍傷了兩根手指”。 極地的生活新鮮、充實,使他對海冰產生了極大興趣,他決定“改行”。2009年,他加入中國極地研究中心,主要從事極地海冰物理學觀測和科學研究。做海冰研究的科研人員少,每遇極地考察需要人手,專業素質過硬的雷瑞波總是積極地“頂”上去。
在雷瑞波看來,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極地人,責任心最要緊。“極地科考性質特殊,一點小問題可能釀成大禍。到了現場,科考隊員就是要靠責任感守好崗位,爭取把小事故化解成小故事。”長期冰站作業前,要把所有冰縫探明,并做上標志。任何潛在風險出現苗頭后,考察隊都會通過群體決策,給出能力范圍內的最佳處理方案。
雷瑞波的“拼”換來了工作上的累累碩果:獲得省部級科技獎2項,發表的論文先后4次被評為中國極地自然科學優秀論文。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極地海冰物理,圍繞北極海冰快速變化機制和表征,他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30多篇。邢大軍據《人民日報》劉詩瑤/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