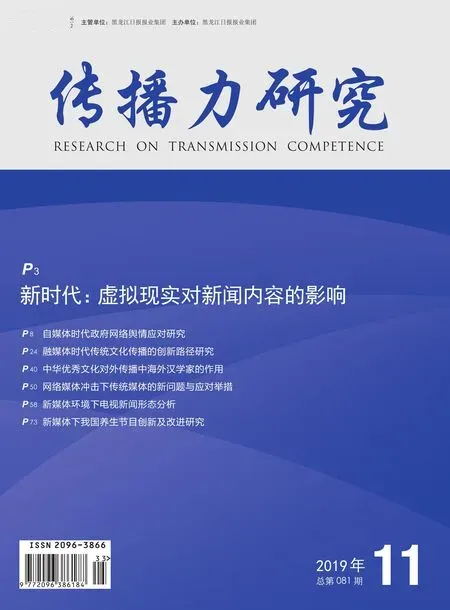淺談電視劇《白鹿原》的敘事策略
徐凱毓 李祎旻 西藏廣播影視制作中心
小說《白鹿原》裹扎著內涵深厚的鄉土文化史和精神史,再現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時代印記,對于民族心理的挖掘及民族精神的刻畫,久久耐人尋味,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為文學思潮激烈變革時期的代表作,成為了新歷史主義文學潮流中的佼佼者。由此翻拍而成的同名電視劇《白鹿原》一經上映,收視率一路走高,并在豆瓣評分中獲得了9.3 分的高分,對其敘事策略的探尋,是深挖其審美價值的關鍵。
一、時間重置
對時間的安置,是電視劇《白鹿原》敘事創新的關鍵一環,與小說有著明顯的區別。具體而言,在小說《白鹿原》中,敘事時間起于“白嘉軒十六歲”,終于“朱先生去世后的幾十年的七八年”,呈現出了鮮明的意識流色彩,插敘、倒敘及補敘等藝術處理手段的運用屢見不鮮。反觀電視劇《白鹿原》,故事的講述主要安排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之間,在紛亂的情節中整理出了一條時間軸,甚至鏈接到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各個重要環節,通過兩個不同時間節點的對比映射,堅定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信仰。除此之外,電視劇《白鹿原》在敘事時間速度的把控上亦值得深究,滲透于整部劇作演繹的始終,是衡量某個情節在整個故事講述中作用的關鍵標識。這部長達3465 分鐘的史詩大劇中,演繹著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編劇在高度尊重和還原小說的同時,亦將自己的個人體驗融入其中,將其歷史性、時代性以及審美性演繹的淋漓盡致。綜合來講,敘事時間速度作為一個相對概念,與敘事情節的疏密存在反比關系。對此,學者楊義指出,“文本的疏密度和時間速度所形成的敘事節奏,是著作者在實踐整體性之下,探究天人之道和古今之變的一種敘事謀略”。正是電視劇《白鹿原》對敘事時間速度的精準把控,使得觀眾深刻感受到了“激蕩百年歷史,鑄就白鹿精魂”的豪邁與激情。
二、空間安排
電視劇《白鹿原》演繹在鄉土中國農業文明的縮影下,片名即是點明了敘事空間,以土地為首要切入元素。土地是人們的生存之根本,更是孕育著生命的起源和文明的發展,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見證著中化民族的崛起。對于白鹿原的鄉黨們而言,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才是追求奮斗的根本,如此才能保證生命的延續。在整部劇作中,每個人都有著對土地的無限向往,黑娃期盼著靠著自己的勤勞掙下土地、石頭戒毒后的生活目標亦是贖回土地,正是因此牽動著這個毫無血緣關系的大氏族發展。同時,電視劇《白鹿原》亦因著土地而演繹著白、鹿兩家的世代爭斗。從更為深層次的角度上講,白鹿原上對土地的爭斗,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對人民的兩種價值取向,突出了我黨為民服務的宗旨。在具體的劇情演繹上,祠堂里熱鬧的分地場景與白嘉軒面對土地被分割時的沮喪形成了鮮明對比,正是基于土地的這層保障,使得中國共產黨迅速歸攏民心,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白鹿原表明看來“一片祥和”,實則暗中涌動,是儒家觀念與革命觀念的碰撞交融,這種以小見大的空間安排,觸發了人們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反思,倡導著誤傷的平等與自由,其中所表達的精神意蘊耐人尋味。
三、主題確立
電視劇《白鹿原》在敘事題材的選定上,以仁義、道德為基準,反射出了日常生活的審美追求。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傳承與發展中,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對仁義禮智信的宣導更是深入人心,并作為人們道德評判的重要標準,廣泛見于日常生活當中。對比電視劇和小說中的《白鹿原》,他們在價值追求上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化,在具體的敘事選擇上,電視劇《白鹿原》將仁義部分進行提煉和放大,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更加清晰、明朗。同時,客觀維度上分析,電視劇《白鹿原》亦存在一定的批判情節,在嚴格執行審查要求的基礎上,進行了相對淺顯的批判與探討,弘揚了傳統優良文化。在敘事策略的安排上,電視劇《白鹿原》之所以強化仁義及道德相關概念,其關鍵在于并非小說那樣的事實搬運工,其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是迎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流的必然選擇,是更符合電視劇受眾的審美需求。由此看來,電視劇《白鹿原》的主題利益更加鮮明,敘事結構相對簡單,大手筆突出了白嘉軒身上的仁義品質,削減了小說中的批判性成分,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回歸,更是對中華民族傳統優良文化的召喚,其所呈現出的主流價值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和認可,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
四、關系重構
國際知名學者塞米利安曾經說過,“不朽的小說作品的條件之一就是創造出令人難忘的新的人物形象。”從敘事藝術的處理上講,電視劇與小說之間存在很多的相似之處,其根本的價值在于描述、敘述。對故事中各個人物形象及關系的梳理,在很大程度上牽引著觀眾的情感演變,是電視劇制作中不容忽視的一環。因此,電視劇《白鹿原》對于人物關系的處理亦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其在竭力展現小說思想精髓的同時,做出了微調,甚至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人物情節,戲劇張力的表現更強。例如,小說中對于鹿子霖與白嘉軒之間的關系敘述并非明朗,他們既是發小又相互競爭,存在著一種對抗而又依存的復雜情感。而電視劇《白鹿原》從一開始就對這二人的關系進行了著重渲染,因白嘉軒“不戰而勝”的當選族長突出了他們之間的對立關系,較之小說來的更加直接。事實上,這種對抗性人物關系的重構,著重表現了電視劇《白鹿原》的敘事特色所在,大膽而不失真切的改編,牽動著觀眾的思緒,使之更為自然地融入到故事情節當中。某種意義上講,正是緣于電視劇《白鹿原》對人物關系的這種處理方式,使得整個敘事過程更加順暢,符合觀眾們的審美習慣,使之對整個故事情感脈絡的把握更為精準。
五、影像呈現
電視劇《白鹿原》對效果的改編,亦可視作是藝術再造的過程,通過文字向聲音、畫面的符號轉化,使得整個敘事過程更為形象、立體,帶給受眾差異化的感官刺激體驗,而這也正是影視藝術的魅力所在。單就文本本身而言,電視劇《白鹿原》足以稱作是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的重要參照文本,對其他影視制作有著重要的啟示借鑒價值。電視劇《白鹿原》對于聲音的處理,高度尊重真實生活,并盡最大努力進行了還原,各個角色之間的交流以對白為主,輔以秦腔等地方戲,將故事的發生背景環境演繹得淋漓盡致,突出了整部劇的風格樣式。在此過程中,臺詞對白均是帶有濃重陜西方言的口音,有著極強的地方文化代入感,將白鹿原生存的原生態環境塑造的惟肖惟妙,在這種聲音強調下傳達出的情感久久耐人尋味,所呈現出的獨特審美價值,吸引著人們對陜西文化的探尋與向往。知名導演路易·達指出,“視覺的力量才是整個電影情緒感染力以及說服力的首要選擇。”在敘事策略的選擇上,電視劇對畫面的導入與應用,是區別于小說更明顯的部分,對觀眾形成了強烈的視覺刺激,感受到了一種更為立體化的審美享受。同時,電視劇《白鹿原》對于部分生活場景的描述,進行了唯美化處理,代入了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審美體驗。
六、結語
綜上所述,電視劇《白鹿原》的敘事策略選擇,與小說的敘事藝術處理有著很多方面的差異,在時空安置、主題確立、人物關系等諸多方面均有體現,同時由于文本載體的不同,加之聲音、畫面的影像呈現,帶給了受眾更為深切的情感體驗,整部劇作的代入感、娛樂感有所增強,對其他影視劇的制作亦有重要借鑒意義。作者希望學術界大家廣泛參與此類課題研究,從不同維度視角分析電視劇《白鹿原》的敘事策略及特點,繼而推動我國影視藝術的發展,為人們的現代化精神文明生活增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