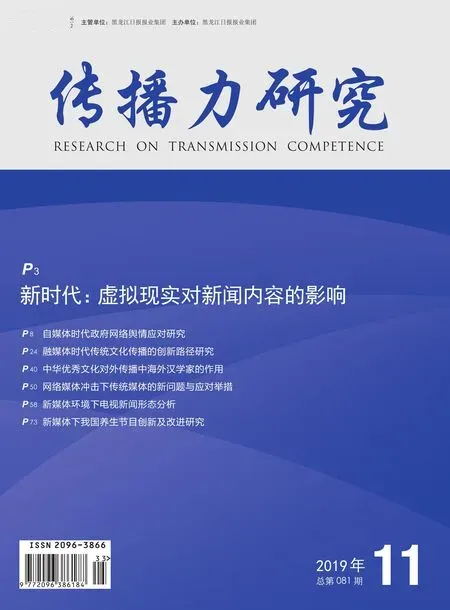談電影《城南舊事》敘事與倫理的互動
王飛翔 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
一、第一人稱自敘下的“倫理網線”的構建
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倫理和敘事兩個學科結合進行探討并不是兩者的簡單疊加,正如龔剛所說:“對道德寓言式的文學敘事的研究未必就是倫理——敘事的研究,只有將道德意圖和敘事方式結合起來考察才可視為倫理——敘事的研究。”[1]作者的敘事策略干預了倫理傾向,所以說作者是于其作品的道德立場進行直接對話,不同的敘述方式有著相對應的生命感知,在敘事于倫理的互動下方可捕捉作者的隱藏位置及立場。
《城南舊事》以英子為敘事視點進行擴散,在第一人稱自敘的敘事策略下去構建影像中的人物倫理場域,這種敘事者參與對話的形態與倫理秩序的構建相呼應。在影像作品中,敘事視角是看待世界的另一種視線與角度位置,當導演要構建一個敘事宏大虛擬世界的時候,必然不可能將世界的原封原貌搬運到銀幕媒介上,而是要去選擇性的藝術化處理,去體現導演的謀略及思想。
當“隱含作者”被我們捕捉到存在的印痕時,影像中敘述者的每一個行動都產生了符號化的含義。英子為圓點,建構起英子——父母的血親倫理,英子——瘋子秀珍、英子——小偷,英子——乳母宋媽,三個故事建立起交往倫理。在英子與周圍的他者發生倫理事件之際,作者的意圖便可延伸到英子的視角之中,實則表現的是作者對待周邊事物關于“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善”“何為正當”的考量。在其中可意會出:在20 世紀20年代家長父權制下女性角色普遍的、潛移默化的地位;在“小偷”身上可以影射出當下特殊的階級矛盾以及對與“正當”的評判標準;“乳母”的結局實則是導演通過敘事的謀略的“不穩定性”告訴觀眾女性身份的悲劇性的張揚。
二、綴合式團塊結構下的女性倫理問題
綴合式團塊結構是一種相對小眾的敘事結構,影像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不聯系,具有向心性,例如《小城之春》《城南舊事》皆是采用了這種敘事結構,通過一種貫穿機制能使影像折射出富有哲思、意象的文化內涵。不同模塊的組成即是自成一體的,又是統一完整的,具有“能動”的特性,如楊義所說:“結構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各部分之間不是機械式的可以任意拆卸和組對,而具有氣脈神韻灌注于其間,形成一個統一的生命體。”[2]敘事之結構問題一直是敘事學的結構部分的核心內容,中國古典小說順序講究“天人合一”,注重傳統的“道”與“技”的互動,而敘事學與電影學學科交叉之后,影像文本的結構也同樣抒發導演對于結構生命氣息的融合,富有哲思。
《城南舊事》三個自由的段落敘事,同時出現三個婦女形象——秀珍、宋媽、母親,從而展現出一系列的女性倫理問題。
在20 世紀初,女性形象刻有陰郁的“東方精神”,這是社會歷史根源的問題。英子在電影的第一段落中遇到了一個他者口中“瘋癲”形象的秀珍,她的丈夫被抓,而在以“宗祠為重”的傳統思想作用下,女兒被丟棄在天橋下,至今不見蹤影,“嫁夫從夫,夫死從子”,而子被棄,只能接受“貧而無依,老而無告”的悲劇性命運,從而使人物瘋癲,所以說秀珍的“瘋子”形象是傳統倫理的糟粕方制造的,英子不受勸阻,以孩童的人物形象,帶有個體自由意志與秀珍成為“朋友”,幫助秀珍找到女兒,然而秀珍的身份已經失去了社會結構的倫理位置,所以結局伴隨著女性個性自由的消解而引發悲劇。
乳母宋媽的倫理行為是貫穿著整部影片的,其悲劇性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完全闡釋了“以宗祠為重”的血親倫理的“偽道德律令”,花甲之年寄人籬下只為遙遠故鄉的子嗣生存問題,往來僅僅依托書信,故事末端才揭示子嗣已然不在的現實,傳統社會的家族本位的倫理范式通過宋媽“婦德”彰顯出來,生活在中心來自遙遠已經不存在的子嗣,幸福亦然來源于此,這種幸福是建立在喪失了女性自由與選擇權的泥沼中,所以人物的悲劇性直接的顯現出傳統社會女性的倫理地位,根深蒂固的宗祠思維被侍奉為神明,女性個體實則是身體與貞潔的操控對象。
敘事結構的順序、連接與對比對影像內容的精神層面的傳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敘事結構將人物的位置及行動的方向確定下來之后,各個組合段進行連接,使得結構的各個部分不再僵化和機械,避免成為一盤散沙,又能將內容縫合成為具有積極活躍的生命體態。
三、結語
《城南舊事》以英子的視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去感受周邊人與物的分離,分離的背后卻是隱含著豐富的倫理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歷史的厚重感帶來的壓迫,另一方面則是敘事作為工具而謀劃出的手段,所以敘事與倫理是親近的,正如《城南舊事》這種“散文詩”類的電影在表述相思和哀愁的同時,也在緩慢述說著生命細線般的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