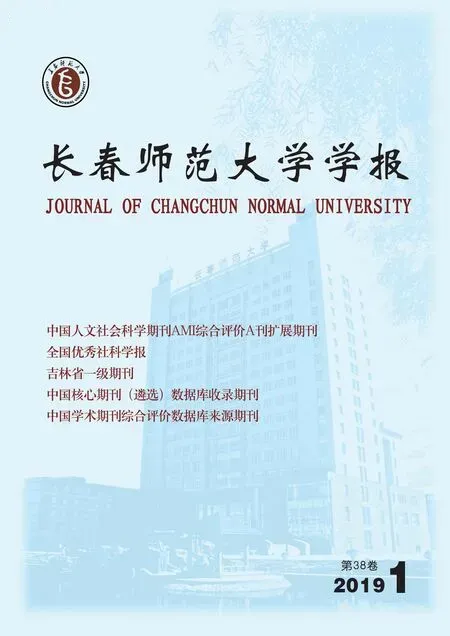從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舉選賢
田子爽
(西安財經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
制舉是唐代科舉中一種特殊的選才形式。“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1]唐代制舉效仿漢代察舉,皇帝多在重大事件發生之際開設制舉,親自下詔選拔賢良人才,以表達樂善求賢之意。改元是指新君即位或在位期間改換年號。對封建王朝的發展命運而言,改元是至關重要的大事,意味著一個新的局面即將開啟,會被載入王朝的歷史檔案之中。而新君即位、改換年號,在昭告天下改朝換代的同時,可能會使政治局面出現動蕩不穩的情況。因而即位改元,不僅對新君而言,還是對封建王朝的政權穩固而言,都是關鍵時刻,不容有絲毫的閃失。新君通過制舉選賢的形式來與天下對話,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賢納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廣納賢才、勵精圖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統治,從而確保統治權力的平穩過渡。此時的制舉,不僅僅是一種選拔賢良的途徑,其在穩定時局、安撫民心上產生的政治功用更為凸顯。本文以唐朝皇帝即位改元為切入點,來考察唐代的制舉選賢。從相關文獻記載來看,從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即位登基之時開設制舉,從中可見唐代制舉選賢的重要政治意義。
一、初盛唐時期即位改元的制舉選賢
初盛唐時期一般指唐朝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通過梳理《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等相關制舉詔令可以發現,初盛唐時期有五位皇帝在即位改元之際開設制舉。最早見于唐太宗即位之時,下《即位赦》,其中有云:“高年碩學,直言正諫,所在長官,隨狀薦舉。”[2]6唐太宗非常重視符合“高年碩學,直言正諫”標準的賢良,因而下詔要求地方長官薦舉此類人才。這里的“薦舉”,非嚴格意義上的成熟制舉,但符合廣義制舉的范疇,即“所有常選之外與‘天子’關系較為密切的舉人活動”。[3]唐太宗在即位詔中親自選拔賢良的做法被不少唐朝皇帝所效仿。
貞觀十九年(645)二月,李治以太子的身份監國,下《監國求賢令》,其中的選賢標準是:“其有理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任輕;或孝弟力田,素行高于州里;或鴻筆麗藻,美譽陳于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為時新。如斯之倫,并堪經務,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蓽,深為可嘆。所在官僚,精加訪采,庶使垂綸必察,操筑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送。”[4]3078此時的李治并未真正即位,但在代理朝政之初選拔賢良不失為一種昭告天下新主即將執政的巧妙之舉。當時州郡所舉薦的人才有數百人之多,可見李治的監國得到了天下的認可。貞觀二十三年(649)九月,李治正式即位,是為唐高宗,又下《令京司長官上都督府諸州舉人詔》,其中有云:“有司詢訪,宜以名聞,有一于此,當超不次: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嚴才,堪膺教胄者;志節高妙,識用清通,博聞疆正,終堪卿輔者;游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事,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然不移者。京司長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4]757此時制舉的人才類型如德行、才能、文學已經有明顯的區分,選拔的標準開始明晰化和具體化。傅璇琮先生認為:“唐代初期高祖、太宗兩朝,制舉科是從沿襲傳統到衍變為有唐代設科取士特色的發展時期,到高宗初,就與進士、明經科一樣,成為科舉的一部分。”[5]
之后,或因宮廷變故,制舉選才的類型較為簡單。如神龍元年(705)唐中宗即位,二月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4]759唐睿宗唐隆元年(710)六月即位,下詔令內外職事官五品以上舉薦賢良,沒有明確的人才標準。唐玄宗于先天元年(712)即位,十二月下制曰:“將帥之任,軍國斯重,御侮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筮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舉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敭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予懷。”[4]761玄宗結束了唐王朝多年宮廷內亂的局面,初步穩定了大唐政權,但仍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因而更加重視人才的實用性。
由上可見,隨著唐太宗在即位改元之際下詔選拔賢良,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在掌握政權時堅持制舉選賢,使即位改元時的制舉選賢成為新君昭告天下的一個重要方式。
二、中晚唐時期即位改元的制舉選賢
以安史之亂爆發為分水嶺,唐王朝進入中晚唐,期間有八位皇帝在即位改元之際進行了制舉選賢。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今河北涿州)起兵謀反,唐朝王室倉皇外逃。期間,唐肅宗于至德元年(756)七月在甘肅靈武即位,下《即位赦》,其中有云:“其有直言極諫,才堪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委所在長官聞薦,詣闕自陳者亦聽。”[2]8盡管處于戰禍之中,唐肅宗仍堅持制舉選賢,實為彰顯皇權,告慰、安撫天下蒼生,亦是對謀反者的警告。
安史之亂平息后,即位改元的制舉選賢繼續進行。唐代宗于寶應元年(762)四月即位,下《即位赦》,其中有云:“其有明于政理,博綜典墳,文可經邦,謀能制勝,及孝悌力田,諸州刺史并宜搜揚聞薦。投匭者不須勘以停處姓名,務招直言,以副朕意。”[2]9
唐德宗于大歷十四年(779)即位,六月下詔:“天下有才業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其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4]766
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唐德宗崩,唐順宗即位于太極殿,二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開設制舉:“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于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于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恭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以名聞,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實,如無人論薦者,即任自詣闕庭。”[2]10順宗于同年八月傳位于太子,是為憲宗,改元永貞,當年并未舉行制舉,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四月,憲宗開制舉。
唐穆宗于元和十五年(820)即位,十一月下制:“如有隱于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具名薦聞。”[4]767長慶元年(821)正月辛丑,唐穆宗郊禋禮畢,下《南郊改元赦》,改元和十六年為長慶元年,并開制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2]393十月,穆宗下詔,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準制舉薦賢良方正人等。穆宗將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宣政殿進行策試。
唐敬宗于長慶四年(824)即位,三月下《即位大赦冊》,其中有云:“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人師,詳閑吏理達于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4]768寶歷元年(825)正月,唐敬宗下《南郊赦》,恩而大宥,大赦天下,改長慶五年為寶歷元年,開制舉:“澄清教化,莫尚乎太學;明治心術,必本乎六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奏,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知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役。”[2]393三月辛未,唐敬宗在宣政殿策試制舉人,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李虞仲任考制策官。
唐文宗于寶歷三年(827)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827)正月下《改元太和赦》,其中有云:“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并限來年正月到上都。”[2]30太和二年三月辛巳,唐文宗在宣政殿親自策試制舉人。
除晚唐的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外,中晚唐的皇帝大都在即位之時或即位改元之時開設制舉。偶有例外,也有特殊原因。如唐憲宗即位之時,尚有唐順宗所征制舉人尚未策試,因此于元和元年四月,唐憲宗以前朝制舉、不敢冒犯先帝為由,下令宰臣在尚書省監試制舉人。此外,中晚唐即位開設制舉的頻率要高于初盛唐。唐王朝有289年的歷史,以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安史之亂前的初盛唐時期,共137年,期間有五位皇帝于即位時開設制舉;安史之亂后的中晚唐,有152年,有八位皇帝在即位時開設制舉。可見,中晚唐新帝即位要比初盛唐頻繁,相應的制舉選賢的次數也多,但也暴露出皇位更替頻繁,皇權統治力的逐漸衰弱。
三、即位改元制舉的選賢意義
首先,從帝王即位選賢可以看出唐代制舉存在與發展的基本軌跡。唐高宗武德五年(622)三月,下詔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薦一人,若有志向品行高潔的懷才不遇之士,也可以自薦。清人徐松在《登科記考》卷一中認為,這是唐代制舉的開始標志[6]。一直到唐文宗開成年間,皇帝即位改元這樣重大時刻都會進行制舉選賢,在位期間每逢國家重大場合,也多以制舉選拔賢良,使得制舉延續下去。但自唐武宗會昌元年(841)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唐王朝結束前的這六十余年里,制舉的記載極少,以至于學術界普遍認為唐代制舉在唐文宗太和年間結束。其實,這期間也有制舉的少量記載。如唐武宗會昌四年(844)九月下《平潞州德音》,還搜訪文學節行、隱跡山林的能人異士;唐懿宗于咸通七年(866)年,下詔對宗族中有行義、文學、史事的人才,要量才敘用。這些都體現出唐王朝仍期待通過制舉選賢,鼓勵有才能的官員來協助治理日漸頹衰的政權。
其次,即位改元制舉詔令中的求賢意識、君臣共治的期待呈現出愈發強烈的趨勢。整個唐王朝的制舉選賢詔令中不乏對賢良的渴求,在制舉選賢的程序和禮儀上都以詔書的形式下發,禮賢下士,以表達對賢良的重視。初盛唐時期的制舉詔令更多地流露出對賢良的重視,而中晚唐時期的制舉詔令在重視賢良的同時,流露出與賢良共治的期待。如唐憲宗即位時,面臨唐順宗朝遺留下的制舉,在《元和元年尚書省試制科舉人敕》中云:“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萬邦之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盛烈,覲十圣之耿光,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洪鐘待扣,膺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光,宜有廷試,本將詢事,豈忘臨軒。園邑有期,營奉是切,永言誠感,未暇躬親。爰命公相,洎于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于興化之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開予,靡有所隱,條例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朕將親覽,擇善而行。并宜坐食訖就試。”[2]544憲宗首先以謙遜的口吻,表達自己初登皇位的惶恐,因而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的放松。此時的唐王朝在經受安史之亂后,出現了嚴峻的社會問題,如農民流離失所、名目眾多的賦稅等等。因此,憲宗希望借助賢才的治世能力,恢復太平盛世,因而要求制舉人的對策能夠圍繞“興化之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暢所欲言。這體現了憲宗意欲重振儒家學說、以儒治國的執政謀略。為了能夠得到制舉人的治國對策,憲宗會親自閱覽制舉人的文章,期望得到治國之良方,以便及時采納。總之,憲宗借先王的制舉選賢,以大段的言辭流露出君臣同心、勵精圖治、恢復大唐盛世的渴望。之后的唐穆宗、唐敬宗皆在即位之時以制舉選賢表達出共同的心聲。
第三,制舉人才的類型與具體標準更加明晰,實用性愈來愈強。初盛唐的皇帝即位時,制舉詔令中的人才類型多是品行類、學識類,這從制舉科目的名稱上即能看出。如唐高宗在選賢時,主要選拔具備淵博學識、品行純良、文筆超拔的文臣儒士。唐玄宗時期,開始強調人才的實際工作能力,“務求實用”。孝悌類科目在初盛唐是比較熱門的科目,頗能體現唐王朝以孝悌求忠臣的人才理念,甚至在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的即位詔中連續出現。安史之亂之際,唐肅宗設置孝悌類科目,希望以孝悌的人倫道德來移風易俗,達到穩定時局的目的。但隨著多種社會問題的日益突出,孝悌類科目逐漸失去了道德品行的自我約束和道德教化功能,社會政治功用明顯弱化。唐德宗之后,此類科目逐漸銷聲匿跡。約從唐順宗開始,大都是諸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的類型,是唐代制舉的“定科”。其中的“直言極諫”“達于教化”“可以理人”等后綴,對賢良的實際治世才干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因而,即位改元制舉詔令中的人才類型的演變體現出唐王朝從文治向吏治的轉變軌跡。
四、結語
唐朝皇帝在即位之時進行制舉選賢,對五代時期的皇帝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不少皇帝紛紛在即位之際進行制舉選賢,如晉高祖在天福元年(936)十一月即位,下《即位赦》:“弓旌聘士,巖穴征賢,式光振鷺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萊、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搜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敘用。”[4]769晉出帝在天福七年(942)六月即位,七月下《即位大赦制》:“山林逸士,草澤逸賢,將裨教化之風,且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逸丘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4]770周太祖在廣順元年(951)正月即位,下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加搜訪,免致遺賢。”[4]770周世宗于顯德元年(954)丙申即位,三月下即位赦制,曰:“應有懷才抱器,出眾超群,或養素于衡門,或屈跡于末位,孤寒難進,志業可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干略,灼然可稱者,所在具以名聞。”[4]770-771上述詔書中的人才類型是相似的,即山野之中懷才不遇的隱逸之士、出類拔萃卻不被重視的官場中人。五代時期政權更迭更加頻繁,新君急需政權的穩固與社會的安定。唐王朝的制舉承載著穩定政權、安撫民心的政治功用,且確實為國家選拔出大量經世致用的賢良。五代的新君同樣有此期待,希望在初登大寶之際,憑借制舉促使眾多懷才不遇的賢良積極應詔,實現君臣共治、天下太平的理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