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詞匯翻譯初探
——以魯迅短篇小說《社戲》的英譯為例
丁 惠,郭利瑩
(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民俗是民間流行的風(fēng)尚、習(xí)俗的簡(jiǎn)稱。民俗文化也可稱為民間文化,是一個(gè)國(guó)家的人民群眾或特定的社會(huì)群體在長(zhǎng)期歷史生活和生產(chǎn)實(shí)踐中創(chuàng)造、共享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時(shí)代性、地域性與穩(wěn)定性等特點(diǎn),受時(shí)間與空間的影響。在民俗文化的成型和綿延過程中,產(chǎn)生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詞匯,它們形象地描繪了豐富的民族風(fēng)俗景象,反映了人們?cè)谌粘I罴皠趧?dòng)中的偉大智慧,更是傳統(tǒng)民俗文化在語(yǔ)言當(dāng)中的詳細(xì)體現(xiàn)。對(duì)這類詞匯的翻譯重點(diǎn)在如何成功將其移植進(jìn)譯文里,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汁原味”的原文文化色彩。
一、文化差異對(duì)民俗文化詞匯翻譯的影響
由于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有著自身顯著的特點(diǎn),在對(duì)外宣傳與推廣的過程中最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民俗文化詞匯的翻譯。我國(guó)與西方國(guó)家在語(yǔ)言表達(dá)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詞匯上的缺位。民俗文化翻譯中的詞匯缺位現(xiàn)象一般指在漢語(yǔ)中能夠通過單獨(dú)詞匯詳細(xì)標(biāo)注的東西,譯為英語(yǔ)時(shí)卻需要添加解釋,也就是說英語(yǔ)中找不到現(xiàn)成的對(duì)應(yīng)詞語(yǔ)[1]。例如,“香火”、“風(fēng)水”、“文房四寶”、“天人合一”等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的詞匯。但東西方也有許多相似的民俗文化內(nèi)容,像在美國(guó)民俗文化中,人們會(huì)在新婚夫婦結(jié)婚當(dāng)天向新人身上撒許多大米,以此來預(yù)祝他們?cè)缟F子,這與我國(guó)在婚床上鋪滿大棗和花生的習(xí)俗極為相似,同樣都是多子多福、生育子女的涵義。因此,在傳播民俗文化時(shí),可突出中西方相似的民俗文化的特征促進(jìn)雙方的交流與溝通。
此外,在民俗文化詞匯中蘊(yùn)藏著許多民俗意象,這同樣是翻譯過程中的難點(diǎn)之一。漢語(yǔ)善于運(yùn)用簡(jiǎn)單精煉的詞匯表達(dá)豐富的情感與內(nèi)涵,民俗詞匯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樣的特征。特別是許多諧音詞匯的表達(dá),在翻譯成英文后往往無(wú)法傳達(dá)出原本的真實(shí)含義。比如,我國(guó)皖南地區(qū)的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已經(jīng)習(xí)慣了在廳堂的長(zhǎng)桌兩側(cè)擺放復(fù)古的瓷器花瓶與鏡子,這叫作“東瓶西鏡”,寓意“東平西靜”,希望家里能夠和諧、平靜、安穩(wěn)。這樣的民俗文化詞匯含義已經(jīng)超出了原本的表層意義。而這種情況就需要翻譯人員事先細(xì)致、深入地了解原文本的文化背景及詞匯內(nèi)涵,并結(jié)合當(dāng)?shù)仫L(fēng)俗民情,以適當(dāng)?shù)姆g方法找到英語(yǔ)中與其含義相符的詞匯,避免出現(xiàn)語(yǔ)義偏離或缺失的現(xiàn)象、對(duì)廣大讀者的理解造成負(fù)面影響,真正發(fā)揮出翻譯的文化傳遞作用。
二、楊譯本《社戲》中的部分民俗文化詞匯英譯分析
作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奠基者,魯迅在自己的文學(xué)作品中真實(shí)而詳細(xì)地描寫了中國(guó)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文化面貌。他的短篇小說《社戲》是一篇反映鄉(xiāng)俗文化與人情的佳作。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了“我”20年來看戲的三次經(jīng)歷:兩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戲,一次是少年時(shí)在浙江紹興鄉(xiāng)下看社戲。其中,“我”在少年時(shí)代看社戲的經(jīng)歷是著墨的重點(diǎn)。作者借助一系列特有文化詞匯飽含深情地刻畫了一群機(jī)智、活潑、淳樸的農(nóng)家少年形象,歌頌了勞動(dòng)人民善良、友愛、無(wú)私的美好品德,表達(dá)了“我”對(duì)農(nóng)家朋友誠(chéng)摯情誼的眷念,特別是對(duì)少年時(shí)期生活的感懷。在小說中,魯迅先生既對(duì)民俗事件及文化進(jìn)行了詳細(xì)生動(dòng)的刻畫,也對(duì)鄉(xiāng)野人情做了直觀的情感渲染,因此,小說體現(xiàn)了通俗自然的口語(yǔ)文體特征,有許多形式短小、內(nèi)容淺顯的詞匯。這部小說有楊憲益與戴乃迭兩位翻譯大家的譯本(簡(jiǎn)稱楊譯本),是“魯迅小說英譯的權(quán)威版本,在國(guó)內(nèi)外流傳廣泛”[2]。楊譯本格外注意保留我國(guó)傳統(tǒng)民俗文化的意蘊(yùn),同時(shí)也很重視文化的有效傳遞與原著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重現(xiàn)與對(duì)等,在國(guó)內(nèi)外讀者中接受度較高,極大程度地促進(jìn)了魯迅小說在英語(yǔ)世界的譯介與傳播。下面就從特有文化詞匯的翻譯與原作語(yǔ)言風(fēng)格的傳遞兩個(gè)角度,對(duì)民俗文化詞匯翻譯問題展開初步的探討。
(一)特有文化詞匯的翻譯
《社戲》中追憶在鄉(xiāng)下與農(nóng)家少年朋友一起看戲的前后情形時(shí),寫到“社戲”、“神棚”、“小旦”、“老生”、“老旦”等專有名詞與戲曲角色,充滿了鄉(xiāng)土風(fēng)情與文化特色。對(duì)這些中國(guó)特有的民俗文化詞匯,主要采用了文化空白保留法來更好地保留原文本中顯著的民間風(fēng)俗文化特征。
當(dāng)源語(yǔ)中某些詞語(yǔ)在目的語(yǔ)中沒有意義對(duì)等的詞匯時(shí),源語(yǔ)中的信息無(wú)法完全移植進(jìn)目的語(yǔ),這種現(xiàn)象被翻譯家索羅金稱為文化空白。在《社戲》中,有許多民俗意象均具有特殊的文化內(nèi)涵。例如,浙江“社戲”這項(xiàng)民俗活動(dòng)。浙江向來?yè)碛小拔幕睢钡氖⒚瑲v史悠久,文化昌盛[3]。在浙東農(nóng)村,社是一種區(qū)域名稱,代表土地神或土地廟,社戲就是社中每年所演的“年規(guī)戲”,它表達(dá)的是人們對(duì)土地的敬重。最初,社戲是在春秋兩季祭祀土地神的習(xí)俗。春社祈求豐收,秋社慶賀豐收,后成為以演戲酬神祈福,進(jìn)而發(fā)展為民間文化娛樂活動(dòng)。“社戲”本身是一個(gè)文化負(fù)載詞。楊譯本將標(biāo)題《社戲》處理為“Village Opera”,突出這個(gè)活動(dòng)發(fā)生的地域和場(chǎng)所,并未指明其背后的敬神祈福意義,僅在文中出現(xiàn)過“village sacrifice”。在《柯林斯詞典》中,“sacrifice”作名詞時(shí)有一個(gè)意思:“the act of offering sth. to a god, especially an animal that has been killed in a special way”,即“祭獻(xiàn);祭祀”,隱約透露出這種鄉(xiāng)村文化活動(dòng)與祭祀神靈有關(guān)。相應(yīng)地,社戲戲臺(tái)對(duì)面的神棚也只處理為“shrine”。《社戲》中的神棚是供神名牌位的涼棚,演社戲時(shí)搭在戲臺(tái)正對(duì)面,有請(qǐng)神靈看戲之意。“shrine”一詞在《柯林斯詞典》中,與中文“神棚”最接近的釋義是:“a place of worship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holy person or object”,即“圣地;圣祠;神廟;神龕”。可以說,僅就供奉神明的場(chǎng)地而言,“shrine”是“神棚”的上義詞,它的內(nèi)涵要比“神棚”大得多。在不參考注解的情況下,那些不熟諳中國(guó)文化的外國(guó)讀者恐怕很難從“shrine”一詞準(zhǔn)確理解原著“神棚”的含義[4]。但楊譯本并未對(duì)神棚的功能作額外的注釋說明,而是原封不動(dòng)地保留了這個(gè)文化元素即文化空白,恐怕更多地是出于引起西方讀者對(duì)中國(guó)民俗文化好奇之意,使目的語(yǔ)文化的讀者自己去查探鄉(xiāng)村娛樂活動(dòng)中出現(xiàn)奉神場(chǎng)所的深層文化原因。
再如,看戲時(shí)出現(xiàn)的我國(guó)傳統(tǒng)戲曲中的基本角色與人物,有“小旦”、“花旦”、“老生”、“老旦”等,由演員按照不同年齡和性格的角色進(jìn)行裝扮,他們的出場(chǎng)方式也有著特定的規(guī)則,這是我國(guó)傳統(tǒng)戲曲獨(dú)特的舞臺(tái)表現(xiàn)方式。西方的戲劇角色大致分為男主角(hero)、女主角(heroine)與其他的配角(supporting roles)。楊譯本將《社戲》中的戲曲角色簡(jiǎn)單翻譯為:小旦——girl,heroine,花旦——the heroine’s maid,老生——old man,老旦——old woman,除此外并未對(duì)角色的性格特點(diǎn)、臺(tái)詞與舞臺(tái)表演特征多作解釋,但西方讀者自然也看得明白這種依照年齡劃分的角色譯法。楊譯本對(duì)文化空白的保留有一些接近異化的處理方法,即“尊重差異,盡量保留源語(yǔ)異質(zhì)語(yǔ)言文化特色。”[5]
(二)原作語(yǔ)言風(fēng)格的傳遞
“文藝作品的風(fēng)格,應(yīng)該是指一個(gè)作家所有作品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主要的思想和藝術(shù)特點(diǎn)的總和……
而形成作品風(fēng)格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作家驅(qū)遣文字、運(yùn)用語(yǔ)言的獨(dú)特手法。這種手法跟人走路的步法、寫字的筆法一樣,各有特點(diǎn)。但它總是依賴于語(yǔ)言的一般規(guī)律而存在,決不是不可捉摸的。”[6]就小說《社戲》的語(yǔ)言風(fēng)格而言,其與魯迅的大部分作品風(fēng)格迥異。魯迅一直對(duì)黑暗的舊社會(huì)與專制制度抱有強(qiáng)烈的憎惡態(tài)度與反抗精神,他多以辛辣、諷刺、犀利的小說語(yǔ)言對(duì)人吃人的制度進(jìn)行強(qiáng)烈的抨擊。但《社戲》這部作品不同,它一面展開對(duì)故鄉(xiāng)的美好回憶,一面充滿了對(duì)故土與鄉(xiāng)間人情的懷戀,因而,小說語(yǔ)言風(fēng)格簡(jiǎn)潔、活潑、生動(dòng)、有趣。對(duì)文中出現(xiàn)的大量口語(yǔ)常用語(yǔ),如“寫包票”、“有見識(shí)”、“中狀元”等,楊譯本以意譯的方法分別進(jìn)行了處理。“打包票”出現(xiàn)了三次,兩次是“我”的朋友雙喜向“我”的外祖母與母親保證能夠?qū)ⅰ拔摇逼桨矌タ磻虿⑵桨矌Щ兀瑮钭g本第一次以“I give my word it’ll be all right!”[7]來翻譯,意為“我保證會(huì)沒事的”,這是一個(gè)許諾,語(yǔ)出自一個(gè)十幾歲的少年之口,顯出農(nóng)家少年聰明機(jī)靈的個(gè)性,也比較符合其敢想敢做的年齡階段特點(diǎn)。第二次出現(xiàn)“打包票”是一行人在戲后將“我”送回時(shí),看到早已等在橋頭的“我”的母親,雙喜說出“都回來了!那里會(huì)錯(cuò)。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這樣的話,楊譯本這里用一個(gè)反問句:“Didn’t I guarantee it would be all right!”[7],既呼應(yīng)了之前的保證“沒事”,又譯出了少年完成承諾后的如釋重負(fù)和令大人刮目相看的得意之情。第三次“打包票”與“有見識(shí)”、“中狀元”兩個(gè)詞語(yǔ)一起出現(xiàn)在看戲后的“偷豆”余波中。歸家途中,少年們因饑餓難忍而偷吃了六一公公田里的豆子,被主人發(fā)現(xiàn),前來質(zhì)詢。因“我”是客人,六一公公又將吃豆認(rèn)作待客,并從“我”口中得悉了對(duì)豆子口味的肯定,進(jìn)而夸“我”:“小小年紀(jì)便有見識(shí),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狀元及第”、“光耀門楣”是中國(guó)古代個(gè)人及家族莫大的榮耀。在以血緣和宗族關(guān)系維系人際關(guān)系的傳統(tǒng)中國(guó)鄉(xiāng)村,這里是一個(gè)“熟悉”的社會(huì),沒有陌生人的社會(huì)[8],因?yàn)楹洗宥际峭毡炯? “我”母親是從這里嫁出去的姑娘,“我”自然也是這里的孩子。一個(gè)鄉(xiāng)間長(zhǎng)輩,對(duì)晚輩的“我”下了“有見識(shí)”、將來“中狀元”這樣的評(píng)語(yǔ),這是一種樸素的贊美,也充滿了樸素的鄉(xiāng)情與溫暖的人情。楊譯本將“有見識(shí)”翻譯為習(xí)語(yǔ)“he knows what’s what”[7],即“什么都知道”,“中狀元”意譯為“come first in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7],即“在官方考試中考第一”,“福氣打包票”譯為“Your fortune’s as good as made”[7],即“福氣簡(jiǎn)直是定下來了”,突出了福氣“fortune”,比較符合鄉(xiāng)民口語(yǔ)特點(diǎn)和六一公公的身份。
三、結(jié)語(yǔ)
楊憲益與戴乃迭兩位先生畢生堅(jiān)持翻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及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幾乎“翻譯了整個(gè)中國(guó)”。本文僅列舉了《社戲》中民俗文化詞匯的部分英譯方法。通過以上英譯的分析可得知,楊憲益與戴乃迭兩位先生在翻譯中秉持的理念是忠實(shí)地傳遞民俗文化。因此,從所采用的翻譯方法來看,楊譯本更加重視譯文的“忠誠(chéng)”,強(qiáng)調(diào)要始終遵循原文,努力將我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民俗文化的原貌最大限度地還原出來,這與魯迅所提出的翻譯應(yīng)保留原著作風(fēng)格的標(biāo)準(zhǔn)如出一轍。對(duì)此,在翻譯民俗文化詞匯時(shí),譯者應(yīng)在充分了解原文本內(nèi)涵及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翻譯,要掌握原文本的中心主旨與核心思想感情,更要熟悉其文化背景,只有這樣才能針對(duì)具體文化詞匯,選擇合適的翻譯方法,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在文本翻譯中進(jìn)行文化傳承的重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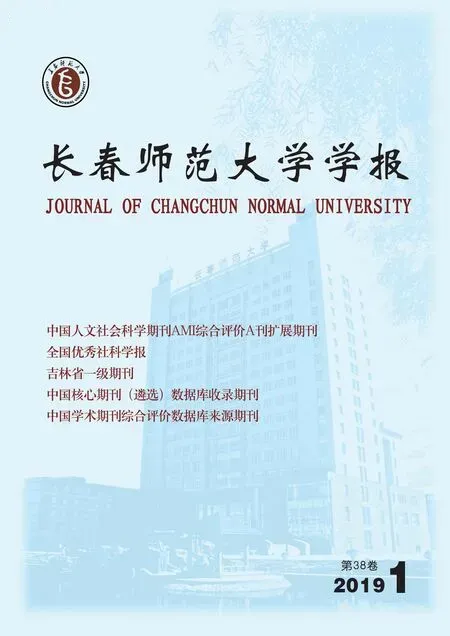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1期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1期
-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聽覺文化研究的理論溯源及發(fā)展軌跡
-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價(jià)值意蘊(yùn)與時(shí)代使命
- 大學(xué)英語(yǔ)教學(xué)改革背景下社團(tuán)語(yǔ)言學(xué)習(xí)法(CLL)教學(xué)策略探究
- 行政管理專業(yè)問題導(dǎo)向式教學(xué)探索與反思
——基于公共經(jīng)濟(jì)學(xué)課程視角 - 走出“就近入學(xué)”政策的認(rèn)識(shí)誤區(qū)
- CDIO理念視角下兩岸應(yīng)用型本科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基地建設(shè)探索與實(shí)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