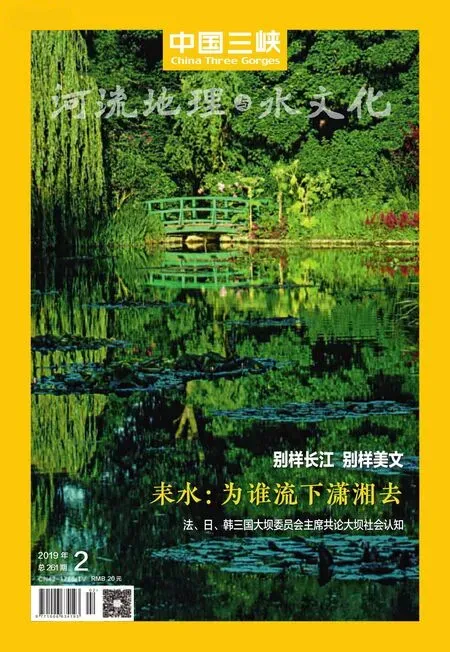蔬食記
◎ 文 | 文河 繪圖 | 劉鑫 編輯 | 王芳麗
白菜
我們這兒,淮北平原,一般農家,都種大白菜。
牲口糞上得足,地壯,菜葉剛長出來,貼地皮兒卷著,水汪汪的。靜靜看一會兒,心里有淡淡的喜悅感。
白菜挺喜歡張揚的,菜葉四下里散著,你挨著我,我挨著你,蓬蓬松松,仿佛一叢一叢的。到了秋天,就開始收心了,菜幫支棱起來,一層一層向里收,一棵是一棵,每一棵之間都保持著相應的獨立距離。就像有些人,年輕時張揚,簡直跋扈,入了中年,則變得格外內斂,甚至沉默寡言起來。
下霜了。白菜幫兒收得緊緊的,瓷實。用手按,按不動。仿佛白菜的心里,有太多的事情藏著。
下雪之前,白菜得收回去。
北方的雪大,天寒地凍。白菜凍僵了,會走味兒,所以,最好把白菜放入地窖。沒有地窖,放在廚房里也行,一般都是對著鍋灶,靠墻角一棵一棵碼好,碼得整整齊齊的,上面再蓋一層干麥秸。冬天,鍋灶里燒火,廚房暖和。炒菜味兒,蒸饃味兒,刷鍋水味兒,柴草味兒,炊煙味兒,還有白菜清幽幽、暗沉沉的味兒,交織在一起,很好聞。
白菜燉豆腐,北方人的普遍吃法。燉湯,嫩白菜葉、嫩白菜心最好。咕嘟咕嘟滾開的湯,菜葉菜心,稍稍一燙即可,清,鮮。
下鍋搟面條,也可以揪幾把白菜葉放里面。

白菜幫兒,可以醋溜。生姜片,辣椒,醋,素油。油熬熱,姜片和辣椒炒出味兒。菜幫切成長條,大火一過。醋溜白菜,脆,水靈。
兒時,雨雪天黑得早,小北風呼呼刮著。夜晚真漫長呀。窗欞上是新貼的舊報紙,風一點也刮不進來,煤油燈點上,屋里亮堂了。那時,父親還是小學教師,常從學校拿些舊報紙來練書法、包東西。
母親問,吃什么呢。
父親看看天,想了想,就對我說,去,喊你國安大伯去,晚上我倆喝兩杯。
我蹬蹬蹬跑到鄰居家,剛進院子,還沒看到人,就喊道:“大伯,晚上喝兩杯!”
國安大伯哈哈大笑,說,好啊。
國安大伯和父親對坐在椿木小方桌前,母親很快就整出兩個家常菜。父親用火鉗從鍋灶里把去了火氣的劈柴疙瘩夾幾塊放在瓦盆里,一盆暗火,暖乎乎的。冷酒傷胃,父親就把小塑料桶里的高粱燒酒倒進白瓷缸里,在火上溫熱。兩人對酌,說些閑話。
兩人喝到高興的時候,母親又端上一盤涼拌白菜心,菜心切得細細的,白嫩,清爽。國安大伯用筷子蘸些酒,送到我嘴里。我用舌尖嘗了嘗,好苦,好辣。
我把房門開個縫,趴那兒向外面看,一股寒意灌了進來,真冷。風嗖嗖掠過房檐,沒有星。夜,黑透了。
蘿卜
俗話說,蘿卜青菜,各有所愛。那么,我就愛蘿卜吧。但,我不愛空心大蘿卜。
我們這兒主要種青蘿卜,白肚青把。淤土地里長的水份少,質地密實,炒著吃最好。五花肉切片,蘿卜切片,加醬油炒,鮮而不膩。
沙土地里長的蘿卜水靈,個兒也更大,微甜,適合涼調,拌蘿卜絲。小時候,有兩年,初冬,父親和村里人一起去縣城附近買這種蘿卜。那時村莊旁的公路上,一天只通一次汽車,去縣城很不方便,他們也舍不得花幾毛錢坐車。他們就拉著木板車,帶著干糧,天麻麻亮出發,走著去,天落黑才回來。一來一回,幾十公路,就為了那么一小板車蘿卜。那時貧窮,活得執著而熱情。
我們這兒也種紅蘿卜,但種得少。可能紅蘿卜有點辣吧。紅蘿卜的形狀很好看,圓圓的一團,有溫柔的弧線。顏色很艷,切開,蘿卜皮兒的里側,甚至紅得發紫。
白蘿卜,渾身皆白,只能燉湯,此地不生。
還有一種蘿卜簡直就是水果,水蘿卜。這種蘿卜皮兒薄,深青,狀若紅蘿卜而小,水分豐富。算是蘿卜中的尤物。洗一洗,直接生吃,咬一口,脆,清甜,原汁原味。
農家節儉,蘿卜纓也舍不得丟。洗凈,開水煮熟,搭在麻繩上曬干,然后收起來,放袋子里存著,算是干菜。冬天,吃豆面條時,放鍋里一些。豆面條煮得黏糊糊的,很好吃。蘿卜纓有點青澀味兒,也算是別有風味吧。還可以腌制。蘿卜纓洗凈,晾去水分,放在壇子里,撒下很多鹽。吃的時候,咸味兒洗去,切碎,拌上小磨麻油,香中帶一點清苦。

幾年前的夏天,去烏鎮,細雨綿綿。細雨中的江南小鎮,看上去更有韻味。飛檐,曲廊,花磚,青苔,蘭草,天井,荷花缸。仿佛整個歲月,就這樣在滴滴答答的雨聲中,悠悠來了,悠悠去了,又綿綿不盡。沿河兩岸,賣有一種腌制的小蘿卜,小巧玲瓏。套用《紅樓夢》中劉姥姥的話來說,這蘿卜頭長得可真俊!買幾包帶回去嘗嘗,咸中帶甜,甜中透脆,很是可口。
過了年,開過春,天氣變暖,蘿卜會發芽。這樣,蘿卜就變“糠”了,就成了空心蘿卜。空心大蘿卜,看上去很好,但味兒其實已經寡了。
茄子
我們這兒的農家,都愿意種青茄,極少種紫茄。青茄呈橢圓形,弧線極美。紫茄紫郁郁的,細長,皮兒比青茄略厚。
茄子開花結果,得打杈。杈分公杈、母杈。魯迅有名言,刪夷枝葉者,決得不到花果。但公杈得摘去,否則枝杈縱橫,爭搶營養,影響通風,不利于結茄子。
茄子的葉子大,糙,澀。鉆在茄棵里打杈,手臂給刮得癢辣辣的。
茄子喜水,夏天,太陽毒,得兩三天澆灌一次。太陽落下去了,天還很亮,用鐵皮桶一桶一桶把水從水井里提出來,倒在溝畦里。流水順著溝畦流向茄棵,咕咕直響。菜地吃足了水,菜才旺。
茄子垂下來,挨著土的地方,容易起瘢。頭茬兒茄子,瘢痕多,但好吃。

新茄子下來,天已經熱了。母親煎茄子,在案板上把茄子切成均勻的小片,放入攪拌好的面糊。豬油熗鍋,燒熱,煎。煎得微焦,微黃,油亮,鍋鏟鏟出,放入青竹蔑編成的笊簸里。這樣,一直煎夠一家六口人吃的。茄子煎好,還要熬。鍋里放上油,辣椒,大料,炸出味兒,再注入半鍋水,燒滾,把煎好的茄片倒入里面燒開,放入一些鮮嫩的小青菜。最后,再放一些剛揪回的大茴香提提味兒,一鍋飯就算成了。
母親做飯,我燒鍋,一把把向灶膛填麥草,廚房里悶熱。我抱怨,吃頓飯,太麻煩了。母親便訓斥,你是連吃都嫌費事!
現在想想,吃,也真是對生活熱愛的一種體現。古樂府里,遠方來信,山川阻隔,夢寐相憶的兩個人,信里浮言盡去,不作任何寒暄語,唯鄭重囑咐“加餐飯,長相憶”。最深切的關懷,反而只能是這樣現實,具體到吃飯穿衣。飯要吃飽,衣要穿暖。
青椒炒茄絲。青椒切細,茄子切絲,大火炒,不能炒老,也是一道家常菜。
蒸茄子。茄子切成條,蒸,蒸爛,蒜泥一拌,即可食用。
《紅樓夢》里,賈府做工復雜的“茄鲞”,好吃倒是好吃,但講究到暴殄天物的程度,已是過分了。吃飯,最重要的是吃得安然。身心安然,如此才好。
小時候,父親騎大架自行車,帶我走親戚。是家遠親,離得很遠,不常來往。天亮出發,到了那兒,已近午時。午餐很豐富,吃的什么,都忘了。唯記得飯后,親戚家切了一盤生茄條,端上來讓我們吃。我家從沒生吃過茄子,我大為驚訝。父親出于禮貌,吃了一根。我堅決不吃。但很多年過去了,那種生茄子濃郁青幽的味道,還留在我的記憶里。
入了秋,茄子繼續結。秋茄子皮厚,不好吃。青茄子長老,就會變白,進而變黃。秋陽下,黃燦燦的,又很靜。風吹過來,菜園一片沙沙響,但某個看不到的地方,還是顯得靜。老茄子留種,第二年繼續種。一年一年,仿佛日子多著呢。但慢慢的,人還是老了。
村子里,很多人,活著活著,就不見了。
蠶豆
蠶豆,亦名羅漢豆。其實,我更喜歡這后一個名字。但我們這,從沒這個叫法。
蠶豆的命皮實,可以種在河畔,地邊兒,荒疏的林間。丟一粒蠶豆籽,扒個窯兒,埋里面,就不用再過問了。冬天,蠶豆棵青青的,很單薄的樣子,但下大雪,也凍不壞。
老家里的人,命都皮實,也像蠶豆棵。所以,也活得豁達,生死無畏。
蠶豆花開了,天變暖和了。
蠶豆花白色的花瓣,帶一點跳脫的淡紫。花心處又帶一片深黑,像一滴慢慢洇開的焦墨。早晨,太陽出來,黑白分明的花瓣上,大露水珠子閃閃發光。蠶豆花總給我一種奇異神秘的感覺,仿佛它們從遙遠的地方,剛剛趕來。
蠶豆花在地頭兒靜靜開著,天空微藍,有幾抹云縷靜靜停在那兒。花斑鳩在樹梢一遞一聲地叫,兩只,東一聲,西一聲,相互呼應。就那么叫著,叫了很長時間,似乎相互期待著什么。它們怎么不飛到一塊兒呢。樹上新葉剛剛長齊,還沒成蔭。仿佛有很多故事,正要開始。
花謝了,蠶豆角長出來了。蠶豆角水嫩,拌面糊,油煎,然后再放湯里煮一下,連皮兒吃,鮮極。但老家人很少這樣吃的,說是糟蹋東西。
鮮蠶豆剝殼,一粒一粒,深青,飽滿,有點古拙。清水煮,不加任何材料,連鹽也不放。煮熟,直接吃,味道鮮而質樸。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一種吃法了。真山真水,自然無飾。

蠶豆放進小砂鍋,八角,桂皮,茴香,辣椒,鹽,小火燉。蠶豆燉熟,燉面,滴些小磨麻油,就成了。端起來,放在一張小白木桌上,坐下,用小湯勺一勺一勺盛著吃。院外,香椿樹頭茬葉子被掰去,第二茬又長大了,成蔭了。又聽到斑鳩叫。很快,就能聽到蟬鳴了。
剝了殼的鮮蠶豆,再剝去皮兒,只要豆瓣,和韭菜放在一起清炒。韭菜的味道張揚,蠶豆的味道內斂,二者恰好互補。青青翠翠的一盤,光陰深秀,滋味鮮美。五月深碧,麥子出穗、斷臉兒、灌漿。該準備豐收了。
蠶豆曬干,用油炸,炸焦,炸開花,撒上鹽,下酒。冬天,農事已畢。勞累了這么長時間,該歇息歇息,散散身子骨了。
豆芽
豆芽,有綠豆芽,有黃豆芽。這里說的是黃豆芽。
挑揀圓滾飽滿的黃豆,清水浸泡,豆皮兒泡軟,水倒掉,放在盆里,用濕棉布蓋住。蓋得嚴嚴實實,放在廚房角落的暗影里。母親說,豆芽見了光,就變綠了。變綠的豆芽有什么不好呢?我想不通,越發對棉布遮蓋的豆芽感到好奇,想看看它們萌芽沒有,到底怎么樣了。就偷偷掀開棉布,看。也沒見有什么,倒是聞到一股濃濃的豆腥味兒。
黃豆生芽了,黃瑩瑩的。兩個豆瓣緊緊閉合,向下勾著,有些呆頭呆腦。
炒豆芽要用生姜片熗鍋,最好再放幾個紅尖椒,豆味兒重,得用辛辣之味兒壓一壓。
豆芽燉湯,豆芽燉得越面越好。豆芽根兒燉爛,放幾根蔥。豆味兒入湯,風清云淡,淡之欲無,湯就變鮮了。

院子里的桂花樹下,堆著一堆蓋房子剩下的細沙。母親抓把黃豆埋進去,澆桶清水。過幾天,青綠色的豆芽探頭探腦地鉆出來。母親扒開細沙,把豆芽拾掇干凈,午飯時,清寒的飯桌上,便又多了一盤小菜。我們兄弟幾個,吃得高高興興,好像額外多得了什么。
懂生活的人,能把清寒,變成清歡。
我們這兒有道菜,豆芽炒粉絲,加肉末,叫螞蟻上樹。
麥子收割后,等一場雨,種豆子。地頭兒豆芽出得稠,得剔掉。豆芽剛鉆出地皮兒,正好吃。天氣熱,光照強,南風大,等兩天,豆芽就老了,支棱出葉子,只好喂羊。做一只羊,也很好的,一輩子,只吃葉子,簡簡單單。
有兩年,幾個朋友,常小聚。一個寫古體詩,一個喜歡哲學宗教,還有一個喜歡心理咨詢。我們離得也近,聚著方便。小飯館一坐,點幾個家常菜,酒酣耳熱,天馬行空,高談闊論。
每次點菜,我都喜歡點一盤炒豆芽。
后來,各自一忙,便聚得少了。偶爾一聚,也少了以前那種閑適和隨性。《聊齋》里說,緣來則聚,緣盡則散。很多世事,也只能作這樣的達觀之想罷。要想更好地熱愛這個世界,我們就必需接納它的種種局限和缺憾。
扁豆
冬夜,擁被臥讀。讀《聊齋》。
王漁洋題《聊齋》詩,有句子,“豆棚瓜架雨如絲”。王漁洋詩主神韻說,但這一句,卻最是樸素有味。瓜架上面結的是什么瓜呢,吊瓜?絲瓜?瓠瓜?不知道。但豆棚,則是扁豆棚了。

我們這兒,稱扁豆為眉豆。眉是濃眉。我們這兒夸一個男人長得帥,則曰,濃眉大眼。濃眉大眼,看上去敞亮。
我們這兒多種青眉豆和紫眉豆。青眉豆開白花,長大了,微微變白。長老了,直白。紫眉豆開紫花,葉梗藤蔓都是紫的,真好看。
清人有個叫艾衲居士的,編著一本短篇小說集,《豆棚閑話》。我讀了兩篇,覺得并不怎樣,就不讀了。卻很喜歡這個書名。像個隨筆集子。累了,坐在豆棚下,說說閑話,談談農事。農耕時代的生活圖景。
扁豆肯結,越到秋天,越肯結。一簇簇的花,開一茬又一茬。扁豆也結一茬又一茬,一串串綴滿藤蔓。秋風吹在扁豆藤蔓上,深青的葉片紛紛翻動,扁豆也帶有寒意。摘的時候,放在手里,涼涼的,內心會突然被什么東西觸動一下。
扁豆切絲,炒青椒。扁豆切條,炒肉絲。扁豆拌面糊,煎。扁豆的味道比較強悍,沖,得趁大油。
扁豆結得太多了。吃不完,煮。煮熟的豆角,再用灶膛里的草木灰吸去水分,然后放在草席上曬。樹葉落了,明亮的日腳斜斜照在堂屋門口,光陰徘徊。母親和鄰居大嬸大娘在房檐下坐著,一針一線,納鞋底,嘮家常。豆角曬干曬透,把灰抖去,裝入布袋,好好存放。過大年,熬肉湯,湯里放粉絲,海帶絲,干扁豆角。扁豆角清水洗干凈了,還隱隱有點草木灰的氣息,憑添一種獨特的風味。
干扁豆角燜五花肉,算是老家舊時生活中的一道家常大菜。
兒時,其實是很貧窮的。偶爾吃頓好的,記憶深刻。回憶起來,天地廣闊,仿佛很豐富似的。悟道的禪師說,“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如常,才好。舊信里,親人之間報平安,常寫,一切如常,請勿掛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