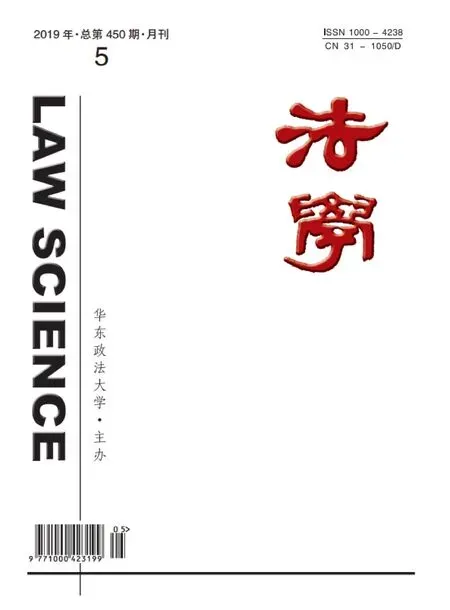國際投資條約下知識產權保護的困境及其應對
●徐 樹
在傳統上,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本無太大關聯,知識產權條約與貿易條約、投資條約相互獨立,各自沿著自身的軌道發展。知識產權條約雖強化了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但因其缺乏行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故使得執行效果大打折扣。〔1〕參見劉筍:《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的不足及TRIPS協議與國際投資法的關系》,《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簡稱《TRIPS協定》)的達成,將知識產權保護納入到了貿易范疇,并為知識產權條約的執行裝上了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牙齒”。但是,因知識產權人在WTO體制下不享有訴權,故其無權援引《TRIPS協定》尋求WTO的救濟。
國際投資條約的大量出現改變了知識產權人依賴本國政府尋求國際救濟的被動局面。〔2〕本文所稱的國際投資條約,包括雙邊投資條約(BIT)及含有投資章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人可作為投資條約下的“投資”“投資者”受到投資條約的保護。當東道國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措施有損知識產權利益時,知識產權人可利用投資條約中的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ISDS),將東道國訴諸國際仲裁,要求賠償其知識產權損失。投資條約及其仲裁機制“沉睡的”功能似乎正漸被“喚醒”,〔3〕See Bryan Mercurio, Awakening the Sleeping Gi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5, No.3, 2012, p.871.成為知識產權人挑戰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要求東道國遵守知識產權規則的新的法律工具。然而,國際投資條約與知識產權條約的競合保護打破了知識產權條約在私權保護與社會福祉之間既已建立的平衡,引發競合保護上的困境,亟待理論深耕。
一、涉及知識產權政策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的考察
當前涉及知識產權政策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主要包括“奧貝泰克訴美國案”“莫里斯訴烏拉圭案”“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及“禮來訴加拿大案”。〔4〕本文僅統計可公開獲取并已作出裁決的案件。除這些案件外,還有部分涉及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的投資仲裁案件未予公開或已經撤案,包括“Erbil Serter訴法國案”(涉及船型設計版權)、“Gilead Science訴烏克蘭案”(涉及丙型肝炎藥品專利)、“Shell Brands訴尼加拉瓜案”(涉及殼牌石油公司商標權)等案件。此外,也有一些投資仲裁案件雖部分涉及知識產權,但并不直接與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政策相關,這包括“Joseph Charles Lemire訴烏克蘭案”“Generation Ukraine訴烏克蘭案”“AHS訴尼日爾案”“MHS訴馬來西亞案”“Grand River Enterprises Six Nations訴美國案”等案件。在“奧貝泰克訴美國案”中,加拿大奧貝泰克制藥公司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的仿制藥品申請未能獲得批準,其認為這侵犯了為仿制藥品申請而進行的投資。在兩起“莫里斯案”中,國際煙草巨頭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主張烏拉圭、澳大利亞的煙草平裝立法限制了其商標的使用,侵害了其商標投資。而在“禮來訴加拿大案”中,美國制藥商禮來公司試圖挑戰加拿大法院的專利無效判決,認為該判決侵害了其專利權投資。
(一)“奧貝泰克訴美國案”
奧貝泰克是一家主要研發和生產仿制藥品(generic drugs)的加拿大企業。該公司向美國聯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了兩項仿制藥品的上市申請,但均未獲得批準。第一項仿制藥品的上市申請涉及美國輝瑞公司的專利藥品左洛復(Zoloft),該藥品主要用于治療抑郁等癥狀;第二項仿制藥品的上市申請涉及美國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專利藥品普伐他汀(Pravachol),該藥品具有降血脂的功效。
2008年12月10日及2009年6月4日,奧貝泰克公司依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11章向美國分別發出仲裁通知,認為美國相關部門不批準其兩項仿制藥品的上市申請構成歧視性、不公平、不公正待遇,是對其已有投資的征收。根據美國《藥品價格競爭與專利到期補償法》(也稱Hatch-Waxman法案),仿制藥品上市申請的批準應當考慮已上市藥品的專利狀況,避免可能的專利侵權。〔5〕參見梁志文:《藥品專利鏈接制度的移植與創制》,《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8期。當原研藥品專利到期、專利被宣告無效或不存在對原研藥品的專利侵權時,首次提交仿制藥品上市申請的企業將被授予為期180天的美國市場獨占權。據此,奧貝泰克公司主張,其仿制藥品上市申請未能獲批是美國聯邦政府、聯邦法院未能正確適用美國法律所致,其既有投資因此而遭受損害。
2013年6月14日,仲裁庭作出裁決,否定了其對案件的管轄權,并指出,奧貝泰克公司在美國沒有與本案相關的商業存在或相關活動,其藥品研發和藥品上市申請的準備工作均在加拿大進行。因此,奧貝泰克公司至多只算對美國的貨物出口商而非投資者,其為仿制藥品上市申請而進行的前期投入不屬于在美國作出的“投資”。〔6〕See Apotex Inc.v.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14 June 2013.
(二)“莫里斯訴烏拉圭案”
2010年2月19日,莫里斯公司向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提交了仲裁申請,主張烏拉圭的控煙措施侵犯其商標權,有違瑞士與烏拉圭BIT下的投資保護義務。〔7〕See Philip Morris Brands Sàrl,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and Abal Hermanos S.A.v.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ARB/10/7, Request for Arbitration, 19 February 2010.該案烏拉圭的被訴措施主要為單一外觀要求和健康警示面積要求。根據前者,相同品牌的卷煙產品須使用相同包裝;根據后者,健康警示信息在卷煙包裝中所占面積比例須達到80%。
2013年7月2日,仲裁庭裁定對案件享有管轄權,拒絕接受烏拉圭的管轄權抗辯主張。仲裁庭認為,莫里斯在烏拉圭的商標構成瑞士與烏拉圭BIT 下的“投資”,其仲裁請求符合各項管轄條件。瑞士與烏拉圭BIT第10條規定,僅當投資爭端訴諸東道國法院后屆滿18個月,投資者才可將該爭端提交國際仲裁。盡管莫里斯提交仲裁請求時未滿足18個月期限的要求,但仲裁庭認為這并不影響其確立管轄權。〔8〕Supra note 〔7〕,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 July 2013.2016年7月8日,仲裁庭作出最終裁決,裁定烏拉圭被訴措施不構成對投資條約義務的違反。在仲裁庭看來,商標權人并不享有絕對的、免受管制的使用權利,其僅具有排除市場第三人使用的排他性權利。在理論上,商標權作為財產權,可以被征收。但是烏拉圭的控煙措施僅是限制了商標的使用方式,并未對商標投資造成重大影響,因而不構成征收。而且,烏拉圭的控煙措施亦不構成對莫里斯商標投資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對該裁決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單一外觀要求”違反了公平公正待遇義務,而且烏拉圭國內法院的不一致判決構成了拒絕司法。〔9〕Ibid, Award, 8 July 2016.
(三)“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
2011年6月22日,莫里斯亞洲集團公司援引中國香港與澳大利亞BIT提出仲裁請求,要求澳大利亞放棄實施煙草平裝法案并賠償其投資損失。根據該法案,自2012年12月起在澳大利亞出售的卷煙、雪茄等煙草制品須采用特定的卷煙紙、包裝材料、尺寸和樣式,除按規定呈現品牌、公司名稱外不得帶有商標、標識。此外,包裝正面75%、背面90%的面積須用于健康警示圖案。莫里斯認為,該立法構成對其商標權的間接征收,是對其商標投資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有違《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義務。〔10〕See 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v.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UNCITRAL, PCA Case No.2012-12, Notice of Arbitration,21 November 2011.
2015年12月17日,仲裁庭裁定對案件無權管轄,并且認為,早在2010年4月29日,澳大利亞總理即已毫無保留地宣布了將對煙草平裝進行立法,自那時起,相關投資者就能夠合理地預見到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法案的通過和實施。本案申請人的最終控制者在了解該信息后,于2011年2月進行了投資重組,由注冊地在中國香港的莫里斯亞洲公司收購了注冊地在澳大利亞的莫里斯澳大利亞公司的股權。重組投資結構只為獲得中國香港與澳大利亞BIT的條約保護,而不是基于稅收等商業因素的考慮。故此,仲裁庭裁決莫里斯亞洲公司對澳大利亞提起投資仲裁程序構成了權利濫用。〔11〕Ibid,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17 December 2015.
(四)“禮來訴加拿大案”
2013年9月12日,美國醫藥企業禮來公司依據NAFTA第11章對加拿大發出仲裁通知,要求高達5億加元的賠償。禮來公司主張,加拿大法院對其奧氮平(Zyprexa)及阿托莫西汀(Strattera)兩種藥物作出的專利無效的判決有違加拿大在NAFTA以及《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下的義務,侵害了其專利投資。〔12〕See Eli Lilly and Company v.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 ICSID Case No.UNCT/14/2, Notice of Arbitration, 12 September 2013.
2017年3月16日,仲裁庭作出最終裁決。仲裁庭先是肯定了對案件的管轄權,但隨后駁回了禮來公司的實體主張。其認為,投資仲裁并非東道國法院的上訴程序,除非有明確證據表明東道國法院存在“過分的、令人震驚的行為”等極特殊情形,否則仲裁庭不宜對東道國法院進行條約審查。在本案中,“承諾實用性原則”作為可專利性標準在加拿大判例法中由來已久,加拿大法院適用該原則宣告專利無效的判決并不構成對禮來專利的征收,也不會導致對禮來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13〕Supra note 〔12〕, Final Award, 16 March 2017.
考察上述案件涉及的知識產權類型,“奧貝泰克訴美國案”和“禮來訴加拿大案”涉及藥品專利,“莫里斯案”涉及商標權。就援引國際投資條約的目的而言,奧貝泰克公司的目的不在于保護藥品專利,而在于限制美國制藥商的藥品專利,從而實現其仿制藥品的盡快上市。莫里斯公司、禮來公司的目的在于強化對其商標權、藥品專利的保護,借以挑戰東道國的知識產權管制措施。
上述案件反映出國際投資條約及其仲裁機制已成為知識產權人挑戰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措施)、保護海外知識產權的全新救濟途徑。傳統上,當海外知識產權因東道國措施而遭受損害時,知識產權人僅可依據東道國法律尋求當地救濟或請求母國政府尋求WTO救濟。而投資條約及其規定的仲裁機制為知識產權人在國際層面起訴執行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打開了另一扇大門。盡管目前尚無成功的案例,但是知識產權人援引投資條約挑戰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措施)的可能性有增無減。可以想見,莫里斯公司、禮來公司的訴訟策略及法律主張將會激勵更多的知識產權人將知識產權爭端訴諸投資仲裁。〔14〕See Gabriele Gagliani,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on Descent and Technical Problem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51, 2017, p.346.案例從實證角度反映出投資條約、知識產權條約對知識產權的競合保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投資仲裁機制與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機制的沖突困境,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由“與貿易有關”向“與投資有關”的延伸帶來了貿易法、投資法在知識產權議題上的碎片化格局,打破了知識產權規則在私權保護與社會福祉之間建立的平衡。如何使得貿易法、投資法對知識產權議題的擴展不打破知識產權規則既已建立的平衡便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理論問題。
二、現有國際投資條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路徑
(一)將知識產權視為“投資”
知識產權被視為“投資”是國際投資條約保護知識產權的邏輯起點。〔15〕參見田曉萍:《國際投資協定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路徑及法律效果——以“禮來藥企案”為視角》,《政法論叢》 2016年第1期。在知識經濟背景下,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更多地依賴于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無形資產。為了促進和保護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投資,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條約明確將知識產權列舉為“投資”的一種形式。
首先,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范圍取決于投資條約文本。比如,有些投資條約未對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范圍作出限定,如美國2012年BIT范本第1條規定“投資”的形式包括知識產權,但并未對其進行界定。該定義模式使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范圍呈現出開放狀態,即便知識產權條約不認可的知識產權類型也可能落入投資條約的“投資”范疇。又如,有的投資條約對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進行了窮盡或非窮盡式列舉。再如,有些投資條約甚至明確將《TRIPS協定》未認可的知識產權類型納入投資保護范圍,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投資章中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范圍遠超《TRIPS協定》范圍,要求各締約方應確保源自植物的發明、已知產品的新用途或使用已知產品的新方法或新流程可獲得專利。〔16〕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第2條及其附件的規定,TPP中有關擴大可專利性客體的規定被“暫停適用”,除非締約國協議終止暫停適用。該規定將使投資條約保護的知識產權范圍超出知識產權條約的要求。
其次,投資者能否獲得或擁有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須遵循東道國法律。知識產權具有地域性,國際條約本身不創設知識產權,而僅僅是對所認可的知識產權類型提供最低保護標準。一個主題可能在一國作為知識產權被保護,而在他國則落入公有領域。〔17〕同前注〔3〕,Bryan Mercurio文,第 876~877頁。是故,僅當投資者按照東道國法律已獲得或擁有知識產權且該知識產權類型為投資條約所涵蓋時,才可以成為投資條約所保護的知識產權“投資”。尚待批準的知識產權申請并不必然得到東道國的批準,因而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申請本身并不能自動成為國際投資條約下的知識產權“投資”。知識產權申請本身不等于知識產權的確立,為知識產權申請而投入的成本也不會自動成為投資條約所保護的投資。
當然,如果知識產權申請受到東道國法律的保護,并被賦予法律上的權利(如優先權),那么該申請本身可能被視為申請者根據東道國法律所擁有的財產。〔18〕See Dany Khayat & William Ahern, Reliance on Investment Treaty Standards to Claim for Failures to Recognize or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Vol.3, 2016, pp.406-409.歐洲人權法院曾在“Anheuser-Busch訴葡萄牙案”中指出,商標注冊申請具有經濟價值,受到葡萄牙法律的保護,可構成申請者所擁有的財產。〔19〕See Anheuser-Busch Inc.v.Portugal,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rand Chamber, Application No.73049/01, Judgment,11 January 2007.即便如此,知識產權申請并不因其可能被東道國法律視為財產而自動轉化為投資,除非其滿足相應的投資屬性。〔20〕See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1.在“奧貝泰克訴美國案”中,仲裁庭明確指出,盡管奧貝泰克公司的藥品上市申請本身可以進行買賣交易,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申請者所擁有的“財產”,但這并不能將其轉變為NAFTA第11章下的“投資”。奧貝泰克公司的藥品上市申請僅僅是其向美國出口相應藥品的條件,因而是作為出口商的行為,而非作為投資者的行為。〔21〕同前注〔6〕,第 206~225 段。
最后,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須具有投資屬性。僅僅被授予或確認知識產權并不能自動成為受保護的“投資”。〔22〕See Carlos Correa & Jorge E.Vinua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Protected Investments: How Open are the G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9, 2016, pp.91-120.“Salini訴摩洛哥案”的仲裁庭指出,“投資”概念具有客觀的含義,一項“投資”須滿足資產投入、風險承擔、存續期間、預期收益以及有利于東道國經濟發展等特征。〔23〕See Salini v.Morocco, ICSID Case No.ARB/00/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s.51-52.不具備投資特征的知識產權難以成為投資條約保護的對象。〔24〕See Sigfrid Fina & Gabriel M.Lentner, The European Union’s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Vol.18, 2017, pp.284-285.一項知識產權是否具備投資特征,應結合知識產權在東道國的獲得、使用、投入市場等情況進行綜合考察。〔25〕See Ruth L.Okediji,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ment”? Eli Lilly v.Canad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5, 2014, pp.1126-1127.譬如,在東道國開展研發并獲批專利、在東道國注冊商標并將其用于在東道國生產并銷售的產品等商業行為,將更容易被認定符合投資特征。反之,若專利產品在他國研發和生產僅是為了出口專利產品而在東道國申請獲得專利的行為,將難以被界定為知識產權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實踐中對投資特征的認定極具彈性,甚至存在“前述投資特征并非界定投資的條件,而僅僅是投資的典型特征”的觀點。〔26〕Christoph Schreu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8.在“莫里斯訴烏拉圭案”中,仲裁庭認為應賦予“投資”寬泛的含義,所謂的投資特征不得用來限制“投資”應有的寬泛、彈性含義。而“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禮來訴加拿大案”的仲裁庭在未考察投資特征的情況下即肯定了商標、專利的投資適格性。由此可見,仲裁實踐傾向于肯定知識產權的“投資”屬性。
(二)實體保護:通過投資待遇條款“引入”和“擴張”知識產權規則
國際投資條約本身并未包含知識產權規則,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主要是通過與知識產權條約進行“掛鉤”或“聯結”予以實現的。〔27〕參見張建邦:《國際投資條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現代轉型研究》,《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投資條約與知識產權條約的“掛鉤”主要表現在非歧視待遇、公平公正待遇、征收條款、保護傘條款、履行要求禁止等投資待遇條款中。
其一,非歧視待遇條款與知識產權條約的銜接。由于知識產權是投資條約所涵蓋的“投資”,因此投資條約的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非歧視待遇條款適用于知識產權,這將導致投資條約下非歧視待遇義務與知識產權條約下非歧視待遇義務的重疊甚至沖突。一方面,《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對非歧視待遇義務規定了諸多例外情形;另一方面,多數投資條約下的非歧視待遇義務卻并未就知識產權設定任何例外。因此,為了協調不同條約涉及知識產權的非歧視待遇義務,一些投資條約明確引入知識產權條約中的非歧視待遇條款。例如,美國2012年BIT范本第14條第4款規定,投資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不適用于《TRIPS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例外或減損情形,該規定為知識產權投資者在投資條約下援引和執行《TRIPS協定》提供了可能。
其二,公平公正待遇條款對知識產權條約的補充。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的相對性保護標準不同,公平公正待遇屬于絕對性保護標準,其對東道國的投資保護義務作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多數投資條約并未就公平公正待遇的判斷基準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對于公平公正待遇條款的解釋和適用,投資仲裁庭擁有很大的裁量空間。公平公正待遇條款的開放式表述已使該條款成為投資者尋求投資仲裁的主要訴訟策略之一,而仲裁實踐對公平公正待遇條款也呈現出擴張解釋的趨勢。〔28〕See UNCTA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 Seque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2, p.10.
實踐中,知識產權人對公平公正待遇條款的援引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第一,東道國違反《TRIPS協定》即自動構成對知識產權投資者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第二,東道國對知識產權的管制措施違背知識產權人的“合理預期”,因而違反東道國的公平公正待遇義務。在“禮來訴加拿大案”中,禮來公司即主張加拿大將“承諾實用性”作為可專利性標準有違《TRIPS協定》的規定,也違背了禮來公司的合理期待,因而違反了公平公正待遇義務。在“莫里斯訴烏拉圭案”中,仲裁庭多數意見認為,烏拉圭的控煙措施是保護公共健康的善意措施,并非武斷行為,且未違背投資者的合理預期。反對意見則認為,烏拉圭控煙措施中的單一外觀要求是武斷的、不合理的,因而違反了公平公正待遇義務,而且烏拉圭法院就控煙措施合法性作出的不一致的最終判決屬于拒絕司法。仲裁員之間的意見分歧表明,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政策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待遇要求仍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知識產權人可能援引公平公正待遇條款挑戰與知識產權條約相符的東道國政策或措施。〔29〕See Kathleen Liddell & Michael Waibel,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Judicial Pat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9, 2016, pp.145-174.
其三,征收條款與知識產權條約的綁定。根據征收條款,除非滿足出于公共目的、符合正當程序、非歧視、給予補償等條件,否則東道國不得直接或間接征收外來投資。知識產權作為投資條約涵蓋的“投資”,也有權免受東道國的非法征收。但問題在于,東道國撤銷、限制或創設知識產權的行為以及東道國頒發知識產權強制許可的行為是否構成征收?對此,多數投資條約規定,與《TRIPS協定》相符的撤銷、限制或創設知識產權的行為以及強制許可行為不構成征收。然而,投資條約征收條款與《TRIPS協定》的綁定雖然避免了兩者間的沖突,但是同時也給東道國帶來了訴訟風險。知識產權人可借助《TRIPS協定》將東道國告上國際仲裁庭,挑戰東道國措施與《TRIPS協定》的相符性。〔30〕See Christopher Gibson, A Look at the Compulsory Licen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Cas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25, 2010, pp.419-422.認定違反《TRIPS協定》即當然意味著肯定征收的自動存在,除非東道國舉證證明其措施與《TRIPS協定》相符。〔31〕See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Challeng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rm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9, 2016, pp.267-270.在“莫里斯案”“禮來訴加拿大案”中,投資者均主張被訴國撤銷或限制知識產權的行為違反《TRIPS協定》,因而構成征收。
其四,保護傘條款對知識產權條約的呼應。保護傘條款是要求締約國遵守對外國投資者所作承諾的條款。例如,瑞士與烏拉圭BIT第11條規定,任一締約方應持續保證遵守其對其他締約方投資者所作的承諾。借助保護傘條款,知識產權人可能將知識產權條約也視為東道國所作的承諾,并通過投資仲裁機制予以執行。〔32〕See Anthony Sinclair, Umbrella Clause, in Marc Bungenberg et al.(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eck/Hart/Nomos,2015, pp.944-947.在“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中,莫里斯援引中國香港與澳大利亞BIT中的保護傘條款,認為《TRIPS協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屬于保護傘條款所涵蓋的承諾,并要求仲裁庭裁決澳大利亞違反了其在知識產權條約下的承諾。雖然仲裁庭最終以缺乏管轄權為由駁回了仲裁請求,但是在今后案件中投資者援引保護傘條款執行知識產權條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其五,履行要求禁止條款對知識產權條約的超越。根據投資條約中的履行要求禁止條款,東道國不得對外資的權利或待遇設置特定形式的履行要求。例如,美國2012年BIT范本第7條規定,東道國不得在外資的設立、獲取、擴大、管理、實施、運營或處置等方面強加或強制執行以下要求:將特定技術、生產工藝或其他專有知識轉移給其領土內的人。該條款禁止東道國對外資強制要求技術轉移。與此不同的是,《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并未明確禁止技術轉讓履行要求。〔33〕參見何艷:《美國投資協定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究》,《知識產權》2013年第9期。技術轉讓履行要求作為履行要求的一種,也不在《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的禁止之列。〔34〕參見韓靜雅:《技術轉讓要求規制新趨勢下的中國因應》,《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因此,履行要求禁止條款具有“超TRIPS”(TRIPS-plus)的性質,擴張了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
綜上可知,投資條約雖未直接規定知識產權的實體保護標準,但通過投資待遇條款引入和強化了知識產權條約規則。不符合知識產權條約保護標準的東道國措施可能會被認定為是對投資條約的違反。即使東道國措施完全符合知識產權條約規則,仍存在被認定為違反投資條約之可能,因為投資條約還包含了超出知識產權條約標準的“超TRIPS”條款。
(三)程序保護:通過ISDS機制“執行”知識產權規則
國際投資條約不僅引入和擴張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體標準,而且設置了保障該標準實施的爭端解決機制。相比《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投資條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其創設了投資者與國家間的投資仲裁機制。
傳統上,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主要借助當地救濟和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然而,當地救濟、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作為知識產權國際救濟的途徑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就當地救濟而言,當地法院可能受制于國內法規定無法直接適用知識產權條約,而國內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可能低于條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當地救濟還可能面臨保護主義的風險。就WTO爭端解決等國家間機制而言,僅有國家享有訴權,而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知識產權人并非國家間機制的適格主體。知識產權人的母國政府有權利卻無義務對東道國提出國際要求。事實上,國家往往基于利益的衡量會盡量避免使用國家間機制挑戰他國的知識產權政策。〔35〕See James Gathii & Cynthia Ho, Regime Shifting of IP Law Making and Enforcement From the WTO to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8, 2017, p.474.例如,《南非藥品和有關物質管理法》第15條引發了跨國制藥公司及其母國政府的不滿,但該爭議僅止步于南非的國內訴訟階段。〔36〕參見何艷:《涉公共利益知識產權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反思與重構》,《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4期。巴西、印度等國認為《美國專利法案》第18章相關條款違反了《TRIPS協定》義務,并向美國提起WTO爭端解決的磋商請求,但該案至今未進入專家組程序。〔37〕See United States-US Patents Code, WT/DS224/1,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Brazil, 7 February 2001; WT/DS224/2, Request to Joint Consultations-Communication from India, 19 February 2001.一國在決定是否對他國知識產權措施提起國際訴訟時,不得不考慮其本國是否存在類似措施被他國起訴的可能性。即便一國為保護本國知識產權人利益將他國訴諸WTO等國家間機制并獲得勝訴判決,知識產權人也不會因此獲得對其既有損失的任何補償。
與當地救濟、國家間機制不同,投資條約下的ISDS機制明確賦予投資者訴權,允許投資者依據投資條約就東道國措施直接提交國際仲裁,尋求知識產權的損害賠償。作為“去政治化”的爭端解決機制,ISDS機制能夠更大程度地排除投資者母國、東道國的政治干擾,為投資者提供更有效的國際救濟平臺。在ISDS機制下,作為“投資者”的知識產權人掌握訴訟的主動權,無需依賴其本國政府對東道國提起仲裁程序,也沒有其本國政府的外交和政策顧慮。而且,知識產權人可直接援引投資條約的實體、程序條款,挑戰東道國措施的合法性,要求東道國賠償其損失。若能獲得勝訴裁決,知識產權人就可根據所適用的仲裁程序規則,援引《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或《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在各國法院請求承認和執行裁決。
ISDS機制強化了投資條約、知識產權條約的可執行性和可訴性,給作為“投資者”的知識產權人提供了海外知識產權保護的額外救濟平臺。借助ISDS機制,知識產權人可將對知識產權條約的違反包裝為對投資條約的違反,從而“執行”甚至“改寫”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從形式上看,作為“投資者”的知識產權人在ISDS機制下僅可援引投資條約的保護,但是由于投資條約中的投資待遇條款引入了知識產權條約,故而為知識產權人運用ISDS機制執行知識產權條約提供了方便,知識產權人得以有機會影響知識產權條約的解釋和適用。
三、國際投資條約對知識產權保護應有其固有的邊界
(一)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的自主空間應予尊重
國際投資條約通過引入和強化知識產權規則,為知識產權增添了新一層保護。然而,將知識產權作為“投資”予以保護,并不意味著改變了知識產權的屬性、剝離了知識產權的社會功能。因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目的不僅在于保護知識產權本身,而且在于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來激勵創新,實現私人權利與社會福祉間的有機平衡。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是一體的,不能割裂開來,對知識產權的限制通常從保護對象、保護條件、保護范圍、保護例外、保護期限等方面表現出來。〔38〕See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Investment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同前注〔32〕,Marc Bungenberg 等編書,第1693頁。
《TRIPS協定》在確立知識產權保護最低標準的同時,也為成員方預留了政策的靈活空間,允許成員方根據自身情況合理地平衡私權保護與社會福祉。例如,該協定第27條第1款規定,專利授予的條件為“具有新穎性、包含發明性步驟,并可供工業應用”,但并未對新穎性、發明性(創新性)、可供工業應用(實用性)作出具體定義。而且該協定第1條第1款還規定,各成員有權在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實踐中確定實施《TRIPS協定》規定的適當方法。可見,《TRIPS協定》僅是確立了可專利性的最低條件,但這些條件的具體含義和標準則交由各成員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合理確定。〔39〕《TRIPS協定》規定的靈活性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多邊法律框架中與專利有關的靈活性及其在國家和地區立法中的落實》報告中,對《TRIPS協定》中關于專利的靈活性進行了詳盡的列舉。See WIPO, Patent Related Flexibilities in the Multilateral Legal Framework and Their Legislative Implem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CDIP/5/4 Rev.,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153559, last visit on 30 October 2018.在彈性機制之外,《TRIPS協定》還包含了不少例外條款,如第31條允許成員方未經權利持有人同意強制許可第三人使用知識產權。是故,成員方有權運用《TRIPS協定》內嵌的彈性機制和例外條款來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政策。
然而,當知識產權被財產化并被納入投資條約范疇后,對其的保護得到了強化,但知識產權的限制則存在被弱化之風險。〔40〕See Rochelle Dreyfuss & Susy Frankel, From Incentive to Commodity to Asset: How International Law Is Reconceptualiz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6, 2015, p.566.實踐中,知識產權人常常主張知識產權的絕對保護,試圖剝離知識產權立法下對知識產權的限制,縮減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的彈性空間。例如,在“禮來訴加拿大案”中,禮來公司主張加拿大法院依據“承諾實用性原則”認定其藥品專利無效的判決構成對其專利投資的非法侵害。事實上,《TRIPS協定》并未對實用性等可專利性標準作出具體要求,而是交由各國視本國情況自行界定。“承諾實用性原則”是加拿大法院根據本國實踐對實用性標準的細化,是遏制“常青”藥品專利、防止不正當延長專利的法律規制方法。倘若該原則被認定違法,則加拿大在《TRIPS協定》下關于可專利性標準的自主政策空間將被不當侵蝕。正因為如此,審理此案的仲裁庭明確指出,加拿大關于可專利性標準的政策選擇權利不容置疑。
需要警惕的是,即便投資者援引投資條約挑戰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的仲裁訴請最終失敗,其仲裁要求對東道國仍可能形成“寒蟬效應”。因為冗長的仲裁程序和高昂的仲裁費用是投資仲裁的兩大痼疾,在一些投資仲裁案件中,當事方耗費的仲裁成本甚至超出了投資者的賠償要求。例如,在“莫里斯訴烏拉圭案”中,莫里斯要求的賠償數額為2 227萬美元,而其為該案耗費的仲裁成本為1 690萬美元,烏拉圭的仲裁費用則為1 030萬美元。〔41〕Supra note 〔7〕, Award, 8 July 2016, para.583.莫里斯不惜支付高昂仲裁費用的目的不僅在于要求烏拉圭賠償損失,更在于迫使烏拉圭修改或放棄控煙立法。就經濟實力而言,莫里斯遠在烏拉圭之上,莫里斯2013年的收入超過800億美元,而烏拉圭同年的GDP僅為557億美元。〔42〕同前注〔35〕,James Gathii、Cynthia Ho 文,第 436 頁。烏拉圭政府曾表示其自身無力承擔巨額仲裁費用,若非仲裁費用得到了第三方資助,其當時可能不得不考慮放棄控煙立法并與莫里斯達成和解。在“吉利德科學公司訴烏克蘭案”中,吉利德科學公司是一家美國生化制藥公司,其在烏克蘭市場銷售一款治療丙型肝炎的專利藥品。由于烏克蘭批準其他制藥公司在烏克蘭研發生產該專利藥品的仿制藥品,于是吉利德科學公司依據美國與烏克蘭BIT對烏克蘭提起投資仲裁,主張烏克蘭侵犯了其專利權投資。〔43〕See Gilead Sciences Inc.v.Ukraine, Settlement Agreement (not public), 25 January 2017.迫于仲裁壓力,烏克蘭與吉利德科學公司達成了和解協議,吉利德科學公司撤回了仲裁請求。〔44〕See Luke Eric Peterson & Zoe Williams, Pharma Corp Withdraw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fter Ukraine Government Agrees to Settlement of Dispute over Monopoly Rights to Market Anti-viral Drug,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 16 March 2017.由此可見,龐大的仲裁成本對于缺乏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不堪重負的,而投資者的濫訴行為、仲裁威脅策略也可能對這些國家構成強大的威懾效果,迫使他們主動修改或放棄原定的知識產權政策。〔45〕事實上,國家為了避免訴累而調整或放棄投資管制措施的事例并不鮮見。例如,肯尼亞等國由于受到外國煙草商的訴訟及仲裁威脅而對控煙立法猶豫不決。See Cynthia M.Ho, A Collision Between TRIPS Flexibilities and Investor-State Proceedings, UC Irvine Law Review, Vol.6, 2016, p.411.
(二)投資仲裁庭的裁判權有限
投資仲裁是投資條約下的爭端解決機制,投資仲裁庭僅對投資條約所涵蓋的“投資”“投資者”“投資爭端”具有管轄權。而且,投資仲裁庭僅可就投資損害賠償事宜作出裁判,無權要求敗訴的東道國修改或取消其涉案措施。
首先,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應為投資條約所涵蓋、具備投資特征且為東道國法律所認可。投資條約所涵蓋的知識產權類型并不當然構成條約所保護的“投資”,僅當該知識產權被用于投資目的,具備資產投入、風險承擔、收益預期等特征時才可能成為投資條約的保護對象。而且,由于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知識產權僅在授予或確認其權利的國家產生并僅在該國范圍內受到法律保護,所以東道國法律不予認可的知識產權類型將無法獲得知識產權,故而也就無法作為“投資”受到投資條約的保護。
其次,作為“投資者”的知識產權人應為符合投資條約國籍要求的自然人或法人。實踐中,投資者在境外投資時往往會考慮國籍籌劃方案,通過在第三國設立中間公司獲得特定的國籍身份,從而享受東道國與第三國之間投資條約的保護。〔46〕參見黃世席:《國際投資仲裁中的挑選條約問題》,《法學》2014年第1期。投資者的這種國籍籌劃行為也被稱為“挑選條約”或“選購條約”。當然,國籍籌劃并非毫無限制。若投資者在投資爭端發生后或在能夠合理預見投資爭端時才決定重組投資、改變其投資國籍的,則其國籍籌劃行為將構成濫用程序,無法獲得目標投資條約的保護。譬如,在“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中,莫里斯為了獲得中國香港與澳大利亞BIT及其仲裁機制的保護,決定重組其投資,由注冊地在中國香港的中間公司介入并對澳大利亞提起仲裁。然而,仲裁庭指出,莫里斯在進行國籍籌劃時已經能夠合理地預見澳大利亞的控煙立法,其與澳大利亞的投資爭端已經具體化,故其通過國籍籌劃提起的投資仲裁程序構成濫用權利。
再次,作為“投資爭端”的知識產權爭端應為關于投資條約權利義務的爭端。投資者不得援引非投資條約下的權利義務對東道國提起投資仲裁。盡管投資條約通過投資待遇條款引入了知識產權條約規則,但投資仲裁庭并不因此獲得對知識產權條約爭端的管轄權。知識產權條約項下的解釋和適用爭端仍應通過知識產權條約爭端解決機制予以解決。有關《TRIPS協定》的解釋和適用爭端由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屬管轄,投資仲裁庭無權對《TRIPS協定》的權利義務爭端進行裁判。根據WTO《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23條的規定,對違反WTO協定的救濟只能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成員方不得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外尋求執行WTO法。〔47〕See Simon Klopschinski, The WTOs DSU Article 23 as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Systemic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the Light of TRIP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9, 2016, pp.211-239.投資仲裁不得成為執行WTO協定的法律工具。例如,在“美國《1998年綜合撥款法案》第211節爭端案”中,WTO上訴機構即指出,與《TRIPS協定》 的相符性問題應由上訴機構裁定。〔48〕See United States-Section 211 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 of 1998, WT/DS176/AB/R, paras.362-362.當然,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3)(c)條的規定,投資仲裁庭在解釋投資條約中的知識產權條款時應當考慮“適用于條約當事國間關系的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其中即包括《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但是,投資仲裁庭對知識產權條約的“考慮”僅限于解釋投資條約的目的,并不能賦予仲裁庭對知識產權條約爭端的管轄權。
然而,在實踐中,知識產權人常常會借助于投資條約中的保護傘條款、公平公正待遇條款和征收條款來質疑東道國知識產權措施與知識產權條約的相符性。〔49〕同前注〔31〕,Henning Grosse Ruse-Khan文,第 250頁。就保護傘條款而言,投資者認為條款中“任何承諾”的表述涵蓋了東道國在知識產權條約下的任何義務,這些義務可通過投資仲裁機制予以執行。就公平公正待遇條款而言,投資者主張其有權期待東道國遵守知識產權條約并保持本國法律體系的穩定性。對于此,“莫里斯訴烏拉圭案”的仲裁庭指出,保護傘條款僅要求東道國遵守其對投資者作出的特定的、具體的承諾。普遍實施的立法、授予或確認知識產權均不構成保護傘條款下的承諾,除非東道國已對投資者作出特定承諾,否則投資者不應該期待東道國的法律僵化不變。而公平公正待遇條款也不應成為凍結東道國法律、限制東道國規制主權的借口。因此,知識產權人無權以保護傘條款、公平公正待遇條款為由要求仲裁庭審查東道國措施與知識產權條約的相符性。就征收條款而言,不少投資條約規定其征收條款不適用于與《TRIPS協定》相符的撤銷、限制或創設知識產權的行為或知識產權強制許可行為。該規定本意在于確保《TRIPS協定》的彈性機制和例外條款不受投資條約征收條款的減損,也讓投資仲裁庭因此有機會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以判斷東道國措施是否與《TRIPS協定》“相符”,這可能導致投資仲裁庭與WTO爭端解決機構在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上的沖突。事實上,在莫里斯公司對澳大利亞提起投資仲裁請求之后,烏克蘭、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古巴、印度尼西亞等國也先后啟動了WTO爭端解決程序,主張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法案違反了《TRIPS協定》。〔50〕See Australia-Tobacco Plain Packaging, WT/DS435, WT/DS441, WT/DS458, WT/DS467, Panel Reports, 19 July 2018.如果投資仲裁庭與WTO爭端解決機構對澳大利亞是否違反《TRIPS協定》 得出不同的結論,無疑將引發投資條約機制與WTO機制的沖突。
最后,投資仲裁庭僅可裁定金錢損害賠償,不得裁定懲罰性賠償或要求東道國取消或修改涉案的立法、司法或行政措施。WTO協定涉及國家間的整體義務,而投資條約涉及國家對私人的個體保護義務,所以兩者在救濟方式上是有差異的。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救濟形式主要表現為履約要求而非提供賠償,而多數投資條約規定投資仲裁庭僅能裁決金錢損害賠償,因此仲裁庭無權推翻或廢除東道國的涉案措施。即便是投資仲裁庭認定東道國的涉案措施與投資條約不相符,只要東道國作出相應的投資損害賠償即可,無需修改或取消其涉案措施。盡管如此,投資仲裁程序對東道國政策選擇的負面影響仍不容小覷:其一,投資仲裁庭在裁定東道國損害賠償責任的同時,也將給東道國涉案措施貼上“違法”的標簽,此舉將會降低東道國的國際聲譽。其二,東道國涉案措施的“違法”標簽可能激勵更多的投資者發起投資仲裁程序,從而抬高東道國的仲裁成本,影響東道國的政策選擇。
四、國際投資條約對知識產權保護困境的應對方案
當前,國際投資條約已成為發達國家繞開WTO多邊體制輸出高標準知識產權規則的重要工具。國際投資條約將知識產權納入“投資”范疇,通過投資待遇條款引入和強化知識產權規則,并授權知識產權人運用ISDS機制對東道國提起投資仲裁程序。“莫里斯案”“禮來訴加拿大案”的赫然聳現,都表明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政策正招致來自知識產權人的投資仲裁威脅。在此背景下,對國際投資條約下知識產權保護的邊界予以明確,以確保東道國知識產權政策的自主空間不受國際投資條約及其仲裁機制的不當侵蝕必要且急迫。
于我國而言,慮及國際投資結構的變遷以及對外開放戰略的穩步推進,在國際投資條約的知識產權議題上,既要確保建立和維持適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要為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政策預留出自主空間,從而實現私權保護與社會福祉之間的平衡。具體而言,我們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投資條約內容及投資仲裁機制做出調整和改革,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爭端。
(一)明確知識產權“投資”“投資者”“投資爭端”的范圍
防止知識產權人濫用投資條約及投資仲裁機制需先明確界定投資條約下有關知識產權“投資”“投資者”“投資爭端”的范圍。對于“投資”,投資條約應明確知識產權作為投資形式的前提條件,避免仲裁庭任意擴大知識產權“投資”的范圍。例如,作為“投資”的知識產權須依據東道國法律授予或確認,而且獲得或持有知識產權本身不構成投資。對于“投資者”,投資條約應明確排除對權利濫用者的保護。若知識產權人在投資爭端已發生或能夠合理預見投資爭端時進行國籍籌劃,則其不得以新的國籍身份主張投資條約及投資仲裁機制的保護。對于“投資爭端”,投資條約可通過正面清單或負面清單方式限制知識產權爭端的可仲裁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提交投資仲裁的知識產權爭端須限于投資條約下的爭端;另一方面,可排除特定類型爭端的可仲裁性,如TPP第29.5條對允許締約國排除有關煙草控制措施訴請的可仲裁性進行了規定。對于被排除可仲裁性的知識產權爭端仍可訴諸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
(二)完善涉及知識產權的投資待遇條款,并設置條約例外
知識產權人訴諸投資仲裁的目的在于執行投資待遇條款。投資待遇條款的表述越模糊、越寬泛,則知識產權人濫用投資條約及投資仲裁機制的空間也就越大。因此,投資條約須明確投資待遇條款適用于知識產權訴請的情形、條件、程序和效果,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為締約國的知識產權政策預留合理的空間。
為了避免仲裁庭直接以知識產權條約作為判斷投資待遇的依據,可考慮在投資條約中設置相應的“脫鉤”條款。具體而言,投資條約在與知識產權條約“掛鉤”的同時,也要明確違反知識產權條約并不自動構成對投資條約的違反。例如,根據《歐盟與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CETA)第8.12條第6款的規定,認定成員方撤銷、限制或創設知識產權的措施與《TRIPS協定》或CETA知識產權章節不相符并不意味著存在征收。〔51〕歐盟與新加坡投資保護協定的附件三“征收與知識產權”中亦有類似之規定。TPP雖未明確將征收條款與知識產權條約“脫鉤”,但其附件9-B對征收的認定進行了排除性規定:除極少數情況外,一締約方旨在并用于保護公共健康、安全、環境等合法公共福利目標的非歧視性管制措施不構成間接征收。TPP在其注釋中對公共健康的管制措施進行了詳細列舉,包括但不限于與藥物、診斷方法、疫苗、醫療設備、基因療法和技術、健康援助和器械以及血液和血液制品的監管、定價、供應和報銷有關的措施。CETA第8.10條第6款還規定,違反本協定其他條款或違反任何其他協定,并不構成對本條款(公平公正待遇條款)的違反。〔52〕參見歐盟與新加坡投資保護協定的第2.4條第7款、歐盟與越南自由貿易協定的投資章第2節第14.6條、TPP第9.6條第3款中亦有類似之規定。這些規定雖不能完全排除知識產權訴請,但其意義在于防止仲裁庭以知識產權條約為依據直接判斷投資待遇的相符性。〔53〕See Bryan Mercurio, Safeguarding Public Welf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ealth and the Evolution of Treaty Draft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6, 2015, pp.262-263.除“脫鉤”條款外,締約國還可采取如下備選方案——將投資待遇與東道國法律(而非知識產權條約)進行“掛鉤”。例如,印度2015年BIT范本第2.6條規定,投資條約不適用于“與東道國法律相符的”知識產權強制許可行為或撤銷、限制或創設知識產權行為。該規定同樣能夠避免仲裁庭以知識產權條約為依據認定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措施是否符合投資待遇義務。與此同時,投資條約還應納入和細化例外條款,允許締約國為了公眾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等社會福祉限制知識產權的投資待遇。在限制知識產權待遇方面,有一般例外和知識產權例外兩種形式。一般例外是就投資條約整體設置的例外,可適用于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所有投資訴請。知識產權例外則僅就知識產權事項設置投資待遇義務的例外。就一般例外而言,一些投資條約借鑒《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第20條設置了一般性例外條款,允許東道國基于公共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等合法公共目標豁免投資待遇義務。例如,中國與加拿大BIT第33條、中國與東盟投資協議第16條規定,本協定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阻止締約方采取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或健康、保護可用盡的自然資源等目的所必需的措施。就知識產權例外而言,投資條約可針對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征收條款、履行要求條款等條約義務設置知識產權專項例外。例如,中國與加拿大BIT第8條第4款規定,就知識產權而言,一締約方可按照締約雙方均為成員的知識產權條約的規定,背離本協定第3條(投資準入)、第5條(最惠國待遇)和第6條(國民待遇)。
(三)改革投資仲裁程序,提升投資仲裁的公信力
當前的投資仲裁制度存在程序設計、解釋偏好、裁決結果等方面的內在缺陷。〔54〕See Peter K.Yu, The Investment-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66,2017, p.829.對投資仲裁制度的改革應以防范知識產權人濫訴、限制仲裁庭裁量權、平衡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家管制主權為原則,從仲裁程序的啟動條件、仲裁訴請的審查程序、仲裁裁決的糾錯機制等方面著手進行改革。〔55〕參見徐樹:《國際投資仲裁中濫訴防范機制的構建》,《法學》2017年第5期。在仲裁程序的啟動環節,可設置友好磋商、當地救濟、仲裁通知、仲裁時效等仲裁前置條件,將其作為締約國同意仲裁的先決條件。而且,締約國可明確禁止知識產權人通過“挑選法院”“挑選條約”等策略在不同平臺挑戰東道國的知識產權政策。若投資者將爭議措施訴諸投資仲裁,則投資者不得就爭議措施再行提交其他爭端解決程序。在仲裁訴請的審查環節,為了減輕東道國訴累,應在更早的階段審查和駁回投資者的濫訴請求,可考慮設置締約國的訴請過濾機制以及仲裁庭的快速審查程序。締約國的訴請過濾機制可借鑒一些投資條約中有關稅收訴請之規定,對知識產權訴請設定同樣的審查過濾程序,締約國的審查決定對仲裁庭具有約束力。〔56〕同前注〔35〕,James Gathii、Cynthia Ho 文,第 482 頁。就仲裁庭的快速審查程序而言,可在投資條約中設置特別程序,允許仲裁庭快速駁回知識產權人的濫訴請求,并要求濫訴方承擔對方的仲裁費用。
除此之外,由于特設仲裁、一裁終局、私權導向等“商事化”特征的存在,投資仲裁裁決的不一致性、裁決結果的不可預期性等弊端造成了投資仲裁的“正當性危機”。〔57〕投資仲裁的“正當性危機”表現在多個方面,包括仲裁裁決之間的不一致性、對公共利益的忽視、對投資者利益的偏私等。See Susan D.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aw Review, Vol.73, 2005, pp.1521-1625; Michael Waibel et al.(eds.), 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Perceptions and Realit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為了應對此危機,國際社會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案,大抵可劃分為“漸進模式”“系統改革”“范式轉換”三大陣營。“漸進模式”陣營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其主張投資仲裁仍為最佳方案,對投資仲裁程序僅做出適當調整即可。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CPTPP總體上維持了投資仲裁的程序結構,是此陣營的代表性協定。〔58〕截至目前,已有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墨西哥、新西蘭及新加坡等6國批準了該協定。“系統改革”陣營以歐盟為代表,其認為投資仲裁機制存在根本缺陷,有必要建立投資爭端解決的常設機構,并引入上訴機制。歐盟在與加拿大、越南、新加坡分別簽訂的貿易投資協定中即設置了雙邊上訴機制,創設初審仲裁庭與上訴仲裁庭。而巴西與南非等國則屬“范式轉換”陣營,其完全否定投資者與國家間仲裁機制的合理性,主張通過當地救濟、國家間機制等替代方案來解決投資爭端。〔59〕See Anthea Roberts, Incremental, Systemic and Paradigmatic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2, 2018, p.410.這些改革方案既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投資仲裁在認識上的分歧,也反映出不同陣營對投資仲裁改革路徑的領導權之爭。〔60〕參見王燕:《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的美歐制度之爭》,《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2期。事實上,這些改革方案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取代關系,而是呈現出多元共存的格局。締約國談判的結果可能是不同改革方案的彈性和動態組合,當締約國對上述改革方案難達共識時,可通過選擇性加入或退出、強制磋商等靈活性機制為進一步談判預留空間。
(四)協調投資仲裁機制與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機制
投資條約、知識產權條約對知識產權的競合保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投資仲裁機制與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機制的沖突困境。由于投資條約與《TRIPS協定》等知識產權條約“掛鉤”,因此當一項知識產權訴請同時被提交投資仲裁程序與WTO爭端解決程序,將可能導致投資仲裁庭與WTO爭端解決機構在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上的沖突。為了避免沖突,確有必要在投資條約中加入“銜接條款”,確保WTO爭端解決機構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的優先性。〔61〕近年來,由于美國單方面阻撓WTO上訴機構成員的遴選,使上訴機構面臨“癱瘓”的風險。為了恢復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轉,WTO成員正在積極談判推進WTO改革。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思考是否存在WTO機制之外的其他替代性機制。有學者指出,現行的投資仲裁機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均非解決知識產權投資爭端的理想途徑,并建議設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在具體制度設計方面,其主張國家間機制相比投資者與國家間機制更有優勢和可取性,應借鑒WTO機制建構知識產權投資爭端的國家間解決機制。還有學者建議整合貿易規則與投資規則,將WTO爭端解決機制升級為世界貿易與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應予說明的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以國際社會的政治共識為前提,其改革前景尚不明朗,在達成最終改革方案之前,WTO爭端解決機構仍將是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的首要機構。同前注〔36〕,何艷文;楊國華:《論世界貿易與投資組織的構建》,《武大國際法評論》2018年第1期。“銜接條款”可以表現為剛性要求或彈性安排。就剛性要求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及大韓民國政府關于促進、便利和保護投資的協定》第9條第2款規定,本協定任何規定均不得解釋為減損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方加入的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根據該規定,投資協定下的實體義務和爭端解決機制不得減損《TRIPS協定》下的實體義務和爭端解決機制,當兩者出現沖突時,后者優先。就彈性安排而言,CETA第8.24條對投資仲裁程序與其他爭端解決程序設置了彈性銜接機制。當根據其他國際條約啟動的國際程序與投資仲裁程序存在重復賠償之可能性,或者其他國際程序對投資仲裁訴請的解決有重大影響時,投資仲裁庭應當盡快中止其程序或確保在其裁決中考慮其他國際程序。不過,該規定并未在投資仲裁程序與其他國際程序之間設定嚴格的等級關系,因為投資仲裁程序是否需要中止以及其他程序裁決具有何種效力均由投資仲裁庭自行裁量。
當然,投資仲裁機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在知識產權投資爭端解決上既有競爭性,也有互補性。〔62〕See Brooks E.Allen & Tommaso Soave, Jurisdictional Overlap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30, 2014, pp.7-8.兩者雖涉及相同的東道國知識產權措施,但在爭端主體、訴請基礎、救濟形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一方面,知識產權投資者可依據投資條約提起投資仲裁程序,尋求損害賠償;另一方面,投資者母國也可依據WTO協定啟動爭端解決程序,要求東道國修改其知識產權措施。倘若為了避免兩者沖突而矯枉過正,完全排除投資仲裁庭援引和適用《TRIPS協定》的可能性,結果將使知識產權投資者本應享有的條約權益得不到救濟。所以說,問題不在于投資仲裁庭能否援引《TRIPS協定》,而在于如何實現投資仲裁庭與WTO爭端解決機構在解釋和適用《TRIPS協定》上的一致性與協調性。
故此,在投資仲裁程序與WTO爭端解決程序的銜接機制之外,還要對投資仲裁庭的解釋方法作出明確指引。原則上,投資仲裁庭的管轄范圍僅限于有關投資條約的爭端,而有關《TRIPS協定》的爭端屬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專屬管轄范圍。然而,有限的管轄權并不一定意味著對法律適用范圍的限制。〔63〕參見馬爾蒂·科斯肯涅米:《國際法不成體系問題:國際法多樣化和擴展引起的困難》,國際法委員會研究組報告,A/CN.4/L.682,第 44~45 段。投資仲裁庭雖無權管轄《TRIPS協定》 爭端,但仍可能將協定作為其適用的法律。對此,應當明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釋規則對投資仲裁庭的約束力。根據該公約第31(3)(C)條之規定,仲裁庭在解釋投資條約中涉及知識產權的條款時,僅可考慮適用于當事國間關系的“有關”國際法規則。《TRIPS協定》作為投資條約的“有關”國際法規則,僅可作為解釋材料予以考慮,無法直接成為投資仲裁庭認定東道國措施與投資條約相符性的依據。〔64〕同前注〔47〕,Simon Klopschinski文,第 238~239 頁。投資仲裁庭應當忠實運用體系解釋方法,不得將投資條約作為執行知識產權條約的工具,否則即超越了其作為投資爭端解決機構的職權。
五、結語
在商品、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日益全球化的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已不再是獨立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之外的“孤島”,這也反映到知識產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規則體系中。《TRIPS協定》的達成使知識產權保護步入到了“與貿易有關”的規則時代,而國際投資條約對知識產權議題的廣泛介入,又將知識產權保護帶入“與投資有關”的新領域。此一轉變是知識產權國際立法“體制遷移”不斷延續之產物。〔65〕See Lawrence R.Helfer, Regime Shifting: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New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aking,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9, 2004, p.1.雖然此種遷移引發了國際社會對體制競爭及沖突的擔憂,但同時也加深了對知識產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三者之間關系的理解,推動了知識產權規則體系的融合。〔66〕同前注〔54〕,Peter K.Yu文,第 910頁。知識產權法與貿易法、投資法的“聯姻”促進了相關領域的跨學科對話和相互借鑒,通過案例的積累可進一步明晰知識產權的相關概念、規則和原則,進而引發更多的討論,這也是知識產權國際立法調整的重要動力來源。例如,作為對“禮來訴加拿大案”的回應,歐盟與加拿大FTA第8章附件D申明,投資仲裁庭并非國內法院的上訴機構,知識產權的存在與效力應由國內法院裁決。各成員可自行確定在其法律體系中實施本協定知識產權條款的適當方法。〔67〕同前注〔24〕,Sigfrid Fina、Gabriel M.Lentner文,第 289~300 頁。又如,作為對“莫里斯訴澳大利亞案”的回應,TPP第29.5條允許締約國將煙草控制措施排除在投資仲裁的范圍之外。〔68〕同前注〔53〕,Bryan Mercurio文,第 273~274頁。
可見,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相伴相生,過度保護與拒絕保護均不足取。貿易法、投資法對知識產權議題的擴展不應打破知識產權規則在私權保護與社會福祉之間建立的平衡。就投資條約而言,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維持知識產權規則內嵌的彈性機制和限制條款應為今后發展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