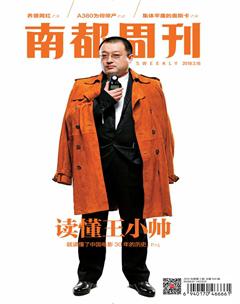皇家林苑開放日,恰是櫻花盛開時
吳鉤

吳鉤
每年的這個時節,櫻花競相綻放,以“三月賞櫻,唯有武大”聞名于世的武漢大學照例又會開放校園,讓游客踏春賞花。從去年的情況來看,四方游人蜂涌而至,出現了一些大煞風景的事情,比如有的游客瘋狂搖動櫻樹,制造所謂的“櫻花雨”;有的游客攀折花木,亂扔垃圾;激增的客流量也會給校園“添堵”,影響學生的日常生活與上課;校方若實行限入制,則勢必會冒出“黃牛”。
困擾之下,有人發問:“武大開辦櫻花節,真的合適嗎?還高校一個寧靜,不好嗎?”也有武大學生在網絡上留言:“櫻花節,對學生來說是櫻花劫!吃早飯現在要排十幾分鐘,坐校車能在車上被堵二十分鐘,早上去上課的路被封了,各種不方便。封校or停課放假,請學校考慮一下:學校獻給游客,我們學生走!”—聽這語氣,有些傲嬌了。真的。
所幸武大校長竇賢康先生很大氣,說:“武大櫻花全國聞名,大家愿意到武大來,武大有責任接納。為盡到這份責任,學校愿意為此承擔每年約600萬元經費。”我真心佩服竇校長這個胸襟。
我平日比較關注宋朝歷史,從武大接納賞櫻游客之舉,很自然地便想到了宋時洛陽的一項可貴風俗:每年暮春時節,洛陽牡丹盛開,各家園林都會打開大門,讓游客入內賞花。
唐宋之時,洛陽還是最負盛名的城市之一,而洛陽最負盛名的東西有兩樣:園林與牡丹。著名詞人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寫過一篇《洛陽名園記》,記述了當時洛陽名園,這些名園多種植有牡丹,特別是天王院花園子,就是一個純粹的牡丹園:“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株)。”
宋時洛陽牡丹的名氣,如果謙稱天下第二,就沒有誰敢稱天下第一,半點不遜今日的武大櫻花。也所以,每至牡丹花開季節,“都人士女傾城往觀,鄉人扶老攜幼,不遠千里”。前往洛陽名園觀牡丹的游人之多,也不比今日前往武大賞櫻之人少。洛陽的名園基本上是私家園林,但園林主人從來不敢將圍起來的春光與鮮花據為己有,而是開放給所有游客欣賞,形成“開園放春”的慣例。
有些園林不但打開大門,還“張幙幄(搭帳篷),列市肆,管弦其中”,允許“四方伎藝舉集”。游園的客人不但可以賞花,還能夠欣賞文藝表演。多美的事啊。所以,“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今日讓武大學生苦惱的游客喧鬧、擁堵等問題,我相信也會出現在宋時的洛陽園林中。但是,沒有一個園主想獨占春色,將賞花的游客趕出門去。
這是唐宋園林的開放傳統。其實,那個時候,連開封的皇家林苑都是定期向市民開放的。生活在清代的京師市民,想都別想進入圓明園游賞,但生活在北宋的人們,在每年的春暖花開時節,卻可以到瓊林苑、金明池等皇家林苑游春,因為每年的農歷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瓊林苑和金明池都要打開大門,縱民游覽,這叫做“開園”、“開池”。
每至開園之時,金明池與瓊林苑內,每一日都是游客如蟻,觀者如堵,“雖風雨亦有游人,略無虛日矣”。當時開封府郊外的鄉村流行一句諺語:“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為什么連村里的老太婆也意氣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入城游皇家林苑唄。
宋時皇家林苑與洛陽名園的開園時間,都是在暮春季節,正好跟今日武大櫻花節同時。不奇怪,因為春暖花開,正是踏青賞花的大好時節,好花堪賞直須賞,莫待花落空看枝。宋人“開園放春”的傳統,也許可以給今日呼吁武大“封園”的朋友提供一點啟迪:不管是牡丹,還是櫻花,都是上蒼一年一度的饋贈,理當與天下人共賞。更何況,公立的大學校園并不是某一群人獨享的禁園,更當與天下人共之。
當然,我也知道,大學校園不同于公園、園林,校園的首要功能是教學,需要寧靜,不受干擾,而賞櫻的游人蜂涌而來,難免會發生種種問題,甚至可能會影響校園秩序。不過,這種種問題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校方可以限制每日入園的人數,增加志愿者維持秩序;有一部分問題則是可以容忍與諒解的(想想宋時皇帝的宮殿都能容忍市井商民喧嘩),比如“吃早飯現在要排十幾分鐘”之類。畢竟,櫻花綻放的時間就那么幾天,很快花就會凋謝,游客也將稀少,校園也會恢復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