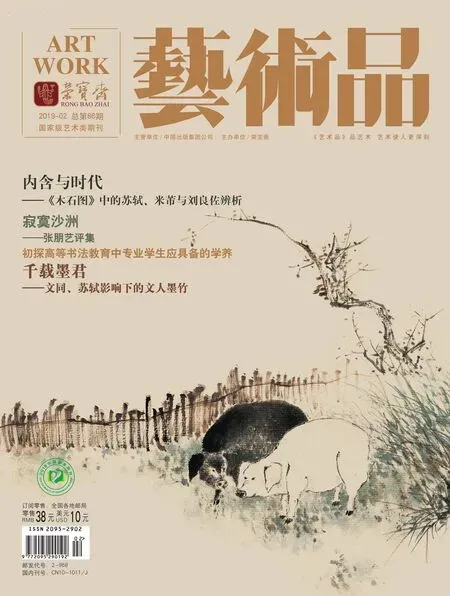吉金叢談·卯簋蓋
文/叢文俊
卯簋,西周中期時器,出土地點不詳,此其蓋銘。銘文記敘了榮伯封賞其家臣“卯”職官、馬牛及土田,卯因以作器。
銘文布局隨蓋形而微圓,前八行行列清楚,秩序井然,后四行則以界格不足其用,遂使文字依其小大而漸次擁擠,而有疏密之變。由此可見,書者事先并未依字數安排界劃,而后面九、十兩行或守界格,或突破之;末二行則全失約束,隨機應變,以此造成通篇游離于繩墨內外,雖迫于事,而能自由生動,頗有可以借鏡者。久味之余,尤令人心馳神往。

卯簋蓋銘拓片

臨《卯簋蓋銘》 68cm×68cm 紙本 2018年

臨《卯簋蓋銘》局部
古人論書,以為肥勁難得,乃據近體為言,若以斯理求之上古吉金,或具體于此銘,則非正道。卯簋非王室作器,書法自然不能盡其楷式,且彼時大篆尚未完全成熟和普及,故不宜以王室典范來論其妍媸。依余觀之,其肥易知,而內涵筋骨,從容紆徐,淡遠之意更在形外,須再三品味始能得其仿佛。同時,結體偏于省略,以及多見不合規范之處;加之變形與偏旁位置移易,給人以既簡且樸,拙而欲工,天淳斯在,眾美斯列,有言所不盡的美感。臨習者若不能盡解個中奧妙,即使形似,亦必神情懸隔,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者殆此。
卯簋蓋銘拓本傳世甚稀,然以拓工精粗有別,裱褙工藝亦或等差,故爾文字結構、書體肥瘦等亦或不同,余之所臨乃肥本,多為學者所據。在肥瘦之外,筆意并無損益。其實,上古金文字小畫細,字口時或漫漶,紙之厚薄,拓之輕重,都會影響到美感風格,只有勘破皮相,才能獲取最佳的臨帖狀態。
臨習卯簋,須仔細審視字形,明解其省簡之理,以及偏旁位置移易等權衡變化之道,這些都是卯簋蓋銘文字的個性所在。次須體味字外之妙,筆短趣長之美,亦即古人所謂“長使意氣有余,畫若不足”的意余于象,可以為人提供足夠引發審美聯想的妙處。第三才是用筆。在反復讀帖之后,“規矩暗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用筆則以沉潛為基調。沉謂沉著,潛謂筆力含收,平淡從容,自然流美。筆不欲遲,遲則軟緩;亦不欲疾,疾則失度;筆不宜重,重則癡滯;亦不欲輕,輕則滑浮。簡言之,以審美所得決定心意,以心意運筆,即使不中,亦不會太遠。
余初臨此銘,曾以經驗運筆,未及其半,即覺神意有虧而不能稱心,遂輟廢。后再讀帖二日,思悟筆法,乃豁然洞開,一氣呵成,如得鬼神之助,縱未臻于上乘,亦不乏可以觀玩者。或謂上古金文,論其一時之作,皆大體相似,舉其一即可反三。余壯時所見近同。及至晚歲心意平淡,體味漸深,遂覺前非。上古作器題銘,即使為一人所作,而以時間、位置、器屬、文字多寡等種種差異,作品之美感風格也會隨之有所變化,唯須明察秋毫乃能知之。至若一時之多人作器題銘,以書制者不同,美感風格自然會各成其妙。清賢稱漢碑一碑一奇,余則謂金文一器一奇,此出于多年研有所得,甘苦之言也。臨習既多,益篤信不疑。

臨《卯簋蓋銘》局部

臨《卯簋蓋銘》局部
上古金文時見銹蝕漫漶的現象,或以字口皆殺而肥,或以剝落而瘦,乃至于殘斷壞缺,都是必須學會正確面對的問題。其一,擇其未殘的部分熟習之,借以推及全篇,以“寫”來改造所有殘泐的筆畫,期之于復原初始狀態;其二,在具備一定基礎之后,順勢而為,就殘泐狀態探索新的美感與風格,要審慎,要循序漸進,并配合以相應的拙、澀、枯、重等用筆方法以實現心中所想;其三,若清、民國時書家所作,以書卷氣改寫,以學養化之。無論怎樣臨習借鑒,都不得染俗,避免作字、畫字、妄改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