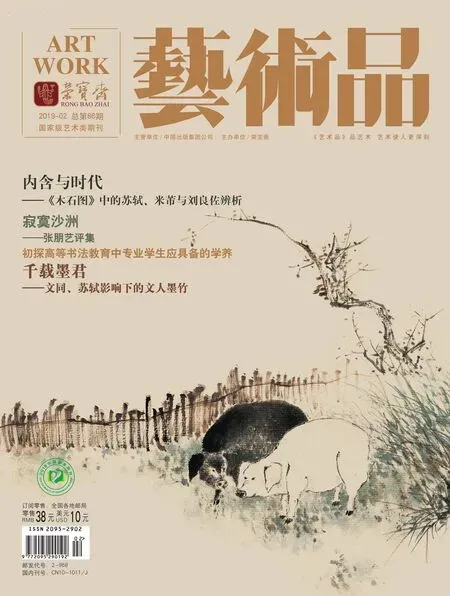容軒讀印—清代流派印(九)
文 /楊 勇
七、晚清其他重要印人—趙之謙、胡钁
篆刻發(fā)展到晚清,盛極一時的浙派已經走向程式化,鄧派在清中期的發(fā)展雖然沒有浙派的陣勢,但鄧石如所倡導的“印從書出”,不僅為吳讓之、徐三庚等鄧派印人指明了方向,也為晚清及近代印壇提供了新的發(fā)展路徑,而乾嘉以來金石的出土、研究與整理,更為印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材料,為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胡钁等人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契機。
(一)印外求印的趙之謙
趙之謙(1829—1884),字益甫,號冷君,后更字撝叔,號悲盦,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工詩詞,善文章,精于考證,擅長書法篆刻,成就卓越。在晚清藝術史上,趙之謙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藝術家之一。在繪畫上,他是“海上畫派”的先驅人物,其開創(chuàng)的金石畫風對近代寫意花卉的發(fā)展影響巨大;在書法上,其在楷、行、篆、隸諸體上真正全面學碑,最終形成魏碑體書風,成為清代碑學理論最有力的實踐者;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廣為取法,融會貫通,以“印外求印”的創(chuàng)作理念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了鄧石如倡導的“印從書出”的創(chuàng)作模式,開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著有《六朝別字記》《悲盦居士文存》《二金蝶堂印存》等。
趙之謙篆刻初從“浙派”入手,后又轉師“鄧派”。趙之謙約在34歲左右,便“一心開辟道路,打開新局”,以戰(zhàn)國貨幣、秦漢碑刻、詔版、鏡銘等入印,并融會貫通,自成面貌。趙之謙是“印外求印”的典范,曾聲稱“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松江樹鏞考藏印記”邊款),其通過辛勤探索,終于突破了前人的藩籬,尤其是在浙、鄧兩派之后使篆刻有了新的發(fā)展。盡管趙之謙一生刻印不到四百方,但其無疑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巔峰,影響了后來的吳昌碩、黃士陵、趙叔儒、易大廠等。
趙之謙篆刻的成就,離不開其友魏稼孫的促動。趙之謙不輕易奏刀,魏稼孫便以激將法促使其刻印。在趙之謙34歲時,魏稼孫提出為其集《二金蝶堂印譜》,趙之謙大批量的篆刻創(chuàng)作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至趙之謙36歲時完成印譜。三年中,趙之謙為魏稼孫刻印二十多方,為胡澍刻印近二十方,為沈均初刻三十余方,加上自用印及為其他好友所刻之印,三年刻印共計二百余方,占趙之謙一生所刻印章的一半。此外,魏稼孫編《二金蝶堂印譜》,請吳讓之作序,吳讓之在序中云:“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辭耶。”趙之謙以為吳對自己的評價并不如想象那么高,僅稱自己“已入完翁室”,這對趙之謙來說恐怕是個不小的刺激。趙之謙這一時期大批量的印作,直接原因是為補充《二金蝶堂印譜》,另一原因,應是篆刻前輩吳讓之的存在和刺激。
趙之謙在為魏稼孫刻“魏錫曾”“稼孫”對章時,邊款曰:“稼孫目予印為在丁、黃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黃之上。”又在“趙之謙印”邊款中云:“龍泓無此安詳,完白無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趙之謙印”邊款中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趙之謙在致友人函中說:“弟在三十前后,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以后一心開辟道路,打開新局。”這種俯瞰千古、不服輸的氣度,應該說與魏稼孫的刺激不無關系,而為趙之謙編印譜又是個關鍵性的契機。
趙之謙是一位才情橫溢的藝術家,其治印并不把篆字局限于古印,還從其他任何有關篆字的古代遺跡中吸取營養(yǎng)。正如胡澍為其印譜所寫的序中所言:“竊嘗論之,刻印之文,導原篆籀……如漢魏碑版、六朝題記,以及泉貨、瓦磚,措畫布白,自然入妙,茍能會通,道均一貫。”“茍能會通,道均一貫”八字從文字的淵源流脈處,闡述其可能性,贊賞了趙之謙實踐的可貴之處。趙之謙摹古而不泥古,求新而不取寵,其篆刻立異標新,往往出人意表。在歷代印人中,趙之謙的篆刻風格多樣,給后來之黃士陵、齊白石以至關重要的出新契機。例如,趙之謙首創(chuàng)單刀直沖的猛利刀法,刻了一枚白文印“丁文蔚”,鋒穎逼人,開啟了齊白石大刀闊斧印風的先河。又如,趙之謙以干凈利落的線條鐫刻的“靈壽花館”,成了黃士陵在平板中寓機巧的先河。
(二)熔秦鑄漢胡匊鄰
除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三人外,胡匊鄰也是晚清印壇成就比較突出的一位。胡钁(1840—1910),字匊鄰,號老鞠、不枯、晚翠亭長、竹外外史,晚年又號南湖寄漁,別署不波生、葆光亭主人,書畫作品多落晚翠款。浙江石門(今桐鄉(xiāng))人。善書畫篆刻,亦工詩詞。書法初學虞世南、柳公權,后致力于漢魏碑版,古拙遒勁,頗見功力。山水峰巒渾厚,筆墨蒼茫;蘭菊亦娟逸有致。善治印, 工刻竹,治印名聲和吳昌碩相媲美,雖蒼老不及而秀雅過之,刻竹極精,所刻扇骨技藝亦不下于蔡照。亦擅石刻,曾為鑒湖女俠秋瑾墓刻碑。著有《晚翠亭詩稿》《不波小泊吟草》,又有《晚翠亭藏印》《晚翠亭印存》等。
胡匊鄰篆刻受趙之謙影響,更得力于漢玉印、磚文、詔版等,疏密變化自然有致,白文印尤有特色。胡匊鄰的篆刻,以質樸、自然、清朗、渾穆的特點感人至深,毫無怪異、新奇、夸張、斑駁之處,有一種寓清遠于平淡的大巧若拙的韻味。20世紀50年代初,上海宣和印社曾出版《晚清四大家印譜》,選集吳熙載、趙之謙、吳昌碩、胡钁四家作品。高野候在《晚清四大家印譜》中認為:“匊鄰專摹秦漢,渾樸妍雅。功力之深,實無其匹。宋、元以下各派,絕不擾其胸次。”方去疾先生曾在《明清篆刻流派簡述》一文中,對胡氏的篆刻作了確切、深刻的評價:“胡钁的篆刻得力于玉印、鑿印、詔版,細白文的成就很高。轉折如曲鐵,錯落有致,看似草率從事,若非苦心經營,何能臻此?他處理筆畫懸殊的印文,更能體現其功力深厚。”
清代金石學的興盛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空前繁榮。一是學習和研究資源的拓展,不斷出土的碑版、鐘鼎、封泥等金石文物為清代印風的成熟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二是由于金石學帶來了古文字學的復興,出現了大量的篆書大家,如鄧石如、吳讓之、吳昌碩、徐三庚、趙之謙等開宗立派的篆刻大師,促使清代中后期篆刻流派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
近代印壇,實際上是趙之謙印風與吳昌碩所創(chuàng)的“海派”、黃士陵所創(chuàng)的“黟山派”三分天下。師法趙之謙者有王爾度、錢君匋等;師法吳昌碩者有徐新周、趙云壑、陳師曾、趙古泥等;師法黃士陵者有李尹桑、鄧爾疋、喬大壯等。與此同時,浙派在“西泠后四家”之后也有新的印人群體涌現,尤其是“西泠印社”的成立,影響更為深遠。


趙之謙朱文“賜蘭堂”
“賜蘭堂”是趙之謙為晚清潘祖蔭所刻。潘祖蔭(1830—1890),字在鍾,小字鳳笙,號伯寅,亦號少棠、鄭盦,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數掌文衡殿試,在南書房近四十年。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通經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政務之外,潘祖蔭以金石考藏有名于時。
趙之謙到京師謀取官職,得潘資助百金,直到 44歲時謀到《江西通志》總編之職,后任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此印邊款有“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之語,是趙之謙有紀年印章之最晚者。光緒八年(1882),潘祖蔭得到慈禧太后特賜御筆蘭花,特以“賜蘭堂”名其齋室,請趙之謙刻此印。趙在邊款中特為注明:“皇太后特頒天藻,以志殊榮,敬勒斯石。”可見刻此印時是非常鄭重的,此印左右各盤一龍,姿態(tài)飛揚。趙之謙妙于運思,此印莊重大氣,刀法渾厚暢達,廟堂之氣躍然紙上。


趙之謙朱文“靈壽花館”
此印趙之謙未署款,后為張魯庵所得,其師趙叔孺鑒為趙之謙所刻,并刻觀款于石側。“靈壽花館”是沈樹鏞的齋號,沈乃趙之謙的摯友,曾得趙刻印30余方,幾近趙之謙治印總數之十分之一,可見二人友誼之深厚。此朱文印用字既非小篆,也不似繆篆,而有戰(zhàn)國貨幣文字之意趣。趙之謙的篆刻取法廣博,其朱文印優(yōu)美雅正,開“新浙派”之源,后世王福廠、韓登安一系鐵線篆,是從趙之謙印風格發(fā)展而成的,趙之謙是一位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大家。
此印“花”字六條斜線出乎意料,其他三字則橫平豎直,四個字筆畫互相穿插搭接,緊緊相依,但因為空間分割奇妙,所以貌似刻板實則暗含靈動,這種以直挺光潔的線條巧妙分割空間的做法直接影響了黃士陵,黃士陵將這種風格發(fā)揚光大,并形成了“黟山派”。

趙之謙白文“巨鹿魏氏”
此印作于同治三年(1864),乃趙之謙在京城赴考時為魏錫曾所刻。魏雖不刻印,卻篤好集古,匯輯印譜,有“印奴”之稱。魏錫曾對印學有精辟見解,曾作論印詩24首,評論明清以來各家篆刻。趙之謙與他經常討論印學,為他刻印也刻意求新。
此印四字中雖有“十”字界格,章法上卻不等分空間,四字緊緊相連。趙之謙不僅在印面上發(fā)揮其聰明才智,在邊款上也作了前無古人的重大探索。魏碑邊款,朱文邊款,以至山水、人物、走獸都用以入款。由于趙之謙在邊款上傾注的心力,使原本被印人多有忽視的邊款,由不起眼的附庸身份而升騰到具有相對獨立性、表現力的地位。此印四周有趙之謙自作的論印詩,其中“古印有筆尤有墨,今人但知刀與石。此意非我無能傳,此理舍君誰可言”兩句,既是趙之謙對此印的自賞,也是對當時平庸印人的批評,對一百五十多年后的當下印人仍是一種警醒。



趙之謙“臣何澂”“竟山”對章
此印材質為白芙蓉石,印面均為縱22毫米,橫22毫米,印石高37毫米。邊款分別為“刻意追橅,期于免俗,撝叔爲鏡山制”“漢鏡多借‘竟’字,取其省也,既就簡并仿佛象之,撝叔”。此對章朱白二印,氣象典正,見刀見筆,乃趙之謙為何澂所刻自用印。何澂(1834—1888),字竟山、鏡山,號瑀伯、心伯、傳洙。山陰(浙江紹興)人。齋堂為思古齋。約活動于清咸豐、光緒年間。深于金石之學,能詩,工篆刻,善花卉。與同郡趙之謙、秀水蒲華為書畫友。



趙之謙朱文“為五斗米折腰”
此印印材為普通青田石,印面縱48毫米,橫48毫米,印石高53毫米。印頂邊款為:“撝叔戲反陶彭澤語以自況。”關于印頂邊款的真?zhèn)危X君匋在《趙之謙刻印辨?zhèn)巍贰ⅠR國權在《趙之謙及其藝術》中均認為印頂邊款是后人仿趙氏邊款風格補刻上去的,小林斗庵在《中國篆刻叢刊·趙之謙》中則以為邊款存疑。印側長款為唐醉石補刻,內容為:“悲翁嘗與長洲江弢叔湜、會稽丁藍叔文蔚游東甌,文采風流,金石照耀,時稱三叔。然悲翁治印,于邑極少流傳,蓋其兀傲之性,不屑為人,非真知篤好,或斬不與也。節(jié)廠三兄寢饋金石,為邑中后起,于海上得悲翁刻印數十方,足補其鄉(xiāng)文獻之,豈獨資后學師事而已。己丑正月,醉石記。人字下脫作字,之字下脫闕。” 此印取法吳讓之,結體疏朗奇逸橫生,一些線條似斷還連,手法極為細膩,有跌宕起伏的節(jié)奏感。


胡匊鄰朱文“晚翠亭長”
此印當是仿漢朱文之作,線條盡可能橫平豎直,轉折處有時故作殘斷,更顯遒勁。筆畫的粗細變化大致為四周略粗,而近中心略細,恰如銅印磨損后的效果。邊款為“新構晚翠亭,匊鄰因制是印”,可見作者刻此印時欣然自喜的心情。胡匊鄰所處的時代,篆刻家大多受到浙派或皖派印風的牢籠,要從中突圍并形成自己的風格確非易事,胡匊鄰上追秦漢,極力擺脫時風,所做朱文印古樸凝練,刀過之處,斑剝任其自然,極少修飾。在章法上,此印寓疏落于茂密之中,極耐品味。


胡匊鄰白文“玉芝堂”
此印為胡匊鄰細白文印代表作,邊款云:“曾見古玉印色澤甚佳,文曰‘玉芝堂’,頗有漢刻意,惜無紐,未得。今卜居郡中,背模其文,即以名吾室。”雖說是“背模”漢玉印,卻在漢玉印的整飭工穩(wěn)中加入了隨意恣肆的趣味,在總體工穩(wěn)的基調中有了細節(jié)的變化。胡匊鄰刻此印時已68歲,風格已非常成熟。此印印面碩大而印文疏簡,全印不施漢玉印中常用的弧筆,而是借鑒了秦詔版峭拔硬朗的筆勢,全印沖刀酣暢穩(wěn)健,線條清剛峻爽,直角轉折處刀角多沖出線外,增添了鑿刻的意趣。此印得益于漢玉印、鑿印、詔版等,章法在疏落中有緊湊,得自然之趣。



胡匊鄰白文“烏程龐氏娛園收藏印”
此印材質為青田石,印面縱27毫米,橫27毫米,印石高50毫米。邊款為:“萊翁收藏既富且精,匊鄰樂為制印。”龐元濟(1864—1949),字萊臣,號虛齋,浙江吳興南潯人。其父龐云鏳為南潯巨富。龐元濟既有財力,又精于鑒賞,收藏有銅器、瓷器、書畫、玉器等文物,尤以書畫最精,與于右任、張大千、吳昌碩等人均有交往。
此印筆畫清健瘦硬,結體也隨文字的繁簡而加以自然安排。雖以界格分字,并不顯板滯。胡匊鄰致力于將兩漢鑄印、玉印和秦詔版經過提純精練,使印作表現出純正雅潔、清朗明凈的風格,而白文印也代表了胡篆匊鄰刻藝術的最高成就。



胡匊鄰白文“無任主臣”
此印材質為黃芙蓉石,印面縱19毫米,橫19毫米,印石高48毫米。邊款為:“仲恕詞兄正之,胡钁。”陳漢第(1874—1949),字仲恕,號伏廬,室名千印齋(因藏印近千而名),浙江杭州人。清季翰林,清史館編纂,晚年寓居上海。擅寫花卉及枯木竹石,尤善畫竹。藏印頗富,有《伏廬印存》。胡匊鄰治印,刀法挺秀,運刀穩(wěn)健,故線條雖細但勁挺有力。其印很少粗壯的滿白文,常見的是遒勁清逸的細白文。此印布局自然工整,用刀勁健,為胡匊鄰白文印典型風格。



胡匊鄰白文“硬黃一卷寫蘭亭”
陸游《山居戲題》中有“嫩白半甌嘗日鑄,硬黃一卷學蘭亭”詩句,此印改陸游詩句一字,并稱是仿漢鑄印,現藏上海博物館。
此印刀法敦厚,鋒芒不顯,故筆畫圓融而瘦勁,如渾金璞玉,將漢鑄印、鑿印、玉印等風格熔于一爐。章法以疏朗自然為主,古穆寧靜。此印四周刻《蘭亭序》全文324 字,胡匊鄰款文精致秀雅,在同時代印人中別樹一幟,所以求刻者特地請他用切刀法摹刻翁方綱縮本《蘭亭序》。印頂有胡匊鄰摹刻吳徵所繪《蘭亭修稧圖》,胡匊鄰是刻竹、刻硯高手,故能將此圖刻得如此精到,使作品具有多元的欣賞要素,也展現了其兼擅多能的藝術涵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