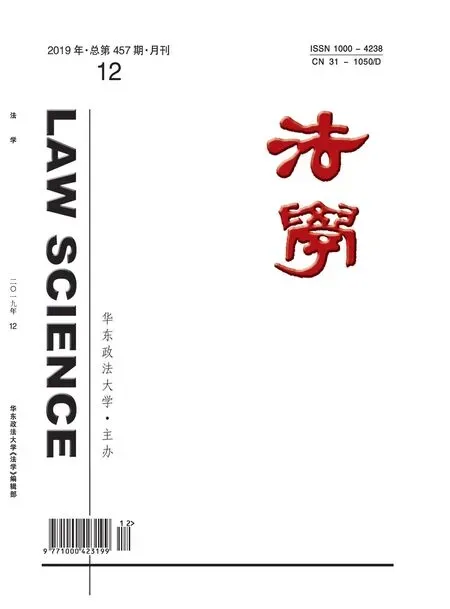能源體制革命抉擇能源法律革命
●肖國興
《能源法》〔1〕《能源法》絕對是“重點領域立法”,立法先后列入《能源發(fā)展“十二五”規(guī)劃》《能源發(fā)展行動計劃2014—2020》《能源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甚至成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所提能源革命的實現(xiàn)路徑。立法工作已十年有余,迄今依然是中國人的夢想。在《能源法》立法出現(xiàn)“制度時滯”的同時,其他能源立法隔靴搔癢式的修訂又常成為能源法制度演化中的笑柄。能源立法與能源體制的掣肘一直是能源法律制度創(chuàng)新的羈絆,無論是能源立法的進程,還是行政部門的立法權,抑或能源央企在能源立法中的“話語權”,能源立法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異化現(xiàn)象都映射出能源體制對能源法制的牽制。
政黨政治有關深化電力體制、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時間表與路線圖及其肇始的能源體制革命為能源法律革命帶來了希望,〔2〕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規(guī)劃了深化體制改革的時間表與路線圖。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建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的能源體制改革目標。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9號文《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2017年15號文《關于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再次為能源體制革命規(guī)劃了具體措施。只可惜法律人僅從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思維出發(fā)去判斷法律制度自身演化的時序與進程,卻并未能從政黨政治中看出能源法律革命的機遇。
能源體制是社會結構的縮影,社會結構是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與行政結構的整合,從直接決定性來看,能源體制至少是產業(yè)組織與行政組織的整合,雖然行政體制在其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但是能源體制絕非行政體制。〔3〕財政是銜接政治體系、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這三個社會子系統(tǒng)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體制改革以財政為主線。參見[日]神野直彥:《體制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王美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政治體制、行政體制與市場體制或者政治結構、權力結構與產權結構都匯集在能源體制中。只因為如此,能源體制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種,能源法律革命是能源體制革命的必然要求并構成其組成部分。
筆者認為,能源體制革命是權力革命,更是產權革命或市場革命,因為能源發(fā)展歸根結底決定于產權與市場功能的發(fā)揮。權力結構決定市場結構、產權結構、資本結構、企業(yè)或產業(yè)結構。能源體制革命引領能源法律革命,能源法律革命只有成為能源體制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才有希望,當然能源體制革命也將依賴于能源法律革命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一、制度內核:組織結構決定規(guī)則結構
從制度是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一種要素,到制度是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唯一要素,從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fā)展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到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fā)展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制度在經濟增長與發(fā)展中的作用被演化到極致。〔4〕劉易斯認為,資源、資本、勞動、技術、制度等五大要素都決定著經濟增長。(參見[英]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梁小民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7頁。)諾思則認為,真正直接決定經濟增長和發(fā)展的是制度,因為其他要素都是制度要素。(參見[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遷》,陳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9頁。)羅蘭認為,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xiàn)很強的相關性,但尚不能確定一定是制度導致了經濟增長。([比]熱諾爾·羅蘭:《發(fā)展經濟學》,金志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頁。)阿西莫格魯認為,制度績效直接決定經濟增長。([美]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A.羅賓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李增剛譯,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249頁。)盡管有人依然鼓噪技術是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源泉,但也不得不承認決定技術進步與否的是不斷改變的社會組織制度。〔5〕參見[美]理查德·R.納爾森:《經濟增長的源泉》,湯光華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很顯然,制度作為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內生變量或外生變量已成學界共識。
(一)制度是“組織+規(guī)則”的行為結構
制度是行動指南、選擇集合、交往結構,〔6〕參見[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wèi)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制度之所以有這樣的作用,就在于制度本身是分散者通用的行為準則,而分散者通用的規(guī)則正是組織的規(guī)則,只有在組織的行為框架內才會有規(guī)則存在與適用之可能。實際上,制度從來不是單個人的規(guī)則,而是人的集合體或者共同體組織的規(guī)則,集體行動正是通過組織來實現(xiàn)的。制度其實就是集體行動的邏輯,正如阿夫納·格雷夫所言:“與制度相對應,組織是由特定人組成的,這些個人通過一定程度上的協(xié)調行為來實現(xiàn)他們亦公亦私的目標。由于個人在組織中追求的是共同目標,并且組織是典型的由重復互動的個體組成,因此大部分組織中成員對于其他成員的行為以及組織規(guī)范與規(guī)則有著共同的信念。這樣許多組織形成了自己的內部制度結構:規(guī)則、規(guī)范。”〔7〕[美]阿夫納·格雷夫:《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鄭江淮等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頁。
制度由“組織+規(guī)則”構成,規(guī)則是組織的規(guī)則,組織是規(guī)則的組織,組織讓規(guī)則有確定的歸屬對象。實際上,規(guī)則的主體不是一切不特定主體,而是特定某類組織體或行為體。組織是制度研究的起點,無論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競爭的經濟、法律與政治維度,市場層級制,還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演化,制度都是組織的符號與邏輯。〔8〕在一系列研究制度的經典文獻中制度研究都是從組織開始或以組織結束的。參見[美]道格拉斯·諾思、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美]哈羅德·德姆塞茨:《競爭的經濟、法律與政治維度》,陳郁等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美]奧利弗·E.威廉姆森:《市場層級制——分析與反托拉斯含義》,蔡曉月、孟儉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美]奧利弗·E.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企業(yè)、市場與合同關系》,孫經緯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二)制度是組織為主體的行為結構
人作為行為主體雖具有廣泛性,但也是通過共同的規(guī)則組成組織結構的。組織作為行為主體的積聚體能夠擴大或放大人的功能,使得制度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作用。制度是組織的行為規(guī)則,〔9〕雖然諾思后來將制度定義為規(guī)則,但是在1971年還是將制度定義為組織加規(guī)則,甚至更強調組織的作用,主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同時他也強調制度對有效率組織的作用,主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同前注〔8〕,道格拉思· 諾思、羅伯斯·托馬斯書,第5頁。即便在制度分析“SSP”范式中同樣可以考察出,績效來源于結構,結構來源于狀態(tài)。〔10〕參見[美]A.愛倫·斯密德:《財產、權力和公共選擇——對法和經濟學的進一步思考》,黃祖輝、蔣文華、郭紅東、寶貢敏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6頁。制度績效是否能夠達到,考察規(guī)則是否適合主體本質或屬性就能得出結論。
組織才是一切規(guī)則的主體。組織之所以能成就規(guī)則,就在于組織孕育著滿足人性的內在要求。“激勵是組織設計的核心”,同樣也是組織變革的原因。〔11〕參見[美]愛德華·勞勤三世:《組織中的激勵》,陳劍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第19頁。組織不僅激勵每個人向著共同方向而努力,也同樣激勵著每個人為實現(xiàn)個人目標而努力,從而成就了規(guī)則和制度。只因為如此,組織是理性人的集合形態(tài),理性就成為組織的本質,美國學者斯科特甚至直接定義組織是作為理性系統(tǒng)的結構。〔12〕參見[美]W.理查德·斯科特等:《組織理論——理性、自然與開放的系統(tǒng)視角》,高俊山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7頁。組織的理性特征決定了組織與規(guī)則或規(guī)范具有必須強調共同目標、集體行動與同一的規(guī)范結構。因此,組織總是制度的,而制度必定是組織的。
體制是組織的集合體,是比組織更大的社會結構。組織是集體行動,而“集體行動不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而是一種社會構建”。〔13〕[法]米歇爾·克羅齊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行動者與系統(tǒng)——集體行動的政治學》,張月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伯恩斯更是將組織結構框源自于政治、行政與市場、企業(yè)或產權的社會結構。〔14〕參見[瑞典]湯姆·R.伯恩斯:《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結構化——行動者、制度與環(huán)境》,周長城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吉登斯則強調體制決定規(guī)則遠不是其中的任一要素所決定的,而是社會結構的總體要求。〔15〕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李康、李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頁。艾斯納甚至明確“體制是決定社會利益、國家與公司、工會和農業(yè)組織等經濟參與者之間的政治制度安排”。〔16〕[美]馬克·艾倫·艾斯納:《規(guī)制政治的轉軌》第2版,尹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所以說,體制就成為了規(guī)則設計的前提,或者成為了制度績效大小的前提,同樣地,能源體制成為了能源制度績效的前提。
(三)能源體制決定能源法律結構
制度優(yōu)勢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前提。真正的制度優(yōu)勢是體制與規(guī)則整合的優(yōu)勢,而不是規(guī)則單獨創(chuàng)造的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其實是從組織優(yōu)勢或者體制優(yōu)勢肇始的。盡管體制包括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但基于行政組織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體制通常會表現(xiàn)為政體的擴散,甚至是政體的延伸,在政府配置資源的經濟體中尤其明顯,這正是能源體制通常被界定為行政體制的原因之一。能源體制是政府、產業(yè)與企業(yè)的結合體或結合方式。基于規(guī)則的組織總是在規(guī)則中存在的原因,看似彼此獨立的組織形態(tài),行政組織與產業(yè)組織卻是相互結合、交叉與捆綁在一國統(tǒng)一的制度結構中的。正因為如此,行政效率與產權效率總是關聯(lián)的或同步的或成正比的。基于權力決定市場,國家對產權效率負責也就成為必然的結論。〔17〕參見[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
體制效率、制度效率即為產權效率。體制效率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行政效率加產權效率,實質上卻是產權效率。這是因為表現(xiàn)為一國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通常是以產權效率,即社會交易成本的高低來衡量的,行政效率只有表現(xiàn)為產權效率時才有意義。行政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政治交易造成的成本通常構成了社會交易成本的主體,包括政府腐敗成本在內的行政成本通常是產權成本轉化而來的。同時,還因為行政體制決定企業(yè)體制,行政體制與企業(yè)體制嵌入在同一個社會結構中,行政直接實施產權,決定了市場資本結構與市場邊際。行政若不為產權效率設計,產權定無效率可言,反之,產權若無效率,行政必定績效低下。行政威權控制必然以企業(yè)或市場結構的壟斷匹配。中國能源體制轉型從經濟體制到行政體制,大多是在二者分離中實現(xiàn)的。行政體制轉型并不為企業(yè)資本轉型及其產權效率負責。停留在簡政放權的行政體制改革并未帶來資本結構與產權效率的提升,甚至部門之間權力與利益的博弈阻礙著大部制改革的進程。
現(xiàn)行作為部門法的能源法從部門規(guī)章或行政法規(guī)起步直到法律的出臺,著實為能源領域的法制奠定了基礎,卻沒有為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及建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提供制度設計與選擇。以至于壟斷與法律同在,法律甚至成為舊體制的護身符。能源體制的轉型首先是行政體制的轉型,行政體制轉型的結果也多體現(xiàn)在法律制度上。基于政府部門在法律制度設計中的主導作用,現(xiàn)行能源法的轉型更多地是取決于政府部門的意愿。政府部門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已經確定為制度的利益形態(tài)不會輕意放棄,這也正是法律制度轉型遲緩的原因所在。正因為如此,中國現(xiàn)行能源法律制度缺陷皆可從現(xiàn)行能源體制中找到答案。〔18〕2017年國家發(fā)改委、國家能源局《能源體制革命行動計劃》明確了能源體制革命的內容包括如下四類:(1)構建有效競爭的能源市場結構和市場體系;(2)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3)創(chuàng)新能源科學管理模式;(4)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這些體制革命的內容明顯與制度革命的內容具有同一性,從而也證成了能源法律革命要首先從能源體制革命著手。(參見《〈能源體制革命行動計劃〉布局四大類共14項主要任務》,http://www.nea.gov.cn/2017-07/21/c_136461254.htm,2019年10月10日訪問)。體制革命比制度革命更加重要,對于建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為目標的能源法律革命來說更是如此,難怪擁有法律與經濟制度知識背景的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10月國家能源委員會上強調,技術創(chuàng)新與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是能源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參見《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http://www.gov.cn/premier/2019-10/11/content_5438589.htm,2019年10月16日訪問。
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建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首先要還原政府公共權力政治屬性,還原現(xiàn)代政府體系。當政府始終是能源配置的主體時,權力異化就會成為現(xiàn)實。而權力異化必然伴隨著權力對權利的越界。權力與市場邊際成反比,權力越大,市場越小,反之亦然。企業(yè)家精神也因此受挫,正如諾思所言,經濟與政治中缺乏競爭減少了創(chuàng)新,尤其是破壞性創(chuàng)新,〔19〕參見[美]道格拉斯·C.諾思、約翰·約瑟夫·瓦里斯、巴里·R.溫格斯特:《暴力與社會秩序——詮釋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頁。只有從行政壟斷中解放市場,能源企業(yè)才會有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
(四)能源法律依能源體制制度設計
政治體制、行政體制與市場體制或者政治結構、權力結構與產權結構都在能源體制中匯集直接決定著能源增長與發(fā)展。正如諾思所言:“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績及知識和技術存量增長速率。”〔20〕同前注〔17〕,道格拉斯 ·C.諾思書,第17頁。在能源體制面前,能源法律只能是“隨從”。體制決定法制,體制創(chuàng)新是法制創(chuàng)新的前提。〔21〕參見[美]史蒂文·瓦戈:《法律與社會》第9版,梁坤、邢朝國、郭星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頁。制度設計固然應當根據(jù)行動者的偏好,〔22〕參見[美]利奧尼德·赫維茨、斯坦利·瑞特:《經濟機制設計機制》,田國強等譯,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只是行動者的偏好必定是組織的、是體制內的。重大改革事項于法有據(jù)也并不表明法制決定體制。不同國家法制的作用不同,體制決定法制卻是現(xiàn)實。正因如此,斯科特等人專門從組織角度研究制度認為,制度本身就是組織,體制就是法律。〔23〕參見[美]W.理查德· 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第3版,姚偉、王黎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
體制決定法制還表現(xiàn)在體制決定法制的變遷。能源體制變遷的形態(tài)與速率直接決定法律變遷的形態(tài)與速率,只是能源法律必須同步進行制度設計,并成為能源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具體而言,隨著電力工業(yè)部改制為國家電網公司,以及“先照后證”改革,《電力法》廢除了電力企業(yè)生產許可證制度;隨著煤炭部歸位安全生產總局,以及行政審批事項的改革,《煤炭法》廢除了生產許可證和煤炭企業(yè)經營許可制度;隨著投資體制的改革,《節(jié)約能源法》增設了國家實行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jié)能評估和審查制度;隨著投資體制和價格體制改革,《可再生能源法》對銷售電量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償制度。〔24〕2013年《電力法》 廢除第25條第3款,2013年《煤炭法》 修改第22條,并廢除23條、第24條、第25條、第26條、第27條、第46條、第47條、第48條、第67條、第68條,2016年《煤炭法》廢除第19條,2016年《節(jié)約能源法》修改第15條。可見,法律出臺或法律某些制度的演化都是能源體制變遷的結果。在能源體制變遷過程中,能源法律是充當體制變遷的組成部分或階段性成果,離開體制的創(chuàng)新或變遷,就不會有法律制度的創(chuàng)新或變遷。
二、體制革命:能源法律革命的希望之光
既然能源體制直接決定了能源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如何演化就必須在能源體制的前提下進行討論。能源體制的演化性質與數(shù)量必然決定法律制度的演化性質與數(shù)量。因此,能源法律革命能否進行,以及革命的性質與裂度,都必須從能源體制革命入手。實際上,自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五年來能源體制革命已經為能源法律革命帶來了希望。
(一)體制裂變通常是制度裂變的起點
革命是制度裂變,更是體制裂變。制度是組織的規(guī)則,作為組織集合體體制的裂變就成為制度裂變的前提。體制轉型是常態(tài),而體制裂變則是非常態(tài)。任何體制都有追逐公平與效率持續(xù)轉型的趨向,雖然漸進轉型與激進轉型并行或交叉,革命卻是在其中必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通常是在分配不公導致利益集團博弈發(fā)生重大變異,〔25〕參見[美]杰弗里·M.貝瑞、克萊德·威爾科克斯:《利益集團社會》第5版,王明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頁。或者是技術創(chuàng)新破壞了現(xiàn)存制度結構與利益平衡時,〔26〕參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7頁。體制裂變或革命就會發(fā)生。法律是體制的,制度隨體制轉型漸進、激進或革命。體制革命一旦啟動,包括法律在內的制度革命就會跟進。在現(xiàn)代社會一國體制多是正式體制,正式體制對法律等正式制度具有直接的作用。正式體制革命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一旦啟動,與之結合配置的正式制度就會在最短的時間里隨之革命。當然法律不等于體制,而且法律是根據(jù)體制需要進行設計的,只有當體制革命經過“試錯”階段,與現(xiàn)行體制磨合出現(xiàn)適應性,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同時滿足法律革命的制度理性有一定的供給時,與之匹配的法律革命才會發(fā)生。雖然基于法律在法律制度結構中不同層級、位階地位與功能的差異,以及受制于立法程序與立法技術,各類法律革命對體制革命跟進時序有所不同。
(二)中國體制裂變與法律裂變同步
中國是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國家,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裂變才會帶來裂變的大勢。能源體制革命就勢生成才會有可能促成法律革命的同步生成與發(fā)展。地緣政治與政黨政治處于社會結構的高端,決定著能源體制的變遷形態(tài)與速率,體制裂變發(fā)起于地緣政治與政黨政治。基于能源領域的公共性與政治性特點,能源體制每個重大變遷都必定會有中央的決斷。縱觀中國能源體制的演化史,無不以中央有關體制改革的文件為演化的肇始。現(xiàn)行的能源法律的出臺或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也總有中央文件或政策的依據(jù)。雖然法律經常出現(xiàn)滯后情勢,但是體制革命與法律革命能否發(fā)生或能否取得較大的績效更多地取決于中央啟動和推動革命的決心!
從制度演化的時序上看,政治裂變決定體制裂變,體制裂變決定法律裂變。實際上,政治裂變一旦出現(xiàn),體制裂變與法律裂變便會同步發(fā)生。這是因為制度演化是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的,體制裂變必須由法律跟進與架構。體制裂變從政治謀劃到實際發(fā)生,特別是按照政治謀劃成為現(xiàn)實,必須以規(guī)范化或制度化作為前提或步驟或階段。同時,法律裂變也必須以體制裂變?yōu)橹魏捅U稀U驗槿绱耍w制裂變與法律裂變不可能獨立發(fā)生,不僅如此二者還必須相向裂變、匹配或配合裂變。實際上,在政黨政治的統(tǒng)籌決策下,體制裂變與法律裂變也只能是同步發(fā)生、同步演化的。
(三)能源市場化劃定政府市場界碑
雖然包括制度革命在內的制度變遷已經跨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但是政府權力與市場產權依然是法律規(guī)范的邊際。中國現(xiàn)代能源市場制度建設是以限制政府權力來實現(xiàn)的。產權直接受制于行政權,產權效率來自于行政權效率,只有將行政權效率定位在產權效率,政府才會真正為產權服務。所以,只有當行政權效率與產權效率同一或統(tǒng)一時,產權效率才會成為政府行為的內在機理,提升產權效率成為政府的行為準則。當產權效率成為政府首要目標時,政府對產權的管制并不一定會帶來較高的交易成本,或許會降低交易成本,因為不論是管制還是放松皆以產權效率為轉移,所以管制就不會給產權效率制造障礙。在市場規(guī)則并不健全或市場主體誠信度不高時該效果會更加明顯。政府與市場通常是通過權力與產權關系表現(xiàn)出來的。由于權力是國家的組織制度表現(xiàn),市場是企業(yè)或個人的組織制度形式;市場是產權的運作的形態(tài),權力決定產權,所以權力與市場的關系完全取決于權力意愿,權力配置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就成為市場制度發(fā)育與成長的根本性路徑依賴。
必須承認的是,民主政治不僅是法治的條件,也同樣是產權效率的條件,因為作為政治體的政府并不必然將產權效率作為追逐的目標,只有當產權效率與其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相一致時其才會追逐產權效率。如何從特殊利益轉向公共利益是政府或權力處理市場或產權關系的必由之路。真正意義上的體制革命必須伴有政治革命,當然,這種政治革命也會在執(zhí)政黨自我完善的情勢下發(fā)生。
(四)“清單革命”引法律革命前程
控制權力、追逐產權效率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內實現(xiàn)的。建立和完善市場體制通常都是政府與市場關系有效率的基本前提,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市場化改革程度與速率直接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功成的制度績效。市場化的核心在于縮小權力邊際,擴大產權邊際,但問題在于,控制權力就是要讓權力成為產權自由度的保障,而不是成為制約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桎梏。
從醫(yī)師處方開始的清單革命已經在明確權力,增加責任,〔27〕參見[美]阿圖·葛文德:《清單革命——如何持續(xù)、正確、安全地把事情做好》,王佳藝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92頁。只是“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改革必須匹配、對稱或對應,而且必須同步。要讓產權效率成為政治效率或行政效率成為能源法制完善的不二選擇,如此方可避免因政治目標影響經濟目標的實現(xiàn),也可以將政府工作的重心定位在經濟增長與發(fā)展上。讓市場經濟從私人產權走向國家主權成為現(xiàn)實,就必須讓“不講道德的大政府”讓位于“講道德的自由市場”。〔28〕[美]史蒂夫·福布斯、伊麗莎白·艾姆斯:《重鑄美國自由市場的靈魂——道德的自由市場與不道德的大政府》,段國圣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為此,能源法的法律價值應當定位在產權效率的正當性上。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市場是管制的市場,包括自由市場在內的市場都是制度的,制度都是有維系者的,政府就是維系者,管制就是政府維系市場的基本手段。只是管制必須為產權效率而存在,否則就應當放松或除去。管制是市場管制,產權交易的市場是管制存在的前提,無市場則無管制。管制的功能在于促使市場功能的發(fā)揮,即產權效率的提升與交易成本的降低,管制只能解放市場,而不是能替代市場。能源法的法律價值正是在設計與安排管制的市場與市場的管制中實現(xiàn)的。
三、法律革命:能源體制革命的現(xiàn)實抉擇
體制是制度的體制,制度是體制的制度,法律革命是否啟動、如何選擇的關鍵取決于能源體制革命的抉擇。與法律革命相比,能源體制革命更不容易發(fā)生,因此能源體制能否發(fā)生、如何革命直接制約或決定著能源法律革命的性質與程度,然而,能源體制革命能否發(fā)生與發(fā)生的方向卻是一國政黨政治根據(jù)能源基準情景與政策情景所決定的。
(一)體制革命開拓法律革命的空間
如果制度演化的動因在于提升產權效率,那么就必須打亂現(xiàn)行低效率的體制,建構破壞性體制,重構能源體制及其利益與權力格局,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配置政府權力,實行“大部制”改革,實現(xiàn)行政權力的合并同類項,縮減政府組織機構,在形式上讓集中權力替代分散權力,提升行政權力的效率,讓外化的行政成本內部化,發(fā)生類似企業(yè)替代市場的功效,使行政交易成本減少,在實質上卻是讓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因為任何行政成本都是政治成本,都會直接轉化或者放大交易成本。
打碎舊體制必須從根本上下功夫。現(xiàn)行行政體制改革從行政審批下放擴大到“放管服”著實有了一定的進步,然而,改革的立足點或著力點依然在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其實以行政審批下放為特征的行政體制改革依然是圍繞行政權力完善進行的,是對舊體制固化措施。減少舊體制的震蕩雖容易操作,但對產權的損害卻會持續(xù)增加,只有當行政體制改革以提升產權效率為立足點時,行政體制改革才會在根本上有實質性突破。
行政體制改革必須與企業(yè)體制改革配套進行。實際上,這兩類體制直接表征出行政權與產權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制度從混同到吸收,當然這兩個體制的匹配改革就要求政治體制統(tǒng)籌行政體制與企業(yè)體制,組成嵌入式結構。體制改革或革命的核心點在于從資源決定型體制向技術決定型體制轉型,資源決定型體制讓政府進行資源分配,權力成為企業(yè)逐利的目標值,政府也因此增加了貪腐機會,導致政府不像政府、企業(yè)不像企業(yè)。而技術決定型體制讓企業(yè)通過市場競爭獲取最大利益,RD&D成為企業(yè)逐利的目標值,政府也因此減少了貪腐機會,企業(yè)回歸產業(yè)組織。只是從資源決定型體制走向技術決定型體制取決于政黨政治,法律只能在政治啟動的制度變遷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能源法必須做好制度準備!技術回歸制度的前提是技術必須回歸資本,能源法必須以技術回歸資本為軸心,同時兼顧資源、勞動、環(huán)境容量等全要素經濟作用的發(fā)揮,才能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做出貢獻。
(二)法律革命與體制革命相伴相隨
雖然能源體制決定能源法制,但是體制的穩(wěn)定與效率必須以法律的穩(wěn)定與效率做保證。從制度結構理論出發(fā),制度效率其實是制度整體效率,而不是某一類制度效率,當構成制度的每一部分都能發(fā)揮作用時,制度效率才是現(xiàn)實的。社會制度結構的合理建構必須充分顧及各類制度都能有效發(fā)揮作用,但是必須承認正式制度特別是在國家治理中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是極為重要的。體制是法律存在的必要條件,但法律同樣是體制存在的必要條件。
能源體制革命實際上是政治革命、市場革命與法律革命的結構性革命。法律革命雖然是附從性革命、外在性或表征性制度革命,但也是體制革命等復合性制度革命的要求。能源法律革命與能源體制革命或確認或規(guī)劃或設計,能源體制革命才能成為持續(xù)的制度革命。中央文件所規(guī)劃的能源體制革命必須演繹為現(xiàn)行的能源法律革命才能成為可操作的現(xiàn)實的制度設計與安排。
(三)能源體制革命要求能源法革命
無論是不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革命,打破現(xiàn)行利益格局的能源體制革命肯定會引發(fā)利益格局的改變。法律雖然是附從性制度或利基制度,但是作為主要的制度變遷工具卻對體制革命起到了助推作用。在任何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法律的重大作用在于穩(wěn)定變革,〔29〕參見[英]羅杰·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第2版,彭小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在于具有公平與效率的共識,〔30〕同前注〔21〕,史蒂文·瓦戈書,第340頁。體制革命一旦受到法律革命的維系,不僅會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制度摩擦力,還會增加體制改革的耐力(在不同政治經濟背景、歷史文化背景以及發(fā)展過程或階段,法律革命對體制革命作用有所區(qū)別)。
革命的體制必然要求革命的法律,而不是改良的法律,更不是反革命的法律。革命的法律或法律革命必須以評估與診斷現(xiàn)行制度為起點。根據(jù)體制、組織與制度的經濟性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顯然是評估與診斷現(xiàn)行制度革命與否的標準。制度理性決定制度選擇,同樣也決定制度變遷和制度裂變的質量,在這里,經濟學、法學與政治學等多學科或多維評估與診斷是至為重要的。舒爾茨認為,隨著經濟價值觀念的提升,制度遲早會發(fā)生演化。〔31〕參見[美]T.W.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載[美]R.科斯、A.阿爾欽、D.諾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劉守英等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65頁。必須承認的是,革命的法律或法律革命所需要的制度理性是多維的,其中經濟理性必定是決定性的,因為發(fā)生在市場經濟下的能源體制革命和能源法律革命必定是以產權效率為軸心,經濟理性無疑是最重要的制度理性。
(四)能源法革命助力能源體制革命
無論是在非傳統(tǒng)體制,還是在傳統(tǒng)體制,法律革命對體制革命的作用都是有限的。雖然非傳統(tǒng)國家法律的作用可能會更大一些,但問題在于法律要順應體制革命而革命,能動革命,主動革命,而不是成為阻撓體制革命的依據(jù)。從中國能源革命的現(xiàn)實來看,現(xiàn)行能源法律非但沒有成為重大體制改革的依據(jù),還經常成為阻撓改革的絆腳石、攔路虎。基于法律體系與法律結構的邏輯性與決定性,現(xiàn)行能源法對能源體制革命表現(xiàn)出的羈絆絕不是能源法本身所能承受的,也就是說,能源法律革命是需要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革命抑或法律革命來實現(xiàn)的,但是這也絕不意味著法律革命發(fā)生之前能源法對能源體制革命就不能做出革命性的抉擇。
在能源體制革命已經開始的大勢之下,能源法的作用可以就勢發(fā)揮,〔32〕史蒂文·瓦戈認為,社會變遷一旦啟動,構成社會制度的任何部分順勢而為,都可能有發(fā)揮作用的空間。參見[美]史蒂文·瓦戈:《社會變遷》第5版,王曉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頁。特別是充分利用政黨政治所開拓的制度邊際進行革命性制度設計,進而與體制革命融為一體、相互推進。能源法要突破現(xiàn)行的立法框架,逐步實現(xiàn)從確認改革到規(guī)劃改革或設計改革(這種法律功能遞增的關鍵在于市場化與民主化程度的遞增)。從法律體系主義的邏輯出發(fā),《立法法》雖然規(guī)定了較為嚴明的法律位階與框架,但是在現(xiàn)行立法過程中立法權限并不嚴謹,〔33〕根據(jù)我國《立法法》第7條之規(guī)定,基本法立法權限屬于全國人大,然而規(guī)范國家機構行為的基本法,如《行政強制法》《行政處罰法》等,竟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所以能源法要做出適應能源革命的法律,仍然存在突破現(xiàn)行立法框架的空間,畢竟這種突破也只是立法技術上的突破。
在體制革命或能源體制革命的大背景下,能源法可能進行的革命性設計或安排應當以擴大民營資本的制度性進入為主,如能源領域PPP制度的設計、可再生能源替代、競爭性市場的建立、能源大型企業(yè)權利影響力的縮小等。〔34〕中國能源領域長期處于計劃經濟,即使是市場經濟已在大多數(shù)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今天,能源領域,特別是化石能源領域及電力行業(yè),國有資本依然占據(jù)主導地位。一方面,建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亟待民營資本為主的社會資本的規(guī)模進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除了出版社、報社等,其他領域均并無非公資本進入限制,但134條中未獲許可不得投資建設的特定能源項目多達15項;另一方面,能源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又亟需民營資本多種形式的規(guī)模進入。國辦發(fā)〔2018〕101號《關于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指出,補短板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能源領域短板明顯,要規(guī)范、有序地撬動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投資,投入補短板重大項目。適應能源領域市場化改革特點,細化包括PPP等投資規(guī)范,營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為民營資本規(guī)模性進入能源領域清除制度性障礙是能源法必須進行的革命性制度設計。當然,這些制度設計一定要與能源體制革命相匹配,并以政黨政治制度牽引相一致,冒進的制度設計并不可取。所以說,能源現(xiàn)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制度建構是能源體制革命走向能源法律革命的必然要求。
四、制度革命:能源體制革命的能源法
能源法的制度設計必須從能源體制革命出發(fā),而不是從能源法律邏輯出發(fā)。任何有違能源體制的制度設計或者沒有根據(jù),或者不能實施。實際上,適應能源體制革命的能源法才能從“效力”走向“實效”。能源體制革命決定著能源法制度革命設計的邊際。雖然適應能源體制革命的能源法革命性制度設計也有一定的立法技術限制,但是能源法律制度設計的真正障礙是體制,而不是技術,因為對于立法技術革命法律人可以自行解決,而體制革命卻是政治家決定的。
(一)能源法從體系建構到體制革命
從凱爾森的法律規(guī)范等級體系到佩策尼克的法律邏輯,〔35〕參見[奧]漢斯·凱爾森:《國家與法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瑞典]亞歷山大·佩策尼克:《論法律與理性》,陳曦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從弗里德曼的法律制度到麥考密克的制度法論,〔36〕參見[美]勞倫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從社會科學角度觀察》,李瓊英、林欣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英]麥考密克、[澳大利亞]魏因貝格爾:《制度法論》,周葉謙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有關法律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法律規(guī)則邏輯的自我演化進行的。即使在伯爾曼的理論框架里,體制也并不是法律變革的主要決定者。〔37〕參見[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第1卷,賀衛(wèi)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體制是法制的體制,法制是體制的法制。法律離開體制或不為體制建構服務,法律的價值就會成為法律人的玩物、自我陶醉的城堡。然而,法制意義卻不復存在!體制需要法制,法制更需要體制。只有體制革命才有法律革命,體制進階必然會帶動法律革命。中國能源法的演化無不是以體制演化為前提,甚至是由體制演化所決定的。
從一定的角度看,形為制度革命的法律革命其實是法律架構的體制革命,這不僅僅是因為體制與法制互為一體,還因為體制革命必然成為法律革命,而法律革命必然是體制革命的附隨物或伴生物。
(二)大部制與權力清單、責任清單
能源綜合管理“大部制”的成因與其他產業(yè)相同,政府職能合并同類項,避免權力沖突和降低行政威權或效力,節(jié)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強權力責任。實際上,真正的原因在于給產權更多的博弈機會,提高產權效率,降低社會成本。能源領域涉及政府管制的內容通常復雜且繁多,最多涉及社會管理、科技研發(fā)、信息、就業(yè)人口等方面,而且資本規(guī)模較大,直接關涉一國的穩(wěn)定,由于涉及的政府職能相當廣泛,建立“大部制”有利于進行集中統(tǒng)一管理,所以說,“大部制”更有利于從壟斷中解放市場。
必須承認的是,“大部制”形式上集中了權力,實質上卻限制了權力。權力集中限制了行政自由裁量的機會,進而縮小了政府支配的范圍與時空,縮小了政府組織機構,也就會放大產權交易的機會空間,使得外化的行政成本內部化,同時也將外化的交易成本內部化。管制與產權的關系雖然有時也可以解讀為權力的市場、市場的權力,但實際上權力的邊際與產權邊際成反比,只因如此,有關權力與產權的設計必須計算甚至精算,政府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應當匹配企業(yè)的“負面清單”進行制度建構。從權力法定到物權法定,權力與產權邊界在法律中得到確認,能源體制因此成為法律制度。此際,被法律定型化的體制革命才能有持續(xù)與更宏大的制度績效。
(三)資本結構革命與能源市場體系
市場經濟的法律規(guī)則是法律作為資本秩序的法律規(guī)則。資本所依的秩序來自于資本互補與互換,資本交易是制度的起源或本質,制度交易或交易制度成為制度的本質屬性。〔38〕參見[德]路德維希·拉赫曼:《資本及其結構》,劉紐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頁。資本結構多元性通常是組織結構與行為結構市場化轉型的開端,能源體制革命必須從資本結構的多元性入手,為培育競爭性市場開拓更大的空間,如此能源法律才會有更多的競爭性市場制度設計。資本結構不開放而僅靠競爭中立建構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并不現(xiàn)實。能源領域行政壟斷的破除必須以體制革命為路徑依賴,否則,不要說能源法對行政壟斷無奈,即使專司競爭與反壟斷的專門法律對行政壟斷也是無奈的。
適應市場經濟的制度必須是促進交易的組織與規(guī)則,任何妨礙交易的組織與規(guī)則都必須改進或剔除。中國能源領域尚處于典型的過渡經濟時段,無論是既得利益集團對現(xiàn)行制度的嚴防死守,還是能源轉型中出現(xiàn)的“進一步,退兩步”,都表明了能源法的制度演化或變遷其實都應當是在交易的限制與掣肘的排除中實現(xiàn)的。適應能源體制革命的能源法革命就應當在制度資本屬性不斷自我的實施中發(fā)揮作用。能源法制度設計必須堅持資本結構革命與能源市場競爭同行,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現(xiàn)代能源市場體系。
(四)《能源法》體制革命制度設計
中國《能源法》立法已走過了十余年,法律人已經殫精竭慮。盡管可羅列諸多未能出臺的理由,但真正的原因在于能源體制在風雨飄搖。
能源體制革命決定于政治革命,只有政治革命才能為體制革命帶來機會。然而,政治革命卻是一個極復雜的過程。難怪薩克斯認為:“轉型最難的部分絕對不是經濟,而是政治。”〔39〕轉引自[美]羅伯特·E.戈定主編、[美]卡爾斯·波瓦克斯、[美]蘇珊·C.斯托克斯編:《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唐士其等譯,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頁。同理,能源革命重要的不是經濟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如同體制決定法制一樣,政治同樣在決定體制,這是因為能源體制的轉型或革命絕對是利益集團利益的改變,甚至是根本改變,必須由政黨政治決策,否則不會成為有組織、有系統(tǒng)的行為方式或規(guī)范結構。只可惜包括能源體制革命在內的能源革命迄今并未成為政黨政治,更不要講成為能源戰(zhàn)略。
中國能源體制革命的路顯然還很長,但中國能源法律革命的路可能并不長,因為能源法律革命的肇始條件通常都是由能源體制革命創(chuàng)造的,若要能源法律發(fā)生革命必然要有體制革命,而且能源體制革命已經醞釀成熟,否則能源法律革命就不會發(fā)生。當能源體制革命成就時,能源法律革命必然會發(fā)生,雖然能源法律革命也并非一蹴而就,但是與能源體制革命相比卻是相對容易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很顯然,制度創(chuàng)新的難點在能源體制革命,而不在能源法律革命。
所以說,《能源法》的羈絆其實是能源體制造成的。《能源法》的制度設計將圍繞體制革命的實施路徑展開。必須承認,正在施行的電力體制改革與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及其可能帶來的《電力法》修訂與《石油天然氣法》立法都會為《能源法》帶來機會。作為基礎性法律的《能源法》只有順應能源體制革命、做出適應能源革命的設計才能推動能源法律革命。從此意義上講,《能源法》首先要擔負起能源體制革命的重任,才能踐行能源法律革命的重任。以競爭性能源市場制度建構為基礎進行制度設計,重構行政組織與產業(yè)組織的關系,特別是以產權效率為目標進行體制與制度選擇是《能源法》富有制度革命設計的抉擇。
五、結論
從垂直一體化到輸配一體化,電力體制改革正在布局,從上游集中壟斷到放開部分油氣田的改革也正在展開。由政黨政治開啟的新一輪能源體制革命的大幕正在拉開。適應能源體制改革的要求,能源法律制度創(chuàng)新已經成為現(xiàn)實。能源體制革命的深度與廣度決定著能源法律革命的績效與成敗,投身于轟轟烈烈的能源體制革命之中,不僅能讓能源法律革命得到實踐,而且可能開拓能源法律革命的空間,因為制度已經開始演化,能夠增強組織能力,擴大組織邊際,甚至造就新的組織,最終擴大制度的功能。法律人要熱衷于能源法律革命就必須要關注能源體制革命,甚至更要注重于后者。也就是說,只有在能源體制革命的實踐中才會為能源法律革命積淀理論與制度規(guī)則。雖然法律人與政治家不同,投身能源革命不一定會帶來生命代價,但是同樣需要做出成本付出的準備,惟其如此,才能做一個徹底的革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