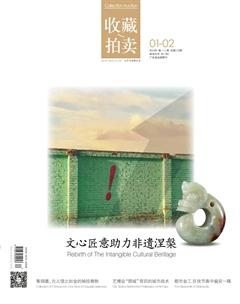四大痛點圍就非遺困局
雨田



曾幾何時,我們曾是那個讓人向往的天朝上國。技藝精湛的手工品為世界各國艷羨,更曾遠涉重洋,成為異國他鄉讓人趨之若鶩的奢侈品。即使未曾踏出國門者,也各具特色,銘記著一方水土的風韻。斗轉星移,那些原本精美絕倫的手藝似乎已跟不上社會極速前進的步伐,成為日益被邊緣化的“非遺”。
毫無疑問,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非遺工藝最多的國家。除了少數在當今獲得較好的傳承與發展,大部分依舊舉步維艱,甚至奄奄一息,亟待社會力量的拯救與扶持。如今,隨著人們對傳統美學的認可與回歸,“非遺活化”再次成為時下熱議的話題。文化遺產日的舉辦,各類非遺工藝展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楚認識到,非遺活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當今面臨的幾大困境仍舊不容忽視,值得世人深思。
賴以生存的土壤缺失
非遺工藝的整體衰落絕非偶然,而是一種大環境下的普遍現象。這并非一朝一夕可扭轉的大局勢。從根本上講,這種整體衰落是因為中國傳統非遺工藝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缺失了。
中國如今的各項非遺工藝,實際上是源自于中國數千年的農業社會,服務于古人的衣食住行。而當今世界的現代文明,是以西方文明為基礎發展而來的,進入近代后,當落后的農業文明向這一“先進”的工業文明靠攏時,必然經歷社會文化的西化,從而對本國傳統文化造成巨大沖擊,而依附于傳統文化的各種傳統工藝自然缺失其生存的土壤。所以,當全社會都在整體追求文明開化時,過去的傳統文化反而被視為落后、老土的代表。
這并非中國一家之窘況,亞洲各國都面臨過類似情形。即便最堅守傳統的日本人,也曾在二戰后一度對西方工業文明推崇備至,對本國傳統工藝甚為冷落。直至當時一些工藝大師、藝術家聯合起來,集體發聲,為傳統工藝爭得一席之地。他們認為,東方傳統工藝有其獨特而深厚的底蘊,足以對話西方藝術,在一代代藝人的努力下,日本人逐步認識到本國傳統工藝的價值,和式與西式的生活方式并行不悖,政府也對傳統工藝進行適當保護與引導,從而讓日本的許多傳統工藝得以獲得較為良好的延續和發展。
另一方面,審美趣味的變化也會讓非遺工藝生存土壤喪失,正所謂一部藝術史同時也是一部贊助人的審美意識與審美趣味變遷史。如果消費藝術的贊助人都缺失了,工藝再好又何來用武之地?如曾顯赫一時的“樣式雷”家族,數代人掌握皇家建筑的設計、營造技藝,卻隨著封建王朝的沒落而迅速銷聲匿跡,堂堂宮廷御用建筑師的后人要為生計問題而變賣家產;廣州十三行的外銷工藝品曾極盛一時,廣彩、廣繡、各類外銷藝術品曾大量遠銷西方,但隨著西方審美潮流的改變也逐步衰落。這些例子舉不勝舉,按經濟學的說法,這就是市場的作用。沒有消費市場,自然也就無法吸引從業人員,甚至導致人才的流失。綜觀各項非遺工藝,其衰落的程度與消費市場的萎縮程度都成正比。
缺乏文化介入,難以傳世
這里說的文化介入包含兩個方面:首先,是非遺工藝品普遍缺乏“文化含量”。中國目前的非遺工藝,除了少部分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絕大部分仍舊在沿襲傳統,復制前人的做法。不少非遺匠人擁有一手好工藝,掌握著難度系數很高的技術,但卻缺乏一定的文化、藝術修養,以至于作品流于匠氣。更具危害性的是,隨著近年社會對傳統文化的回歸、工匠精神的提倡等,不少非遺匠人不注重進行自我提升,而是熱衷于申請各種“大師”頭銜。更有甚者,打著工匠精神的旗號,以炫技為賣點,作品盡是繁復的技巧堆砌,卻不見藝術上的經營與文化的注入。這樣的作品甚至冠以大師名作高價出售,對收藏市場的發展并非利好,反而有害。對一件工藝品而言,藝術價值、文化價值才是其最重要的價值,如果藝術、文化價值不高,并不足以傳世。
在古代,中國傳統工藝從來離不開文化人的參與,明式家具就因文人的把控而呈現出高雅的品位與格調;宮廷御制的瓷器,也必須有宮廷畫師的參與,才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說,因為有文化力量的介入,再結合相應的工藝技術,才能稱為藝術品。“技”與“藝”既分工,又密切配合,從而使技術不至于流于表面。因此,如今一些成功的非遺活化案例,都是文化學者、藝術家參與到非遺工藝的創作中來,從而使其文化與藝術含量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非遺工藝品還缺乏相應的文化包裝,這也是缺乏文化介入的一種表現。少數如刺繡、陶瓷等在很長時間里都受到皇家的喜愛、推崇和扶持,并得以漂洋過海,為全世界所知,則容易獲得傳承與發展,而其他大部分民間技藝往往不具知名度,或因地處偏遠鮮為人知而沒有得到推廣。其次,地方政府對非遺項目的扶持力度各不相同。對于非遺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投入和非遺傳承人的資金支持,我國至今沒有統一的補貼標準,基本上將權力交給地方政府。如果是經濟落后的地區,對非遺技藝的扶持力度有限,文化包裝與對外宣傳更無從談起,這又反過來讓非遺工藝更缺乏市場,形成惡性循環,這樣非遺工藝匠人連生計都存在問題,又談何傳承和弘揚。
創新不足,缺乏與現代生活的連接
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活化非遺不能全靠政府資助,全國有千千萬萬項非遺,如果全指望政府扶持,顯然是不明智的。如果傳統非遺工藝不能進行自我創新,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即使得到再多政府的扶持也是徒勞,只會成為“扶不起的阿斗”。
許多非遺匠人固守一方,對當代審美、藝術潮流視而不見,所謂筆墨應隨當代,如果作品與現代生活割裂,自然也無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正如廣東嶺南工藝美術館館長楊飛武所說的:為何市場上對傳統工藝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這與當下各級工藝美術大師的創作有否突破與創新有關。傳承人和工藝美術大師是否敢于突破傳統題材的束縛,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有個性的東西?這需要非遺工藝從業者既要掌握前人留下的技藝,又要對當下生活有自己的理解。藝術要融入生活,離不開設計的作用。如今一些非遺工藝與當代設計結合,成功地走出一種非遺工藝發展的新模式。如在家具設計中融入木雕、銀絲鑲嵌工藝;刺繡、緙絲通過服裝設計煥發出新的魅力。又如一些精心設計的非遺小鎮,以當代建筑技術融合中國傳統的建筑工藝如石雕、磚雕、灰塑等,使建筑保留傳統韻味的同時,又能滿足現代人的起居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非遺創新也不單是傳承人的職責。還需要全社會、團體的介入,才能幫助非遺工藝創新走出困局。這其中除需要企業等社會力量的資金支持,也需要后繼有人。“當年青一代失去對傳統文化的興趣,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有走進檔案室、博物館、圖書館,從活態變成歷史記憶的危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處處長塞西爾杜維勒表示出擔憂。如果國人沒有發自內心的認同本土、本民族文化,從小又缺乏相應的教育,傳統非遺工藝就缺乏新鮮血液的加入,自然難以獲得創新能力。
匠心不足,只余匠氣
中國諸多傳統非遺工藝大多是“難度系數”很高的技藝,要完成一件作品,需經多道繁復的工序,制作復雜,費時費工。這還不包括新手學習入門花費的大量時間,一些工藝少則三、五年,多則十年以上方能出師。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極高的制作難度也讓初學者望而卻步。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人的精神生活逐漸被快節奏的物質生活擠壓也是原因之一。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手藝的錘煉都需要長年累月的積累,而現代人大多缺乏這種信念和定力。比如緙絲的制作,既要有一定藝術功底、繪畫基礎,又要踏實學上三五年、學成后坐得住,才能成就有品質的作品,這些因素都讓很多人無法堅持到最后。
即使已經從事非遺工藝的匠人,如果不能專注自己所學專長,作品缺乏匠心,也很難得到市場的認可。這里所說的匠心不同于匠氣,匠心是指要有極致的工藝和注入作品中的藝術思想。所以,實際上我們提倡的工匠精神是要具有傳統非遺工藝的匠心,而非匠氣,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另外,一項非遺工藝的繼承不能僅僅靠傳承者的個人熱愛,如果繼承這項技藝無法獲得相應經濟收入,或者說投入的大量時間、精力與相應回報不成正比,都很難讓傳承者甘之如飴。當然更需要警惕的是,資本介入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能很好利用資本的力量,非遺工藝反而容易淪為廉價工業品。一些地區斷章取義簡單地將生產性開發等同于商品開發,把一項手工藝術品的生產方式工業化、使藝術品位雷同化,就背離了“非遺”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保護初哀。
此外,某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缺乏生產性和商業性,導致傳承困難重重,既很難讓傳承人在傳承文化的過程中獲得可觀的商業收益,也與現代文化產生了脫節,只能越來越邊緣化。靠政府的扶持,也僅能維持它們不完全消失,想要發展壯大似乎很難。這也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下,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