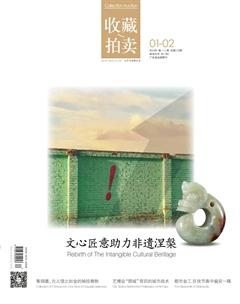藝術小組 借助團體力量聲張藝術
林紫鳴



當代藝術主張個性,但一些當代藝術家選擇聯合,以藝術小組發聲,或抱團取暖,或因某一理念而結合。藝術小組向來又是松散且不固定的。在當今文化傳播日益多元化的時代,藝術小組又將何去何從?
自而松散的小團體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的現代哲學和先鋒派藝術涌入的背景之下,產生了一場前衛美術運動,即“85新潮”。在“85新潮”進行得如火如荼期間,些藝術小組應運而生,如因地域原因而組成的小組“北方藝術群體”;有因共同認同某一個概念或期望遵從某種形式而建立的小組,如“池社”、觸覺小組、新刻度小組;亦有本身就是松散、無組織性的小組“大尾象”“廈門達達”等。
藝術小組作為一種非強制的自治組織,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有些已經解散,有些轉變成為更為緊密的合作形式。正如小組這一種形式,它帶著一定的時效性和偶然性。然而,如今我們不斷地提以像“大尾象”“陽江小組”“廈門達達”等,已經將其約定俗成成為一種風格或者具有某種特征的藝術團體。因此,他們是以何種方式來主動塑造小組的形象和身份變得尤其重要。
陳侗在《空間的交織——1991—1996年間的“大尾象”》一文中寫道:“人們相信組建一個團體是期望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區的藝術狀況,或者說為自己的欲望建立一個平臺的最直接和快捷的途徑。”我們可以這樣說,組建一個團隊,首先最基本的、最初的愿望,應該是希望通過組建團隊這樣的方式來達到資源共享或者功能分配的目的,從而達到效益最大化一如果一個人能完成的事,顯然是不必要組成團隊的。組建團體,可以說是對藝術家的觀念、個人趣味的一次自覺的選擇。不僅這樣,完成作品后的風險也分擔到各個成員身上,因為那是共同產出的結果。
隨后,陳侗又在文中提出:“但是,就像任何制度都存在缺陷一樣,一旦群體的人數達到需要通過建立一個委員會來進行統籌和協調的程度,那么,群體中勢必就會產生‘關鍵人物和分化出‘協同性人物,也就是說,產生權利中心。”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在上文中提及的小組當中,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一有些名字成為小組的核心、代表,而有些名字則藏于小組名字背后,只有出現小組名字時,他的名字才會顯現。小組的成立或解散除了涉及小組內權利問題以外,還有小組內人員的流動性也會影響小組的成立或解散。“大尾象”內的成員林—林移居美國,“廈門達達”的成員黃永砯移居法國,他們的移居均影響到各自小組的創作狀態,后者更加成為“廈門達達”解散的重要因素。
更多元的合作形態
與20世紀相比,今天隨著大眾媒體、科技、技術、社會關系等各種力量的進化,合作變得更加便捷,但是“小組”形式的藝術組合在國內仍為少數,更加多以個人合作而非重新組建小組的方式來合作。
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沒頂公司”顯然是一個從由松散組織變成有規律、合作化的公司形式的例子。“沒頂”是“madein”的中文諧音,也是一個缺失了主語的動詞,那是故意隱沒行動者的身份和身影的創作。沒頂公司創立以后藝術家徐震就徹底放棄了作為傳統個體藝術家的身份,與多人進行集體式創作。
徐震作為個人身份時的作品大多數以戲謔的風格為主,在作品的呈現時多以錄像藝術為主,例如為了證實他攀登上珠穆朗瑪峰并割掉山頂的1.86米所攝的《8848—1.86》(2005);呈現的是一個逐漸紅腫的背部,拍打的過程只有聲音和逐漸變紅的背部以外無其他記錄的錄像作品《彩虹》(1998);和拍攝背向鏡頭的移動的觀眾,直到被一聲從后面的喊叫驚嚇后才回頭的《喊》(1998)。
沒頂公司盡管沒有放棄這種作品中的幽默風格,但代表個人的徐震和代表“沒頂”的徐震是不一樣的,沒頂所走的是共同創作、把藝術品商品化的道路,這些作品的確是共同創作的結果。但當我們把這個集體創作內的個人等同于這個集體的時候,那么里面的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藝術家瑞恩甘德(Ryan Cander)制造了與沒頂公司相反的例子:他虛構了“一個由七名藝術家組成的藝術小組,他給予這七個小組成員詳細的名字和背景,使他們更加具有真實性。他甚至為這個藝術家小組舉辦了整個個展,作為他的一件裝置作品,命名為“上鎖房間中的情景”(2011)。展覽中所有的房間都是被鎖上的,觀眾只能從外圍的各個縫隙來窺探這個鎖起來的作品。整個空間內散布著各種關于這個藝術小組的信息,包括他們的手稿、時間軸、年表等。在這個作品里面,藝術家瑞恩·甘德虛構的藝術家都是他本人,但又不是他本人——因為我們無法從這些虛構的身份中判斷哪些是屬于藝術家本人的特質,而哪些又是他可以捏造的。
“與對獨立個體身份的關注行程對比,當今天的西方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使用身份(identity)這個詞時候,通常指涉的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身份。一位熱哀于身份主題的當代藝術家不僅會問‘作為個體的我到底是誰,還要問‘作為群體成員的我們是誰。”正如我們不能從藝術小組所產生的藝術作品談論誰才是這個藝術作品真正的作者,因為那是集體選擇性呈現一每個人都可能影響到這個藝術作品的產生。
聯合與否,關鍵在于人
身份源自互相依存的力量行程的一個網絡,這些力量為一個共同體內的所有成員規定社會色,但是同時,這些身份又應該是通過社會互動和共同的歷史行程的,而不是固定的。
“政治純形式辦公室”藝術家團體由策展人冷林,藝術家劉建華、宋冬、洪浩和蕭昱于2005年建立,他們的重新組合更像是一種基于對共同理念之上的組合。從實際的角度來考慮,藝術小組正在從自發的組織悄悄轉變成為功能性互補的團體。火遍全球的日本團體實驗室Teamlab在本質上來說也是一個藝術小組,他們的成員由各種創作型人才組成,包括程序員、工程師、CG動畫師、建筑師等,他們的作品都是集合性的呈現;日本藝術團體“明和電機”最初由一家電器制造工廠轉型而來,他們以機器來表演音樂,藍色的日本工廠制服是他們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還發明了廣為人知的產品“電音蝌蚪”。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認為,現代社會不是渾然一體的,而是由許多的“小系統”組成,每一個都是一個場域。場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但有自己的邏輯,而且也遵從整個社會的邏輯和制約影響。而在具體場域的背景結構下,布爾迪厄則使用“慣習”來解釋個體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既非唯意志的,也非結構主義的,他認為個體不是簡單的結構承受者和被動執行者,其主觀能動性也不能超越社會客觀結構的制約。
看起來連成一片的液體,在高倍顯微鏡下看其實是由許許多多分子組成的。許多瞬間即逝的藝術團體以往就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聯合一一人員的聯合,而非藝術理念、藝術作品上的聯合,還有不少只是把他們各自的作品放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合作最終導致不少藝術家團體也慢慢銷聲匿跡。然而,成立團體對年輕藝術家來說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模式,新的媒介也為需要更為強勁的聯合來滿足如今藝術家的需求。至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有更加多的集合型藝術,小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