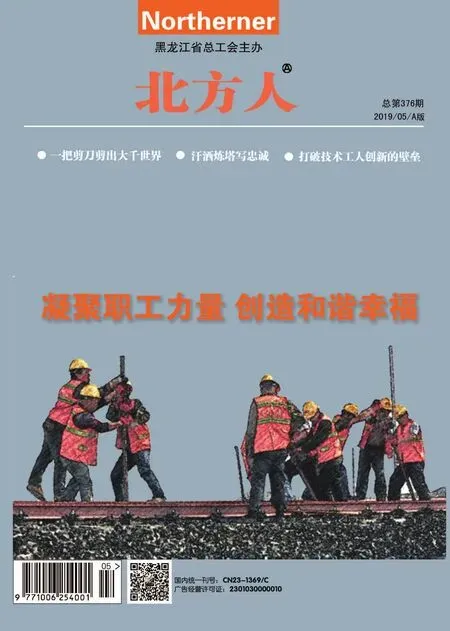人間有味母愛無邊
文/綠蘿姑娘
每每回老家,我都能實打實地胖上幾斤。
老媽很能干,廚房是她大展身手的舞臺。灶上的十二印大鐵鍋威風凜凜,灶下的柴禾“豐儉由人”,火力控制自如,加上老媽一手好廚藝,飯桌上我們一家人的表現猶如饕餮下山。
在我小時候,老媽做完飯,就著灶下的余熱,或是扔進去幾個土豆,或是燒幾根粉條,如果是孵雞鴨鵝的時節,中止生長的“毛蛋”便是最美味的“灶下小食”。
那時,冬季全靠秋儲土豆、白菜、大蘿卜等捱過漫漫長冬,生活捉襟見肘,這些菜也得規劃著小心地吃。有一年,老媽“開發”出一個新菜式——將干辣椒在火塘里烤至輕微發黑、散發出香味,剁碎后放蔥花、調料等調味,味道出奇地好,非常下飯,就著它,我能吃三個大饅頭!那兩年,這道菜成為飯桌上的“常青樹”,解救了深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老媽。
春節前幾周,緊鑼密鼓地,老媽開始一鍋接一鍋地蒸饅頭,包上幾大盆黃米面的豆包,炒上半袋子的瓜子,炸上幾紙箱的丸子、麻花——面粉,是自家種的麥子用機器磨的,老媽省吃儉用,閑時吃黑面,年節時吃白面;包豆包是個大工程,親朋近鄰互相幫忙,這時就看出了老媽的好人緣,熱鬧非常,而我們姊妹倆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說到炒瓜子,這可是個技術活,而春節期間嗑著瓜子嘮著嗑兒是親朋串門時的日常,炒瓜子的水平也是關乎家庭主婦們面子的大事,老媽自然上心,往往也收獲交口稱贊;小時候物質匱乏,唯獨不缺豆油,種的大豆榨出的油用缸裝,很是豪氣,但也只敢在過年時精打細算地炸上一回……兒時的春節,幾乎演化成對吃的企盼,老媽是這場劇目的絕對主角。

待萬物回春,泥土清香開始往鼻孔里鉆時,便是我們小孩子的主場。我和妹妹帶上鐮刀頭,挎上小筐,在田間地頭、草甸子上撒著歡兒跑夠了,就隨地一坐,婆婆丁俯拾即是,專挑嫩的挖。老媽將婆婆丁在井水里淘洗干凈,在菜園子里薅幾棵春蔥,支使我們去醬缸里舀上一碗大醬,或是打飯包,或是直接三卷兩卷直接蘸醬往嘴里送,嘖嘖,甭提多香了!
說到大醬,因為要經常性地“懟它”,這也是我們小孩子十分熱衷的“娛樂項目”:天氣好時,揭開醬缸蓋布,拿著醬耙子在里面上上下下地杵來杵去,將其全面地“活動”一番,很有意思。
每家做的大醬味道都不一樣,小朋友之間也經常拿這個比來比去,總覺得自家的最好吃,我也不例外。大醬的味道也是媽媽菜的味道,它延伸到醬茄子、土豆醬等美味佳肴上,成為我舌尖上的媽媽味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今,就像其他失去的傳統一樣,大醬幾乎沒人做了,超市里琳瑯的各種醬取而代之。如今回老家,醬只是醬,不禁若有所失。
如今,我們姐妹相繼成家立業,家,成為娘家,偶在年節時才與它產生交集。過去勤儉持家供養我們的老媽又開始對我們在老家的每一頓飯“精打細算”,愛吃的,想吃的,都盡可能讓我們吃個遍。如果哪個親戚約飯,老媽便黯然,我知道,她只是想讓我們多吃一頓她做的飯,就像從前,我們依然圍繞在她身邊,在飯桌前巴巴地等著,然后吃得肚子溜圓……
雖然缺吃少穿,但我擁有一點兒也不比別人差的快樂童年。老媽對我們的愛如果說是一道菜,外觀看似平淡無奇,甚至土里土氣,卻滋味十足,熨帖了我的胃,且滋養著我未來的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