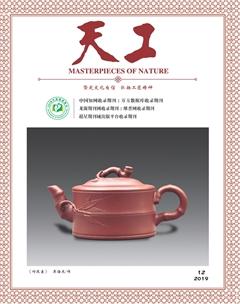情系發色美 匠心繡精品
[中圖分類號] J523.6? ? ? ? ? ? [文章標志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5-7556(2019)12-0038-02
本文文獻著錄格式:劉振蘭.情系發色美 匠心繡精品[J].天工,2019(12):38-39.
刺繡藝術是與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傳統技藝,無論服裝、鞋帽、玩具,無所不包,種類繁多,地方色彩濃厚。我國刺繡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遠古時期由于生活的需求而產生了實用性刺繡。
刺繡,又名“針繡”,俗稱“繡花”。以繡針引彩線(絲、絨、線、發),按設計的花樣,在織物(絲綢、布帛)上刺綴運針,以繡跡構成紋樣或文字,是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工藝之一。古代稱“黹”“針黹”。后因刺繡多為婦女所作,故又名“女紅”。據《尚書》載,遠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規定“衣畫而裳繡”。至周代,有“繡繢共職”的記載。唐宋刺繡施針勻細,設色豐富,盛行用刺繡作書畫、飾件等。明清時封建王朝的宮廷繡工規模很大,民間刺繡也得到進一步發展。
魯繡是一種古老的傳統刺繡工藝派系,春秋戰國至漢代,山東是比較發達的地區,漢代山東設“三服官”生產皇室服裝的剪裁縫紉銹制。它是起源于民間的縫紉藝術,被皇家利用走進大雅之堂。它根植于民間,并流行于民間和人們的生活、信仰聯系密切,是山東地區代表性刺繡,是歷史文獻中記載較早的一種繡種,從而具有不斷發展更新的生命力。
一、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創新
筆者從事魯繡30多年了,自幼受祖母、外祖母和母親的影響深深喜歡上繡花。初做繡花所用的線,大多是比較粗的加捻雙股絲線,俗稱“衣線”,故稱“衣線繡”,多在布上和鞋墊上繡,所繡的是花鳥魚蟲、福祿壽喜等一些簡潔吉祥圖案花樣。由于執迷于魯繡,17歲時母親讓參加煙臺蓬萊刺繡學習培訓班,通過學習理論知識加上實際操作,刺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掌握了解魯繡的風格較它不同,多以暗花織物做底襯,以色彩強,捻雙股衣線為繡線,采用齊針、打籽滾針、數和針、接針等針法,題材選取民間喜聞樂見的人物、山水、鴛鴦、蝴蝶、牡丹和芙蓉花等。
發繡博采“蘇、粵、湘、蜀、京、魯、汴、甌”八大名繡之長,而又獨具一格,是中華民族悠久的刺繡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集抽、勤、鎖、雕等精華工藝于一體,色彩淡雅,構圖優美,虛實適宜,形象逼真,錦遠悠久的齊魯文化賦予魯繡濃郁的地方特色和豐富的人文內涵。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嚴謹細膩、光亮平整、構圖舒朗、渾厚圓潤、色彩明快的獨特風格。魯繡作品的選材豐富,有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山水魚蟲、人物肖像等。針法包括12大類共122種,常用的針法有暈針、鋪針、滾針、截針、摻針、沙針、蓋針等,講究“針腳整齊,線片光亮,緊密柔和,車擰到家”。繡品的種類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畫屏等,既有巨幅條屏,又有袖珍小件,是觀賞性與實用性兼備的精美藝術品。
發繡技藝是民族精神的長期積淀,是民族形式的靈魂之所在,是東方文化的一處獨特景觀和寶貴財富,它題材廣泛、內涵豐富、形式多樣、流傳久遠,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替代的。2002年開始接觸研究發繡,從題材上、技法上大膽嘗試創新,作品主要以寫實性和真實感為長,常常偏重形式表現,改革開放以來,受市場經濟影響,發繡作品更加趨向于定勢化制作,簡化技藝、刻意繁復、矯飾堆砌,特別是題材上基本靠拿來主義,從原來專門制作繡稿,變成直接用畫稿,風格千篇一律,刺繡針法僅僅是復制畫面的一種手段,刺繡核心語言的“針、線”喪失了應有的獨立審美價值,個性創作越來越少,若繼續模式化運用技法,會逐步淪為簡單的工藝品生產,失去文化傳承的意義。魯繡是山東省級和濟南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傳承應積極開展生產性保護、創新性發展,生產性保護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商品開發,而是強調“生產過程”,關注體現“非遺”核心技藝和文化內涵。魯繡既是物質產品又是精神產品,要想更好地繼承和發展,必須遵循生產規律,從歷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質著手,不能單純追求數量、規模、速度,而要在傳統技術的基礎上,強調作品形態、質量、品味,只有將前輩的技藝和生產中的創新融合起來,魯繡的技藝、風格才會發揚光大,才能開辟出一片新天地。
當代藝術已經從崇尚逼真的具象作品發展到重視精神呈現的抽象藝術,強調人與自然、主體與對象、主觀與客觀、感性與理想的和諧統一,強調一定的文化法則,把多樣或相反的因素構成一個融匯的整體。這些年來,筆者一直在思索和嘗試魯繡創新,如何將傳統手工藝與現代藝術潮流、民族地域特色等文化內容融合起來,最終選擇大寫意山水畫題材作為突破口,在繡制《龍鳳牡丹》《麒麟送子》《喜鵲鬧梅》《摩天振羽》作品時,按照繪畫作品,充分利用了發繡的獨特優勢“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的特點。繪畫一筆,繡工千針,一般刺繡都選擇線條輪廓、粗細、絲理、配色都有一定規制的題材,而寫意畫講求“筆墨縱逸,不專規矩”,不論從刺繡本身的工藝要求,還是制作材料的針和線,在這類題材處理上都有巨大難度,寫意畫既是高度自我的藝術,又是高度忘我的藝術,不受時空、體面、光色透視等物理現象的束縛,追求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極高境界,敢于超越客觀物象世界,表現人的精神之情,是一種生命的自覺。作品激揚奔放、波瀾壯闊、富有意境,讓發繡在傳統中融入現代的元素,融入對所處時代和社會生活的記錄與思考,融入人們在精神審美上的新渴求。
特別是《齊白石老人與蝦》《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人》《鵲華秋色》《寒雀圖》《雙駿圖》《柳蟬圖》等作品,在繡制過程中,筆者對工藝方法、布局設色、表現形式等多方面突破了傳統發繡的界限,同時博采眾長,汲取各個繡種的優勢,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對針法、技法、色彩應用不斷進行調整、創新、重組,既保持繡面順、齊、平、勻、潔,又能符合寫意畫中用筆的規律和美學原則,體現筆墨的力度和美感,表現作品的節奏、韻律、動態、氣勢、性格、意趣,總結起來主要有繡神、繡性、繡心、繡精、繡氣。
二、當隨時代的需求精益求精
在創作和制作時,首先是對作品范本進行研讀,由表及里多層次地深入探討,從工具材料、形式構成、構圖章法、筆墨技巧、色彩運用、個性風格、意境處理、審美觀念等分門別類進行剖析,具體研究,然后針對性修改,做到繡、畫完美結合。傳統魯繡制作時,要將選好的面料固定重疊在摹本上面勾描,不但要畫出塊面構成形狀,還要畫出景物或物體的色彩明暗、層次出來,講求的是對畫稿的復原,個性創作很少,而這幅作品講求活臨,上稿時只做區域劃分和主線條勾描,刺繡時不必看一眼繡一針,掌握好繡稿的精神和筆意即可,做到繡意不繡跡,突出偶然性效果。在具體處理上,一方面要考慮整體效果顯現,另一方面要有鮮明的技藝特點。采用對山勢輪廓加深線條,云彩、水波加重冷暖色調對比方法讓畫面更符合刺繡方式。針法上創造車擰針開放法,絲毛針、二三針變化拆分法,讓基礎針法完全變化,山石用二三針加車擰針,天空和云彩平交又加暈針,云霧用二三針、三三針加覆蓋針,水波用斜三角針、亂針加絲毛針,結合過渡部分利用暈針暈染。作品整體藝術效果,虛實得體,“平、浮、突、活”,在勾勒中變幻,明暗襯光,畫面更為細膩、層次更為豐富,充滿活力。繡與畫最大的區別就是畫有筆力,筆力為骨,如果刺繡時對線條只是簡單的堆線順方向處理,就變成了呆厚的打補丁,非常難看,筆者采取線向根據筆力區別走向方式,呈現水墨輕重關系。起筆時線向左右傾斜兩側平;筆腰時變化較多,線向順內側傾斜一面平一面散狀;收筆時線向順方向前密后松,散筆部分暈染為主,線向中心向外擴展長短不勻。此外水墨畫講求墨分六彩,作畫可以用水不同來區劃,刺繡時只能用摻色來區分,墨階大體可分為焦、濃、重、淡、清五個階梯,焦部分摻入金色線,線剖三絲,三線摻一;濃部分摻入灰色線,線剖二絲,五線摻一;重部分摻入紫色線,線剖二絲,六線摻一;淡部分摻入白色線,線剖二絲,二線摻一;清部分摻入銀色線,線剖二絲,二線摻一。其繡品不僅有服飾繡品,有觀賞性的藝術品,更多的是實用工藝美術品。
但是我們正處于一個現代化、信息化的社會,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不斷涌現,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如果一味拘泥于傳統,沒有推陳出新,必將導致魯繡發展的停滯,必須通過創新,豐富技藝本體,在“傳統”與“現代”間找到新的平衡點,利用現代的審美觀點,為發繡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發繡技藝的傳承不是簡單的照抄照搬,而是對傳統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是在理解的基礎上,以現代的審美觀念對傳統加以改造、提煉和運用,使其富有中國特色、體現民族個性。無論何時,人們追求美好的生活不會變,對美和文明的創造也永不會終止。因此,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創新,從而適應新的社會需求,迎來新時代的機遇。
[作者簡介]
劉振蘭,生于1966年11月,濟南人,中國華僑藝術研究院刺繡藝術主任,山東省弘正傳統文化研究院工藝美術委員會副主任,高級研究員,山東省工藝美術協會理事。自幼受家庭影響接觸刺繡,1987年去蓬萊市參加刺繡培訓,1989年在鎮企業毛紡廠專職刺繡,2011年建立雅蘭繡坊工作室至今。2016年在歷下公益大講堂“非遺魯繡”擔任授課教員。2017年10月擔任濟南市殘聯愛心驛站魯繡文化創意培訓班教員。
第十屆中國(山東)工藝美術博覽會發繡《盛世八駿圖》《潑墨仙人》分別榮獲山東省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和銀獎,在第54屆全國工藝品交易會上發繡《蕃女摯龐圖》榮獲“金鳳凰”創新設計大賽優秀獎,《殘雪》在第二十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暨手工藝精品博覽會上榮獲“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銅獎。
(編輯:劉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