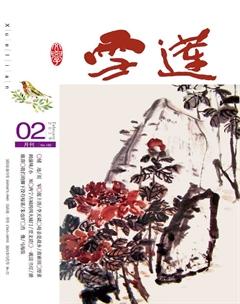我是農家的一炷煙
李光彪
我出世于鄉村農家,生活在滇中彝州,在眾多的農作物中,烤煙仿佛是我的兄弟姐妹再熟悉不過的穡稼了。
自從有記憶開始,就聽父母們講,烤煙是洋貨,是從國外傳來的。老家種煙,則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供銷社從玉溪請來師傅,手把手教會的。
那時,我差不多只是個煙筒高的小孩,常被父親使喚:“小六,去把煙筒提來,爹吃鍋煙”。雖說是提,其實是抱。因為那支常年靠在墻旮旯里的煙筒又粗又大,里面還盛著水,有好幾斤重。每當我把煙筒抱到父親手里,父親總會眉開眼笑,露出一排虎牙夸我:“有出息,爹下次交煙時買糖回來給你吃”。只見父親一邊夸我,一邊用手捻一團自己切的煙絲,塞在煙筒哨子上,邊燃火,邊鼓著腮幫,“咕嘟、咕嘟”吸個不停。一陣吞云吐霧,兩股火煙從父親的鼻孔里噴出來,仿佛那農家灶房頂上飄出的裊裊炊煙。難怪母親常說,我家有兩棵煙囪,一棵是煮飯灶上的煙囪,另一棵則是父親的煙筒。
母親形象的比喻確實如此。全村四十幾戶人家,家家都有樹鑿的、或是鐵皮做的、或是膠皮管做的、或是竹筒做的,各式各樣的水煙筒。多的三、四支,少的一、兩支,不僅男人吸,而且部分女人也會吸。一到集中開會,不約而同,各自帶上煙筒,整個會場就像是在進行有趣的吸煙比賽,傳來遞去,輪換吸個不停。如果男人不會吸煙筒,便會遭人諷刺:“人閑煙受苦,男人不吸煙,白來世上蹲”。如果男人一口吸不完一鍋煙,咳咳卡卡,證明技術不高,沒有本事,便被人瞧不起:“不昌盛的,沒出息”。諸如此類,還有更多“飯后一鍋煙,賽過活神仙”、“吃煙有煙錢,吃酒有酒錢。”的種種鄉諺口傳不絕。吸煙筒成了衡量男人的本事,主人生活的象征。就連有客登門,也要先敬煙筒,后泡茶,再做飯菜待客。看煙筒的大小,好中差,自然也就明白了主人家底厚薄,生活苦樂。
大概是父親煙癮大的緣故,生產隊專門安排他當師傅,烤煙葉。那烤房是全村最高、像座雕樓似的建筑,矗立在曬場上的倉房旁,被村里人稱為“銀行”。一桿桿青黃色的鮮煙葉分層、分臺裝進去,經過五、六天的烘烤,就變成了黃爽爽的煙葉。出爐后,分級、扎把,賣給供銷社,就變成了全村人年底計工分紅的救命錢。父親會烤煙葉,受人敬重,我常到烤煙房里玩耍,不時有人到烤煙房里來就火燒包谷、燒洋芋吃。見者有份,我沾了父親的光,總是能吃到別人分給的噴香火燒包谷和洋芋。
烤煙葉并不輕松,從煙入爐點火開始,就要日夜廝守,不能走遠。而且也要技術,就是父親常說的“小火溫、中火升、大火猛”,地洞、天窗,該關則關,該開則開。每道環節,都要視煙葉水分的干濕程度,不斷進行調整,才能烤出好煙,讓辛辛苦苦種成的煙葉,不雞飛蛋打,有個好收成。
烤煙是農作物中最難服侍的莊稼,幾乎與一年四季的農活都有關。平時,要堆捂上等的農家肥;春節前后,要用最上等的地育苗,精心澆水、打藥;開春,又要鏟火土,煉草木灰;栽時又要細垡、理墑、打塘、兌營養土、蓋農家肥、澆水。幾場雨過后,煙苗又要鏟雜草、松根、施提苗肥,或是提溝壘墑排水。一直要到夏末初秋,煙葉才逐漸成熟,可以陸續采編、入烤、分級、扎把,變賣成錢。付出的辛勞,不亞于“粒粒皆辛苦”的盤中餐。若是年成不好,遇上干旱、洪澇、冰雹、颶風,全村的烤煙,一年僅幾百塊的收入,即便風調雨順,也只不過幾千塊錢。盡管如此,烤煙始終是全村人唯一的生財之道,還得年復一年,廣種薄收,讓全村人多有分紅的希望。
進入包產到戶后的八十年代,農民獲得了土地的自主權,家家爭先恐后擴種烤煙。那時,我已是十多歲的少年,按照父母的教導,要穿衣、上學,甚至要娶媳婦,要住新房,樣樣都必須從種烤煙發掘。于是,我家一下子種了好幾畝煙,除了那些常規的生產措施外,要各自新建烤房。砍椽梁、抬木頭,背石頭、脫土基砌墻,一泥、一石、一瓦、一木,累得一家人叫苦連天。但為了發家致富,全家人還是要年復一年種煙。
種煙也曾讓我飽嘗辛酸。令我非常費解的是那些曾經讀過的課本,做過的作業本,被大人當作廢紙,裁粘成紙袋,裝上營養土,插上烤煙苗,埋進煙地里,化為烏有。令我最痛苦的卻又是澆煙苗。栽煙時節,紅火辣日,放學回家,或是放假,常被父母安排去參與栽煙,幫大人做些放化肥、放煙苗、蓋糞之類的輕巧活,一直干到星星點燈,雞棲蟬鳴,才摸門進家,得吃晚飯。若是遇上干旱,長時間不下雨,栽下去的煙苗要保住,還要挑水澆,幾十挑水,雖然只盛著半桶,但都要從我肩上擔過,讓我變成了初上架學拉犁的牛,肩頭又紅又腫,沒過幾天就脫了一層皮。沒辦法,父母只好找幾只平時裝酒的塑料桶,讓我用竹籃背,一瓢一棵,去澆那些長滿誘惑的烤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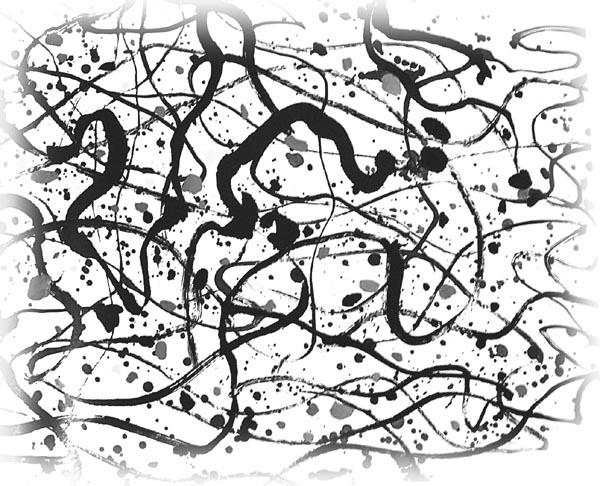
在種煙活中,令我最討厭的是采摘入爐要編的煙。父母把采摘的鮮煙葉碼柴似的垛起,潑上水,由我不停地像個售貨員,一葉一葉遞給他們編桿。不知不覺,那看不見的煙油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粘得我雙手漆黑,就像糊了層狗屎、牛屎。直到煙葉編完入爐,手上的煙油哪怕是用泥砂搓,石頭刮,洗衣粉、肥皂洗,也只能洗過大概,要好幾天才會消失。剛洗凈,下一茬煙葉采編入爐又開始了,我依然只好悶悶不樂地上陣,夢想著有一天自己能像遞煙葉一樣數錢。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轉眼幾年過后,烤煙越種越多,村莊越變越大,“大鍋蓋”的電視也越來越多,我也長大成人,外出求學,疏遠了種煙的活計。只有每年暑假回家,才有機會打打幫手,父母看我白嫩嫩的手,干干凈凈的穿著,不想再讓我參與采煙、編煙、理煙。但我明白,一年在外讀書,要花去的幾百上千費用,大部分都來自于父母手下種的煙,賣的錢。此時此刻,我對煙的敬意,油然而生,總是不聽父母的勸阻,幫家里做些有關烤煙的活計,再累也心存感恩。
吃盡了種煙的苦頭,換來了生活的甜頭。烤煙讓我脫掉布鞋、穿上皮鞋,換下羊皮、裝上西裝,一躍昂首走進城市,過上了坐辦公室、抽黃屁煙的生活。慢慢的才知道,自己家鄉是個農業縣,烤煙是全縣的支柱產業,是農民增收、財政增長的主渠道,就連自己養家糊口的工資也與烤煙息息相關,經常參加一些有關烤煙生產的會議和督促、檢查工作。因自己有過種煙的經歷,所以,說出的話還基本在行、不離譜。尤其是烤煙“雙控”剛開始那些年,長期習慣了粗放經營的農民意見很大。我就任鄉黨委書記,每年種煙、訂合同,都要動用不少干部,苦口婆心,說不少煙話。才使得管轄范圍內的烤煙創下新高,成了全州推廣示范的典型,并為我后來一路走好奠定了關鍵一步。
種植烤煙半個多世紀,改革開放四十年,風風雨雨,歷經滄桑,烤煙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設新農村也好,總體實現小康目標也罷,農家的生活,農村的變化都離不開煙。可喜的是,隨著烤煙生產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政策措施扶持力度越來越大,一年一個樣在變,有了統一、集中育供的大棚漂浮商品苗;有了千畝連片,承包土地種煙的農場式老板;有了不用柴、不用煤,而是用電烤的上百座連體集群式烤房;有了減災防雹的保險措施。農村已初步探索出了一條與當前農村產業結構相呼應的路子,打開了現代煙草產業蓬勃向上的前端,開啟了現代農業陽光燦爛的標航。
我是農家的一炷煙。是烤煙一直牽扶著我走過童年,走出困苦,令我感激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