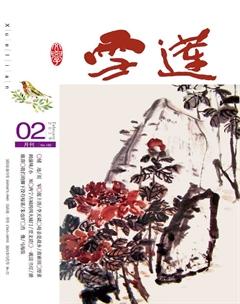故鄉是座城
崔元成
一
如果說大地是一片碩大無比、紋理分明的樹葉,那么故鄉就深藏在這神秘的紋理之間;如果說這片樹葉是由西北向東南在逐漸變綠,那么故鄉就在接近綠的邊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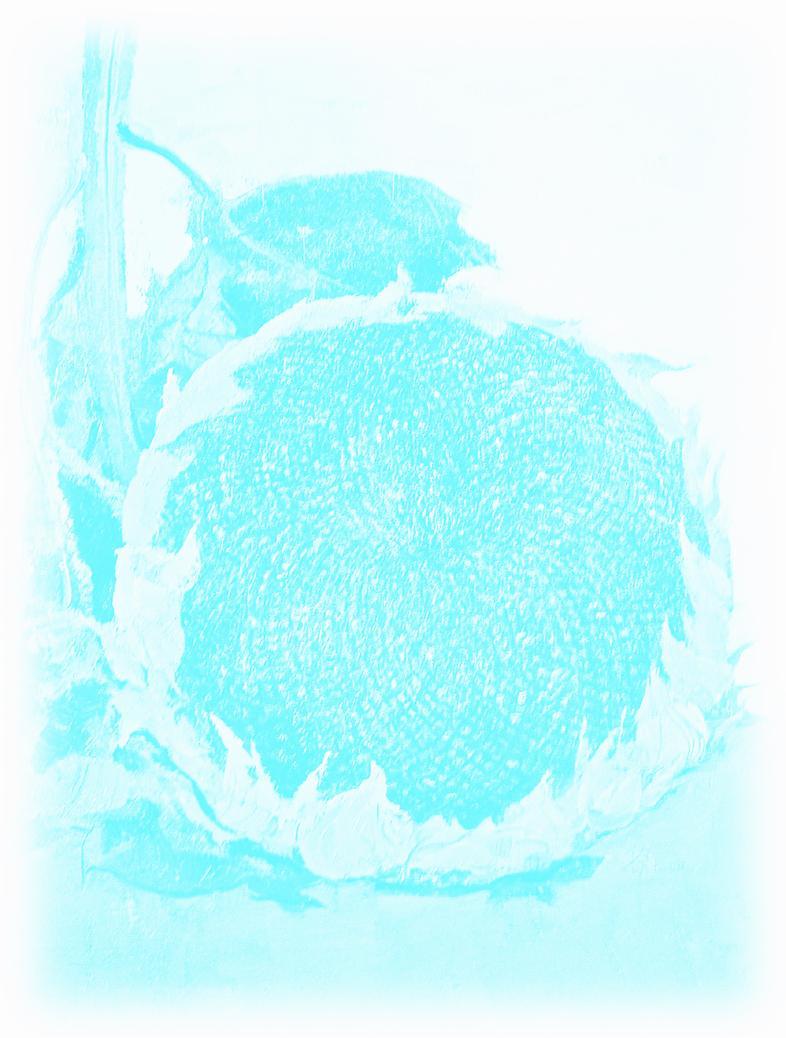
那是黃土高原上看似極為普通的一個村莊,安靜地臥在陜北的塬上,可是村子中央郁郁蔥蔥的古槐和波光粼粼的澇池絕對是方圓百里罕見的風景。古槐下的空地上總是聚集著村民:或者是須發蒼蒼的長者坐在麥稈編制的草堆上講述著遠古留傳下來關于先輩的神奇往事;或者是客居都市的叔伯歸來小憩的功夫在描述著鮮為人知的山外世事;還有剛從收音機里聽了新聞就急著出來和大伙討論國家乃至國際大事的。說到興起驟然同時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嚇得老樹枝頭上的老鴰撲棱棱地飛走了。如果老槐樹下是男人們的舞臺,那么澇池邊上則是留給女人們的天地。上了年紀的老人多是坐在澇池畔的石巖上一邊做著零活一邊聊著家常,年輕媳婦們則不約而同地拿來家里要洗的衣物坐在澇池邊上儼然是鑲嵌給明鏡的花邊。她們又是洗衣又是說笑,甚是熱鬧。漂洗衣物時甩出五顏六色的花布竟然招來蜂蝶圍觀!而那拋甩衣物的優雅動作、瞬間飄揚的炫麗不是故鄉最美的舞姿么?過路的行人往往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兩眼這個途經的村莊。記憶深處,故鄉總是這個永恒的畫面。
那時我正在村里念小學,學校就在澇池畔下來走幾步就到的那個祠堂對面。老師那時常對我們說,娃兒們,好好念,你們的先人在看著吶。我們村是這方圓數十里內唯一的一個大村子,學校設育紅班至五年級六個年級一共一百多個學生,下課的時候一窩蜂似的撒在校園里,自然比澇池畔古槐下熱鬧多了。上課的鐘聲一響,教室里又擠得滿滿的。我們的教室是那種大房子,一間房子安排兩個年級。我念育紅班,和五年級同在一個教室。記得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的課程沒有意思,就經常聽五年級的課程。晏子使楚的故事最早就是那時候聽來的。這雖然是一個普通的鄉村學校,但是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從這里出去的娃娃有的考到了省醫科大學,有的考上了外省的研究生,他們是娃娃們學習的榜樣,更是村莊的驕傲。
為了娃娃們能夠念書,鄉親們付出的決心是驚人的,父親就是他們其中的代表。父母一年四季省吃節用,可還是最擔心開學的日子。村里教書的老師都是認識的,學費也不貴,實在沒有錢還可以賒,可是在鎮上、縣上上學就難了。為了湊齊學費變賣農副產品、糧食是司空見慣的事,向親戚借錢的情況也不少,甚至借高利貸的情況也有。總之為了我們念書想盡了辦法,受盡了煎熬。好在我們遵從父命還是在最困難的時候熬了過來,最終沒有讓家人失望。
故鄉崇尚文化是出了名的。據有關文字記載,清朝嘉慶至道光年間,村莊單是某姓人中就出了八個秀才。偏遠的的西北山村啊,四五十年間竟有如此之多的讀書人榜上有名,談何容易?誰說“上帝布道此處偏遺漏”呢!自我記事起,村莊一直保持著不羨慕誰家錢多糧足只羨慕誰家有識字人的樸素傳統。又說那時候有個公社干部仗著自己身份特殊,給村民講話時不注意言辭鬧了笑話,當場被反問得無言以對,從此以后,政府無論選派駐隊干部還是民辦教師,都是挑了又挑才決定的。故鄉名聲在外,我們偶爾去了別的村莊,當被問及來處,當地人于是無不恭敬三分。
記憶中的故鄉更是繁華的。水池子邊的老雷是石匠;西窯窟里老樊是木匠;上坪里磚瓦窯里爐火旺盛;老王家里磨面機、榨油機、彈花機長年運轉。莊里幾百口人,單是商品代銷點就有四五家;村莊雖然不是公社所在地,卻是方圓十里的交流中心地帶。公社通知開現場會有時會選在這里召開;不時有小商小販做生意來村里一待就是十天半月。尤其是村里來了放映電影和說書的,周邊村莊的人們不顧一天的辛勞星夜趕來觀賞,澇池畔上的人經常是黑壓壓的,連過往的小路也淹沒了,第二天早上古槐下的廣場上竟然落了一層厚厚的瓜子皮,故鄉因此成為遠近聞名的鬧地“小城”。
二
村子中央的古漢槐,樹身粗六摟(六人合抱),高三十余米,雖然歷經滄桑卻依舊蒼勁挺拔,酷似洪洞之祖。要問古槐植于何年,恐怕早已無從考證。據村里年齡最長的老人說他小的時候記得古槐就是這般模樣。古槐是方圓百里長得最茂盛的,也是最有名氣的。有意思的是澇池和古槐一樣也是方圓百里很有名氣的,更奇妙的是澇池底部是一口石材質地的酷似巨型做飯鐵鍋的物件。先民曾用來寄托鄉情的古槐啊,和這世上最樸素的水利工程澇池共同見證了村莊久遠的歷史,共同構筑了村民心中家園的地理標志。老人還說村中關帝廟里曾掛有明代所鑄的大鐘上已經有村名記載。據相關文字記載,清朝末年村莊尚有“德盛源”號商鋪。遙想昔日,故鄉先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商賈往來,又是何等的昌盛!
我們家族也算是村莊里的大戶人家,曾經光景一度還算殷實。聽家人說那年月黃河經常泛濫遭災,不時有河南安徽乃至山東的難民流落故鄉,好心的族人總是善待這些流浪他鄉的落難之人,若是路過家門,讓他們吃飽喝好歇息繼續趕路;若是愿意留下,則提供食宿幫助落腳。先輩的為人和美德,城鎮年長者皆知;頌揚文辭,現代網絡可以百度看到。前年還有外省故人專程趕來看望第二故鄉。
國家安定家庭才會興旺,城門失火必然殃及池魚。不幸同治六年,西北回民造反波及故鄉,一場浩劫隨之而來。周邊村寨紛紛被相繼攻克,岌岌可危的村民全部躲藏于東邊的寨子。說是寨子,其實沒有一磚一瓦,僅僅是個四面全為陡崖絕壁易守難攻的土臺而已。“亂匪”無奈,只好終日包圍。時間一久,情況甚是危急。緊急關頭,聰慧勇敢的村民趁夜色從后寨吊下幾人,火速從外村購得兩門鑄鐵火炮,隔溝打死一個“亂匪”,半月之久的圍困才得以解救。就這樣村民靠著勇氣和智慧堅守“孤城”,打退了來犯之匪,守護了家園。時光流逝,而村民這守衛家園的傳奇故事早已成為全村人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烽煙時代需要英雄,英雄的精神更需要薪火相傳。五四運動后,紅色革命火種迅速以燎原之勢傳遍大江南北。故鄉地處紅白交界邊緣地帶,不斷遭到土匪騷擾,期間曾經涌現出無數英勇的先輩,他們憑借超人的膽識和智慧赤手奪槍的事跡是我們兒時最喜歡傾聽的故事。小說《最后一個匈奴》主要人物原型、赫赫有名的黑憲章就是在離村莊不遠的后九天寨子開始了革命生涯;解放戰爭時期,畢業于延安抗大的我族先輩遠赴太行,為解放山西運城而血灑中原他們的肉體和精神將與故鄉同在。永遠是村人學習的楷模。故鄉是座城,他們就是城頭迎風飄揚的旗幟,永不褪色!
皇天后土,人杰地靈。哺育了無數英雄兒女的這片神奇土地,早在北周時期已經設立縣制,縣城建在距我村僅十里之遙的門山村,故稱門山縣。當地縣志記載:北周建德六年(577)分云巖、汾川2縣地設門山縣,屬丹州樂川郡,治所在今門山村南6里。歷經一千四百多載風雨滄桑,豪華樓宇街市皆隨風雨而去,古城僅留給后世一段城墻遺址。遺址長30余米,底寬5米,高7米許,通體為白膠土夯實而成,堅硬無比。一段厚實的城墻,展現北朝紛亂景象中,北周橫掃六合稱雄北方的霸氣。
三
城池所在,文明之至。雖幾經變遷,文明教化遺風猶存,古老傳統文化的底蘊勢必影響著周邊村落,先民風范的傳承必澤及后人乃至被傳頌弘揚。
先輩歷來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終有回報。而今村里各層次級別官員已不罕見;碩士、博士研究生、科教文衛人員眾多。雖然他們遍布四方,但是每年時節固定或不固定,年幼或者年長,成群結隊或單獨一人,必然回鄉小住幾天至少逗留片刻,必然是要看望親朋或者祭祀先祖的。
某日我在客居小城偶遇同縣鄉黨閑聊。談及各自村落,鄉黨說一次回鄉曾路遇一蒼發老者迷路。問及前往何地,回答說常年客居他鄉竟然忘記回歸之路,于是他驅車送至我村。老翁不遠萬里,四處打問,只為回歸祭祖先靈的精神感人至深,頗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味道,鄉黨用行動踐行“鄰人遙指某某村”的助人為樂精神更是值得褒揚。
今逢國泰民安,美麗鄉村的創建使古樸村落愈加青春煥發。村莊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百年古槐依舊茂密蒼翠,澇池仍是潭水悠悠。村莊老人悠然頤養天年,孩童欣然享受免費義務教育,青壯年各謀其事,公務員有之,開公司當老板有之,跑運輸攬工程有之,新時代農民亦有之。寬帶網線早已拉進莊戶,電子商務的觸角無限延伸,農民富裕的道路又多了一條。此情此景,恰似陶潛筆下的桃源勝境,又遠遠勝過。
物質生活的豐富,自然不敢忘記祖宗的養育之恩。前年有村民倡議重修祠堂,以昭先祖之神佑,一呼而得百應,群策群力,祠堂很快竣工。莊里隆重擺設筵席三天,引得四方兒女前來慶賀,盛況自然不必言表。憶往昔,曾經是那么千方百計地想離開故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真正在都市生活的久了,總是覺得缺點什么,于是現在又常想著回故鄉看看。原來是記憶和靈魂在召喚!
故鄉是心靈的港灣,故鄉是永遠的精神家園,故鄉更是我輩奮斗的精神城堡。當在外面受了挫折,就想想故鄉厚實的城墻吧!想想故鄉那些令人驕傲的先輩吧!一個人之所以能夠走得更遠,也許就是因為血液里與生俱來的文明因子和自信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