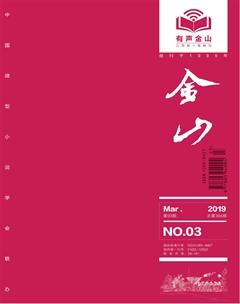小城觀音橋巷55號(hào)的廣播故事
張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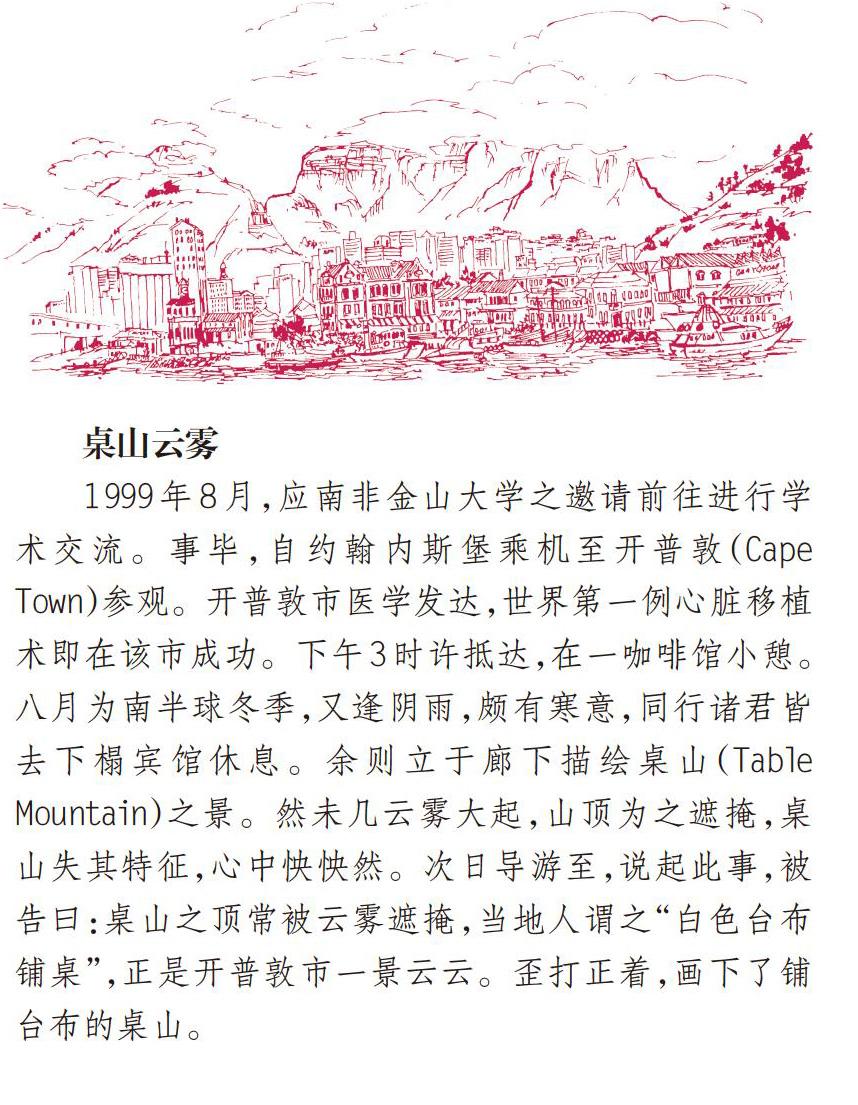
從樓說起……
話說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離小城市中心最近的地界能有這棟樓已經(jīng)了不得了。最高也就三層,占地面積不大也不算小,可足以讓小城人民仰視,因?yàn)樗Q得上是這座城市的的刮刮的“上層建筑”。
“廣播站”對(duì)小城居民來說,神圣而莫測,好奇而敬仰。家家戶戶都被裝上了方方正正的“廣播喇叭”(木匣子)。一根開關(guān)線垂直下來,拉著拉著,日子久了,多半兒線被扯斷。這只貌不驚人的“木匣子”兼著鬧鐘的作用,開啟著小城居民的起居生活和小城大事。
能進(jìn)進(jìn)出出這棟樓的人,不是小城的一般人,或多或少有點(diǎn)來頭、有點(diǎn)講究、有點(diǎn)說頭,即使一般進(jìn)來,也會(huì)不一般著走出去。
這棟樓的前身肯定不是為廣播量身定制的,單從廣播機(jī)房和播音室的隔音效果就能看出來。前樓為辦公區(qū),后樓為機(jī)房區(qū),兩樓之間,不大的空間像一個(gè)樓道里的天井,用不著電話聯(lián)絡(luò),喊上一嗓子,該聽到的、不該聽到的都聽到了。
逢年過節(jié),臺(tái)里發(fā)年貨,幾輛卡車駛?cè)耄纫话矗k公室主任一嗓子,全樓震撼。隨后,從各個(gè)辦公室涌出人群,聚集到樓下一臺(tái)磅秤跟前,不是雞鴨魚肉,就是水果禮包。除了樓下的人頭攢動(dòng),小樓陽臺(tái)上,齊刷刷排成一溜邊,看著“年貨大軍”的熱鬧。
相比起來,后樓比前樓更莊嚴(yán)、更神圣,也更詭秘。
因?yàn)槟抢锸菣C(jī)房,播音重地。所有的新聞、專題稿件,由前樓新聞部編輯完成,送交后樓播音室,經(jīng)錄音室制作,由機(jī)房播出。
如此,看似尋常單調(diào)的廣播技術(shù)流程,承載著小城政府和幾十萬聽眾的衣食住行、生計(jì)民生、時(shí)事風(fēng)云和藝術(shù)鑒賞。
每天有太多的人,專程摸到小樓跟前,駐足觀望,捧出自己虛擬的想象與這棟小樓對(duì)比、印證。在他們心中小樓始終是一個(gè)很難釋懷的謎面,小樓寄托著他們所有的喜怒哀樂、前程理想、愛恨情仇。
小樓有點(diǎn)類似小城新聞界的“黃埔軍校”,一屆一屆,從這里進(jìn)進(jìn)出出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流向各個(gè)領(lǐng)域,登上各個(gè)階層。
后來,小樓從“廣播站”升格成“廣播電臺(tái)”,“木匣子”漸漸演變成半導(dǎo)體收音機(jī),除了那里每天傳出的廣播呼號(hào)氣沉丹田更有底蘊(yùn)了,小樓還是小樓,沒有太多的變化。
老喬和小喬……
這回說說“觀音橋巷55號(hào)”這棟樓的那對(duì)“門神”父子,老喬和小喬。
老喬不胖也不高,背還有些駝,滿臉見天兒漲得通紅,看上去,氣色極好。老喬每天跑得最長的距離也就是從傳達(dá)室到樓下角落上那個(gè)自來水龍頭跟前。不知怎的,老喬骨子里透著一股子傲氣,只有來來往往的人跟他老喬打招呼,很少見到老喬正眼跟別人主動(dòng)招呼的時(shí)候,即便見著這棟樓最大的頭頭,老喬也不例外。
奇怪的是,好像沒什么人知道老喬究竟什么來路,更少見老喬有過笑臉。想跟老喬坐在一塊兒套套近乎,老喬也不會(huì)支應(yīng)幾句。自顧悶頭喝他杯子里的小酒、夾他碟子里的小菜。先以為是他喝完酒才紅臉,后來發(fā)現(xiàn)喝不喝酒,那張臉都亮著紅燈。
那個(gè)時(shí)候還沒通煤氣,老喬傳達(dá)室有只煤球爐,冬天,老喬多半挨在爐子跟前取暖,很少出門走動(dòng)。老喬一副啞嗓子,喊出來的聲音像是劃玻璃那樣,刺刺拉拉的,也不知是喝酒喝的,還是被煤球爐給熏的。一張紅臉配上一副啞嗓,比什么都管用,賊見了都會(huì)渾身哆嗦,絕不敢貿(mào)然下手。
那個(gè)年頭還不興保安當(dāng)門衛(wèi),更別說設(shè)武警門崗了。像電臺(tái)這樣一個(gè)至關(guān)重要的輿論機(jī)關(guān)重地,擱一個(gè)邋邋遢遢、蓬頭垢面的老喬在大門口,也算觀音橋巷55號(hào)之一絕。
也說說老喬的兒子小喬。小喬整個(gè)遺傳他爹,論邋遢有過之而無不及。個(gè)子還不如老喬高。但小喬腰板挺直,不知哪兒來的自信,小喬倒有點(diǎn)像后來派生出來的那個(gè)職業(yè):保安,只是恐怕很難找到他那個(gè)身高的保安制服。
小喬比老喬豁達(dá)、開朗,跟誰都能混熟,跟誰也都能老三老四、勾肩搭背地?zé)岷酢P叹烤故琼斕胬蠁踢M(jìn)了廣播站,還是自己憑著一把子力氣進(jìn)的門,沒人多在意。小喬上上下下躥騰得厲害,見誰跟誰拉呱。小喬的好處,更樂于助人,樓里人誰遇到什么難事,一聲小喬,小喬就到、就幫,還就能幫成。
小喬平時(shí)閑下來,比他爹更像門衛(wèi),見著不著四六的人在大門口晃悠,小喬立馬上前盤問,直到把人問窘,逼走為止。
也許正因?yàn)檫@樣,小喬到哪個(gè)部門串門,都不覺著他犯嫌。當(dāng)然,碰上女孩子們的“有求”,小喬一準(zhǔn)“必應(yīng)”。
這一老一小倆“門神”,倒也給當(dāng)年的廣播站和后來的電臺(tái)吃了一顆定心丸,也沒惹什么大麻煩。
“活雷鋒”一般的小喬,在人們的嘴里都能有那么點(diǎn)兒不俗的口碑,老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幾杯小酒下肚,臉更紅了。
播音組里的那些人,那事...
這棟樓里,要數(shù)播音組的人奇葩怒放,各是各樣的,“百態(tài)千姿”。
“雨田”和“烏白”形同姐弟,膚色白到一塊去了,音質(zhì),南方口音但已經(jīng)很純正的普通話都很像,為人處世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雨田”傳統(tǒng),干練中帶點(diǎn)兒“各色”,不是那么好接近和相處,矜持有余,親熱不足;“烏白”就好許多。部隊(duì)轉(zhuǎn)業(yè)下來,根正苗紅,一身正氣,一副彌勒佛笑臉,待人如春天般溫暖。
“烏白”的謙恭、好學(xué)、勤勉、認(rèn)真和嚴(yán)謹(jǐn)是他日后能成大器的鋪墊。沒見過他跟誰急眼,再糾結(jié)的事兒,“烏白”處理起來,穩(wěn)穩(wěn)妥妥,順順當(dāng)當(dāng)。
“烏白”為人處事一如其播音風(fēng)格:“字正腔圓,清澈明亮”。從他嘴里播出的早新聞,如一縷陽光,健康向上,不含雜質(zhì),甚至讓人們覺得,這新的一天,太陽也是“簇呱啦新”(鎮(zhèn)江方言音,意:嶄新)的。
“雨田”和“烏白”像老鷹孵小雞一般,呵護(hù)著播音組“兩公一母”三只雞:“烏骨雞”衛(wèi)民、“蘆花雞”張波、“白斬雞”米蘭。
三只雞中最形象的當(dāng)屬“烏骨雞”衛(wèi)民。紫黑色的皮膚,夯實(shí)的身板,走道敦敦作響。手掌往外一伸,手背黝黑,手掌白皙。衛(wèi)民勤勉,低調(diào),話是播音組最少的一位。很少與人爭辯是非清白,待人又很謙卑,擅長播專題新聞。偶爾興奮起來的衛(wèi)民,話匣子一旦開閘,滔滔不絕,口若懸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