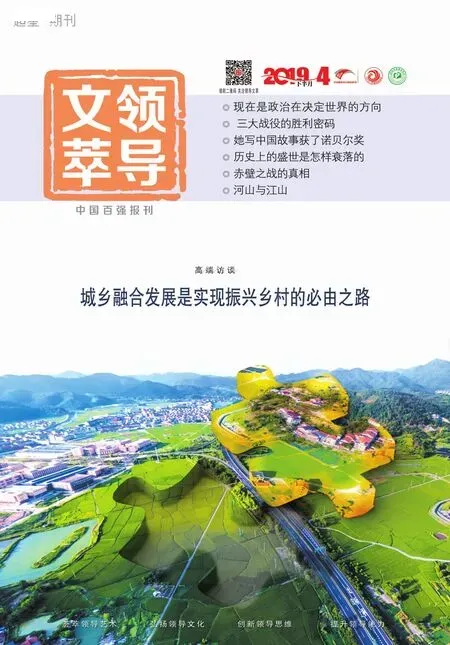應以“謙虛謹慎”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
徐方清
2018年和2019年的國際局勢會有何區別?對于這一問題,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中國新聞周刊:你近期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開始就提到了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發表的長篇演說。不少人將這次演說看成是新的“鐵幕”演說,認為這意味著中美“新冷戰”開始了。但你多次指出,中美進入冷戰的說法是錯誤的。這種風險不存在嗎?
閻學通:任何國際事務都有多種變化的可能,但各種變化的概率有高低之別。我并不能完全排除出現新冷戰的可能性,但我認為出現新冷戰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人認為國際政治只有三種狀態:熱戰、冷戰與和平。然而,這種認識不符合當下世界的客觀事實,也不符合人類歷史。
冷戰并不是熱戰與和平之間的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戰爭烈度和規模都較小,但那不是冷戰。冷戰是特指1945年二戰結束之后到1988年美蘇達成和解這個時期的國際政治形勢,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代理人戰爭的策略在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的狀態,即推行本國的政治體制。我之所以說進入“新冷戰”的可能性很小,是指中美不會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之爭。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在的國際格局中,對于如何定義誰是朋友、誰是對手、誰是敵人,是不是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
閻學通:在不同的時代,國家對敵友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但抽象的標準是相同的,即有無共同利益。在中美兩極化的趨勢下,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大于共同或互補的利益,于是無法將對方定義為朋友。美國已經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了,中國雖然沒有將美國定義為競爭者,但也無法將美國定義為朋友,甚至也無法定義為合作伙伴。
上世紀90年代起,中美將兩國關系定位為“非敵非友”,這不過是假朋友的代稱。我認為,只要中國堅持不以意識形態定義敵友,即使美國單方面以意識形態定義敵友,其他國家以政治意識形態判斷敵友的可能性也不大,多數國家仍會以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判斷敵友。這也是為什么我建議中國對外政策要堅持上世紀90年代中央提出的“對外政策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原則。這個原則為中國改善國際環境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長期堅持,不能改。
另外,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也得堅持“解放思想”的原則,要不斷地改變僵化了的思想觀念。隨著環境、事件、問題以及歷史的變化,任何一種思想觀念都可能不再適于客觀世界。我們要對外交理念進行梳理,分辨哪些是過去適宜但今天不適宜的。對于不適宜的觀念,不能僵化地堅持,而應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調整。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的經驗就是我們不斷地突破自己僵化的觀念,這對國家是有好處的。
比如在中國的身份地位界定上,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將我國的身份界定為什么樣的地位對維護國家利益最有利。定位為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或者其他的什么身份地位。如果我們界定的國際身份地位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有利,那我們就堅持,如果不利,那就應該尋求新的身份定位。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處在中國走向世界強國進程的普通民眾,如何尋找個體的定位,應該用什么樣的一種態度和方式來與急劇變革的世界實現比較好的相處?
閻學通:我以為,中國普通民眾應以“謙虛謹慎”的態度而不是“自以為是”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例如,目前我國還沒有建設成為世界燈塔國家,因此還不具備引領世界的能力。我這里說的謙虛謹慎是指無論自己的實力比他國強還是弱,都應堅持學習他國先進之處,并隨時承認自己的缺點。
中國新聞周刊:從國際局勢的演進看,能否請你簡要總結下2018年的特殊之處,并展望下2019年?
閻學通:2018年最為突出的特點是中美戰略競爭公開化,這將可能是未來多年的趨勢,一兩年內不會發生逆轉。這使得各地區大國采取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給自己留出在中美之間迂回的空間,一方面提升他們自己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中美競爭加劇的同時,世界經濟也可能出現下行態勢,而且這種下行有產生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的危險。不過,中美競爭加劇與世界經濟下行并沒有必然的關聯,很可能兩者只是碰巧發生在同一時期。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