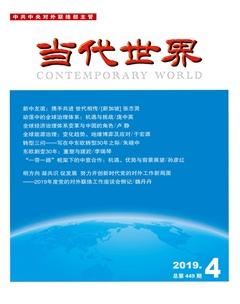在新世界秩序形成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譚哲理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后,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繆爾·亨廷頓等人都在努力尋求世界政治體制的替代方案。然而,這兩位學者研究的出發點是西方現代社會至高無上,在這一前提下無法推理出適合冷戰后21世紀的可行體制。新形勢下,中國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一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謀求共識,避免對抗和沖突”的主張一脈相承。中國在解決經濟、社會和外交等問題中的務實、折衷做法反映出了這一點。與西方現代理念不同的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明顯的包容性特征。
【關鍵詞】新世界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容性
21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南方國家正在改變它們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現。發展中國家在備受爭議的國際體系中的重新定位表明,這些國家既不愿充當主導者,也不愿被主導。相反,發展中國家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有成就的基礎上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意味著要徹底消除貧困,抗擊流行性疾病,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實現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市化和數字化等。發展中國家贊同“世界上沒有一種適合所有國家的‘最佳模式”的觀點。縱觀人類歷史,所謂的“最佳模式”已被證明,在它被輸出到世界上其他地區時,就缺乏適用性了。所謂的“最佳模式”選擇了某些國家強制執行其體制,損害了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語言、知識等體系,從而使它們陷入困境。
當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出現的新情況,恐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其后的冷戰時代更為嚴重。這對南南合作乃至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造成了嚴重影響。這種緊張局面從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缺乏合作以及兩者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造成的。近年來,單邊主義和“貿易戰”愈演愈烈,極右翼勢力抬頭,從而導致穩定與和平形勢趨于惡化。鑒此,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分重要和必要。本文擬從比較的視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含義和實踐進行分析,以體現這一理念的包容性特征。
西方視野下的全球范式轉變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關于冷戰時代的結束和冷戰后的世界秩序一直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自由民主是人類文明和治理的集中體現,正如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所闡述的那樣。第二種說法是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崛起。這兩種說法的核心要義折射出西方列強的衰落以及它們重回世界舞臺中心的企圖。
在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中,西方文明被視為人類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先是將法國革命的成功看作是有效民主的起源,接著將冷戰結束時出現的所有事件解讀為自由民主的勝利。福山聲稱,自由民主是所有國家政府的最終形式。他最為著名的言論是:“沒有任何一個體制能夠替代自由民主。”[1]福山在對冷戰結束進行評論時,將自己的論點總結為一段話:“我們可能目睹的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抑或是一段戰后歷史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本身的終結,換言之,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結。從此,西方自由民主將普遍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2]
為了澄清自己的立場,福山放棄引用美國式民主,而是以歐盟為例,稱歐盟“設法做到了在一個純粹的主權國家的界限之外擁抱民主”。福山指出:“‘歷史的終結從未與具體的美國社會或政治組織模式聯系在一起。繼俄裔法國哲學家亞歷山大·科耶夫啟發了我的最初觀點后,我相信歐盟相比美國更為準確地反映了這個世界在歷史盡頭的模樣。歐盟建立了一個跨國界的法治體系,超越了主權和傳統的強權政治,這一做法相比美國人繼續信仰上帝、國家主權和軍隊更符合‘后歷史世界的特征。”[3]
福山的這一論調強調了他書中的觀點,即歷史始于法國革命(1789—1794年)后產生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包括西方現代國家及其外圍國家。然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冷戰結束并不意味著自由政體的勝利,相反,冷戰的結束僅僅標志著兩極世界的終結和多極世界的產生。在多極世界中,多種政治體制可以實現共存。
亨廷頓后來反駁了福山提出的論點。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之后將出現長期的“文明沖突”。[4]亨廷頓的觀點是,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激烈對抗也將消失,全球性沖突將演變為文化沖突。亨廷頓認為:“人類很多重要分歧和沖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上的分歧和沖突。民族國家仍將是世界事務中最強大的角色,但是全球政治中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國家之間及不同文明群體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5]
21世紀的頭十年發生了席卷世界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在這一背景下,亨廷頓的論點可能被很多人認為是正確的。隨之而來的在文明和宗教沖突框架下而非國與國之間進行的“反恐戰爭”進一步支持了亨廷頓的論點。但是,要想了解亨廷頓論點的背景及可持續性,必須首先解答以下幾個問題:形成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核心依據或主要因素是什么?是關于在原有薄弱基礎上建立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新現代國家的預言,還是從“文明沖突”中產生的全新的國家?弄清這些問題有助于理解亨廷頓是否與福山一樣,將其論點建立在西方現代國家最為優越的前提之上。
在回答上述問題時,需要了解亨廷頓對于自由民主的基礎的分析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廣泛傳播。亨廷頓認為不存在關于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6]他認為,自由民主產生于西方經驗,根源自歐洲基督教歷史。[7]此外,他還指出,沒有特別的理由可以認為自由民主將傳播開來并且植根于擁有不同文化的地區。至于自由民主傳播到日本、韓國等國家,則完全是美國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作用的結果。一旦這些實力相對其他文明出現衰落,民主思想的號召力也將隨之消失。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預言,世界將回到中世紀時期,不同文明將如同19世紀的各帝國那樣相互結盟。人們想知道,為什么在亨廷頓的想象中,西方現代社會以外的文明無法形成連貫的團結同盟并且最終融入到世界體系中去?人們還想知道,為什么亨廷頓始終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具備創造一個免于沖突的新世界秩序。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非常簡單,亨廷頓的想象力集中于這樣一種觀念之上,即連貫的組織力量只存在于西方現代社會建構中。亨廷頓對南南合作及其他反對西方世界體系組織的斗爭均視而不見,更不用說存在著另外一種文明或在北方國家以外的地方存在著有能力組織一個連貫的世界體系的人們的想法了。
跨文化交流與殖民主義
在能夠確保外來文化價值觀有益于當地社會的情況下,促進文化多樣性始終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工作。引進的價值觀往往會對本國的統治者和基層民眾產生影響,并最終成為造福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然而,在遭受殖民統治或其他形式的強加規則的情況下,文化多樣性往往會帶有強加的性質。從強加的文化多樣性中受益的人往往來自殖民宗主國,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受益的是宗主國本身。盡管如此,隨著時間的變遷,這種具有壓迫性質的文化多樣性往往也會演變為主流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近期的全球化浪潮無外乎均建立在以上兩類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外來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占據了舞臺中央,并取代當地原有文化的首要地位。“新文化”之所以能夠逐漸取代“舊文化”,是因為人們認為“新文化”能夠吸引各種資源,包括象征性資源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等諸類資源。只有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能發揮作用的引進價值觀才有較高的價值。根據上述分析,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崛起并進入國際社會的中心舞臺,其結果可能是這些國家的文化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廣泛傳播,并最終取代當地原有的生活方式。這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目的嗎?很顯然,中國的崛起及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將帶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但是,對于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不斷提升會導致中國文化取代當地文化,有幾個論據可以駁斥這一說法。
阻礙中國文化取代當地文化的第一個因素是西方殖民計劃失敗和血腥歷史所帶來的啟示。歷史上,殖民主義曾導致全球出現巨大的貧富差距,但殖民計劃很快就以失敗告終。其短命性質將說服中國不會接受任何殖民主義思想作為維持它在國際社會中享有強大地位的手段。歷史上有充分證據表明,中國是一個傾向于制訂長遠戰略的國家。自鄭和(1371—1433年)下西洋以來,中國在歷史上就從未有過征服和占領其疆土之外別國土地的興趣和情況。此外,清朝覆亡后,中國與外國侵略者進行了長期斗爭,這一歷史使中國不會向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方向發展。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的許多項目都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出現西方殖民計劃所帶來的問題和動蕩。近年來,中國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需要一個能讓經濟繁榮發展的和平環境。
新時期,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的成功和吸引力充分說明了中國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都缺乏興趣。此外,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長期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殖民計劃的實質和根本目的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謀求中庸或共識的理念與殖民計劃的對抗性質南轅北轍、格格不入。
跨文明對話或文明間對話
用中國學者杜維明的話來說,中國的崛起引入了跨文明對話的概念。這是一種“人文主義的視野”,“在文化多樣性背景下樹立了普世倫理的理想……達到了最高層次的自我意識……描述了人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單邊主義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中都是錯誤的構想,它無法理解經濟全球化,抹殺文化多樣性。缺乏正義的自由,缺乏同情心的理性,缺乏修養的法律義務,缺乏責任的權利,缺乏社會團結的個人尊嚴,這些都不足以建立一個包含豐富和平文化內涵的持久的世界秩序。只有通過“文明間對話”才能形成對普世倫理的全面理解,這種理解必須建立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主義和強勢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8]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對全球化的定義和進展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杰弗里·塞胡梅(Jeffery Sehume)這樣定義參與全球化的能力:“全球化強調21世紀的主要特點是‘知識社會,‘知識就是力量。”[9]在描述中國在促進全球化當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時,應該補充一點:中國更看重的是所有國家均能從全球化當中受益,而不是利用全球化去強行干涉別國事務。2018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就很好地佐證了這一點。在這次峰會上,中國承諾將向非洲國家提供600億美元用于實施“八大行動”,這是《中非合作論壇—北京行動計劃(2019—2021年)》的重要組成部分。仔細審視“八大行動”就會發現,中國制定了一個全面的對非計劃。中國并非要把自己棄之無用的東西甩給非洲,而是要向非洲轉移技術,幫助非洲建設新的產業,防止非洲遭受污染等工業發展帶來的弊病。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開篇就提出當今世界困擾多國領導人的許多問題都可以總結為“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習近平主席繪制了人類在整個20世紀所走過的軌跡,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他演講的中心思想是呼吁全人類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回首最近100多年的歷史,人類經歷了血腥的熱戰、冰冷的冷戰,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巨大的進步。20世紀上半葉,人類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劫難,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戰爭、締造和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普遍覺醒,他們最強勁的呼聲就是擺脫枷鎖、爭取獨立。冷戰結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訴求就是擴大合作、共同發展。這100多年全人類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與發展。然而,這項任務至今遠遠沒有完成。我們要順應人民呼聲,接過歷史接力棒,繼續在和平與發展的馬拉松跑道上奮勇向前。”緊接著,習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國領導人響應人民的號召,在和平與發展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2017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南南人權論壇再次呼吁國際社會走和平與發展的道路。論壇最終達成《北京宣言》,這反映了全球南方國家以堅定決心維護和平與發展的能力。習近平主席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證明了中國對全球化的理解和推進充滿包容性,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這一思想指導著人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務。作為一種生活之道,“中庸”思想主張,個人和社會應優先謀求共識,避免對抗。
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顯示出其對中庸之道這一思想根基的依賴。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強調自我修養、寬大仁慈、誠意篤實。[10]在闡釋中庸之道時,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曾指出,其目標是通過維持頭腦的持續均衡狀態以實現平衡與和諧。奉行中庸之道的人是在履行職責,絕無放棄之理。一個優秀的人應該時時謹慎、溫柔教導他人,不輕視不如自己的人。[11]
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式進入全球舞臺,原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那些過去曾經犯下統治別國、迫害他人、排斥異己等罪行的人卻有可能對這一倡議心懷恐懼。筆者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應該被理解為包容性的“新世界秩序”的出現。
結 ?語
西方國家在過去的500年里統治著世界,并且企圖將其價值觀拓展到西方世界以外的知識和文化體系中。個人主義至上的西方國家自行其是,憑借各種手段在全世界行使權力,引發了一波又一波野蠻的單邊主義。現如今,無論是世界貿易組織還是聯合國,在猖獗的單邊主義面前都失去了尊嚴。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該源自不對抗的原則。像中國這樣崛起的國家將建立共識作為其核心價值,有助于人類進步。之所以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代表著“新世界秩序”的成功和可持續性,是因為它消除了一個國家從屬于另一個國家的概念。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宣布并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南南合作機制內各國之間的合作與共同發展奠定了基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推進、實施和可持續發展最為核心和突出的前提條件是,要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價值觀體系尋求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簡言之,不能強行要求任何一個國家接受別國的發展和生活方式。中國強調,有朝一日自己強大了,也不會去侵略別國。這是對“新世界秩序”作出的承諾,前所未有。中國不作西方現代社會的替代品,而是要與世界人民一道為人類謀進步。通過以上分析,人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所倡導的雙贏合作、相互理解、共同發展、和平共處等概念的內涵,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
(作者系南非姆貝基領導力研究所研究員,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副教授)
[1]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027184.
[2] 同[1]。
[3] Fukuyama Francis,“The History at the End of Histo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7/apr/03/thehistoryattheendofhist .
[4] Huntington.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sues/1993/72/3.
[5] 同[4]。
[6] Fukuyama Francis, “Huntingtons Legacy”,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8/27/huntingtons-legacy/.
[7] 同[6]。
[8] Le Pere. G, ed, China through the Third Eye: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s, South Africa: Institute for Global Dialogue Publication, 2004, pp.1-2.
[9] Sehume Jeffrey, Multicivilisational Dialogue in Africa-China Relations in Africa-Chin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New Jersey: World Africa Press, 2018, p. 300.
[10] Wong Ovid, Distilling Chinese Education into 8 Concept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p. 39.
[11] ?Legge Jame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ttp://www.sacred-texts.com/cfu/conf3.htm.
(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