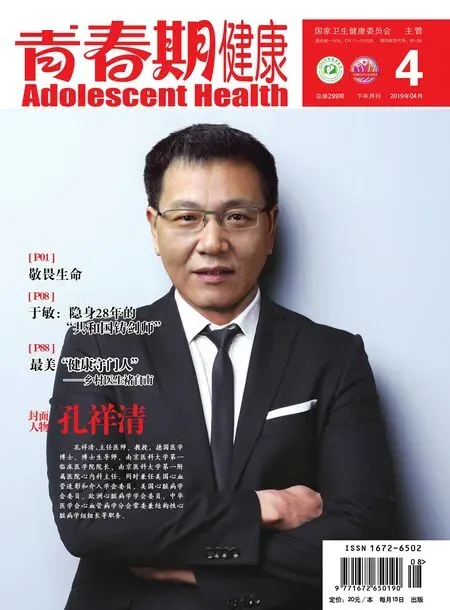于敏:隱身28年的“共和國鑄劍師”
■ 文 王玉琴

2019年1月16日,“兩彈一星”元勛于敏逝世的消息,在網上掀起了“沉痛送別,致敬民族脊梁”的浪潮。被稱作“中國氫彈之父”的于敏,用畢生精力締造了驚天事業,卻過著“沉默的人生”——他隱姓埋名28年,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其間連妻子都不知道其從事的秘密工作,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被解禁。這位讓中國國防實力大幅提升的“土專家一號”,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呢?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寧河縣。他的童年時光是在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的戰亂中度過的。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里“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里,于敏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
于敏意識到自己內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于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碩士畢業后,他被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于敏的研究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站在了國際前沿。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隱姓埋名28年
1960年底,在錢三強的組織下,以于敏等為主的一群年輕科學工作者,在為研發原子彈獻計獻策的同時,又悄悄地開始了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這次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對于敏來說,意味著巨大的犧牲。于敏生性喜歡做基礎研究,當時已經很有成績,而核武器研究不僅任務重,集體性強,而且意味著他必須放棄光明的學術前途,隱姓埋名,長年奔波。
盡管如此,于敏還是接受了任務,從此,于敏的名字“隱形”長達28年。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于敏與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他的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多年后才恍然,“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轟動。1965年1月,毛澤東主席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周恩來總理下達命令:“要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首位。”這年,于敏調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與我國核武器研究主戰場匯合。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部主任,帶領各研究室人員分別攻關奪隘,力圖突破氫彈構造原理。同年9月,作為理論部業務領導,于敏帶隊去上海出差,利用上海華東計算所每秒5萬次的J501計算機,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3個月時間里,于敏帶領科研隊伍群策群力,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這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
回憶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參加過會戰的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研究員蔡少輝說:“第一批模型的計算結果,熱核材料沒有充分燃燒,我們認為是正常的。但老于說,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睡鐵床,鋪稻草,守著吐出大卷大卷紙帶的老式計算機,在那100多天里,于敏的大腦一直像計算機一樣高速運轉,終于帶領科技人員算出新的模型,牽住了氫彈的“牛鼻子”。

中國第一顆氫彈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原子彈和氫彈的研發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為我國曾經飽受“核欺壓”。20世紀50年代,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抗美援朝時,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就曾建議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它是真的在進行核訛詐、核威懾,不是在報紙上說說而已。”于敏說。
模型計算成功后,于敏當即給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秒懂:“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這樣的隱語,是為了保密。在為打造國之重器而隱姓埋名的歲月里,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說的痛苦。
女兒于元一直清晰地記得,幼時父親工作繁忙,從未輔導過自己的功課。甚至一有同事來訪,自己和弟弟就會被趕出屋去。“有一次父親跟一個單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門邊偷聽,聽到他們說起‘肉’,還挺饞,卻被媽媽噌地一下拉出來。后來我才知道,他們談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

1967年6月17日下午,新華社在《新聞公報》上發表了“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的喜報
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羅布泊,隨著指揮員一聲“起爆”的指令,一架飛機的機艙隨即打開,氫彈攜著降落傘從空中急速落下。彈體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時,只聽一聲巨響,碧藍的天空隨即翻騰起熊熊烈火,傳來滾滾的雷鳴聲……紅色煙塵向空中急劇翻卷,愈來愈大,火球也愈來愈紅。火球上方漸漸形成了草帽狀云霧,與地面卷起的塵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強烈的光輻射,將距爆心投影點400米處的鋼板鑄件燒化;700米處的輕型坦克被完全破壞;沖擊波把距爆心投影點近3千米、重約54噸的火車吹出18米,近4千米處的半地下倉庫被揭去半截,14千米處的磚房被吹散……當日,新華社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中國的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用了6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而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其爆炸威力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
大音希聲,數十年秘密奉獻的隱士生涯,讓于敏面對外人時,養成了謹慎少言的習慣,他不喜歡接受采訪,也不認可被記者冠予的“中國氫彈之父”頭銜,總說那些成績都是團隊的貢獻,是集體的榮譽。
運籌帷幄
20世紀80年代,在原子彈、氫彈等技術相繼突破后,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等曾經共同奮戰在核武器研制一線的骨干相繼離開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昔日群星閃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蓮三人。
于敏也想過離開,但“估計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但性能還需提高,必須發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來,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當地寒風刺骨,沙塵漫天,積勞成疾的他突然渾身發抖,嘴唇青紫,繼而頭上直冒冷汗。同事們一看嚇壞了,“老于,先去看病吧!”“這個節骨眼上我怎能離開,抓緊工作吧!”因核試驗已經進入關鍵時期,身體十分虛弱的于敏沒有離開試驗場半步,而是在這黃沙大漠中高聲吟誦著“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悲壯詩句,圓滿完成了任務。
1986年,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認為美國核戰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極限,做再多核試驗,其性能也不會有大的提高。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全面禁止核試驗。倘若那時中國該做的熱核試驗還沒做,該掌握的數據還未得到,核武器事業可能功虧一簣。
聽了于敏的憂慮,鄧稼先也有同感。于是,由于敏起草,鄧稼先修改,胡思得執筆,向中央遞交了報告,希望加快熱核試驗進程。后面發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于敏等人的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的熱核試驗時間。
針對禁核試,于敏提出了以精密實驗室實驗等幾個方面支撐禁核試后武器研究的設想,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中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四大支柱。
于敏的謀略,“拆”掉了美國的陰謀。因此,于敏又被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戰略家,從某種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諸葛亮那樣,運籌帷幄,料事如神。
兵者,國之重器,不可輕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應藏于九地之下,應動于九天之上。
名藏九地之下,聲動九天之上。這正是像于敏那樣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一大批核武研究者們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