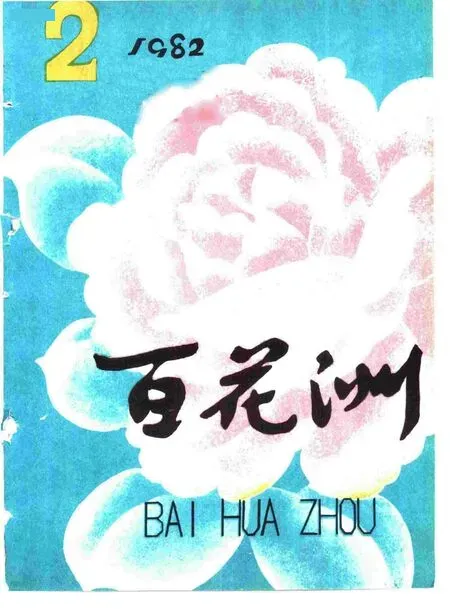摩圍(組詩)
張遠倫
思想者馬尾松
一只灰雀是一個成熟的技師
她的巢選址精準,從不建在即將枯萎的馬尾松上
有一些死亡的氣息只有她能嗅出
一條老藤就在她的新巢邊,似有
大糾葛未解。它連名字都沒有
為了配合灰雀的飛翔,它會盡量減少蕩漾
一個人出現在樹下沒什么意思
在這里,我的世俗生活總能找到替身
我就是一個臨摹者。抑或失語者
向枯藤問一些愛情的問題,向灰雀
問一些家庭的問題。如果來得及詢問自己的未來
請別錯過樹洞,它收養過冰雪也盛裝過大風
只有它像我的老境。有小小的不可測
和時光的傷害。唯有這種傷口
能被覆巢的雛鳥,暫借數日,抑或久久利用
“搖曳”這個詞
不記得是哪一天,我突然討厭起“搖曳”這個詞
我的山坡,不美了
我懷疑山坡上的芭茅草,學不來蘆葦的樣子
那輕度的,有彈性的弧線
終于,今天,我突然一下子
又迷戀上了這個詞
芭茅草,站在山坡上,不斷點頭,又不斷搖頭
黃昏中的搖曳,這個詞,出現在殘絮上
出現在群墳旁,突然,具有了動詞的驚惶
而又,具有了形容詞的,一派安詳
摩 圍
啞巴,為了解釋摩圍
我推舉自己的天靈蓋。我已經
找不到身體上,更接近高天的部分
而你覺得我常常垂首匍匐
取出頭骨,就只能是:又在懺悔
啞巴,為了讀出這個詞語
我的嘴唇變化得很緩慢,聽
摩——圍——而你認為這是我
天天都向你讀出的:姆
一個字有了綿長的尾音,和呼喚
就會變成兩個字,甚至深遠
啞巴,為了向你描繪摩圍
我指向自己的前額,說:這是懸崖
我指向自己的胸膛,說:這是草原
啞巴呀,可你認為我指向了靈魂和心
連連擺手,讓我不要悲傷
啞巴,你是對的
悲傷那么遼闊,愛意難以象形
一座山與你,與我
一旦產生關聯,就會深藏迷霧
就像我倆在人間
唯有縹緲,可以深深會意
注:摩圍,仡佬族語言,意為接近天堂的地方。
一生,只干凈一次
我的羊一生骯臟。我的牛一生骯臟
我一生骯臟
我的羊和牛一生只干凈一次
就是被洗凈,宰殺
皮晾曬在化雪的陽光中
我一生只對你,干凈一次
所謂癡迷,就是凈身,入棺,向你
獻上白骨。我骨子里干干凈凈
可以吸空。這另一個世界的我呀
干凈地,率領著我那干凈的
羊群,牛群,沒有敵意,沒有怨懟
青草連天,交媾,也是干凈的
藤的陰影中回憶明亮
野生獼猴桃藤,有一個陰影
曾經布滿麋鹿的腳印
松鼠的長尾巴,毛毛蟲的唇痕
一場大雪讓什么都消失了
可你的陰影
還在那里,布滿了冰掛的垂體
霧凇的晶體
因此你的陰影里布滿慈悲
如此明亮,像在巨大的安靜中
回憶那樣,明亮
你的陰影里
冬至覆蓋過立秋,大雪掩埋過小雪
我收藏過你
花的俘虜,雪的被告
野桂花的葉子窄一點,尖一點
香氣短一點,收一點
它的孤絕,因為離群索居
便不是花的孤絕
花下一兩人,有一兩個跪姿
因為迷戀憂郁
才能識得香氣的幽深
身后是懸崖,身前是追捕
花朵在野,接受它的撫摸
便是接受自然的刑具
很輕,看不見
啞巴呀,香氣不斷
我想長久地跪臥下去
我仿佛看見雪原就在眼前
如一場遼闊的庭審
我們此生無望,無辯護
我做花的俘虜,你做雪的被告
在野者壇花木犀
暮色變成了霧氣
霧氣變成了露水
露水爬上睫毛,壇花木犀
因此獲得深深的孤寂
她的孤寂,是奇數
方圓十里,再無第二株
你也配有這樣的孤寂,不過
你要先像尊重愛情那樣
尊重海拔。你還要像尊重貧瘠那樣
尊重頁巖,和頁巖里的石縫
壇花木犀因此獲得
深深的死亡的感覺,就如
花簇從葉腋里蜷縮進去
黯淡下去,而后
她滿面化霜,你狀如永訣
注:壇花木犀,俗稱野桂花。
母 骨
圓盤鋸、鐵片、飛來橫石
這些取走我親人骨頭的物體,不見了
右腓骨、手指骨和頭骨,這些缺口
構成了一家人的重量
老人還在醫院里,剛剛破碎的
是一片我們的母骨
因為輕賤
被隨手丟棄在垃圾桶中
隔壁剛剛做完人工植骨手術的人
花數萬元買了幾克骨粉
這讓我相信:地球引力就是命運
巧合不是。當然,神也不是
她昏迷的時候,我在大哭,三百里外
無能為力。無能為力才是最后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