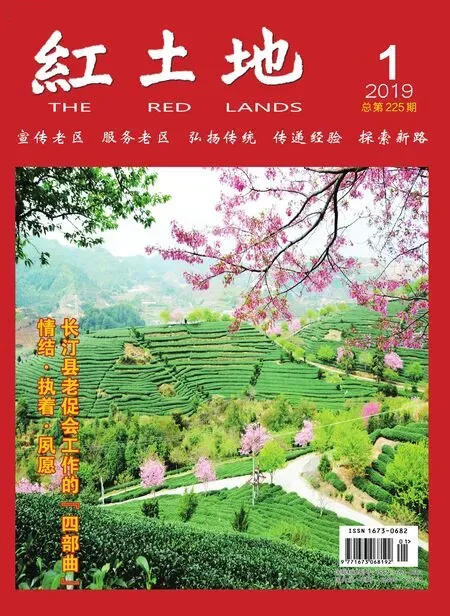又見石榴紅
◎王英
汀州西門羅漢嶺,是36歲的他告別人世的地方。從中山公園的涼亭前安然自飲“就義飯”,再恬淡而肅穆地赴刑場。他盤腿坐于一處青草叢,微微一笑,留給了世人最后一句話:“此地甚好!”
從此,我的家鄉,環繞的蒼松間聳立著他的紀念碑。碑前,漢白玉的半身雕像置于郁郁蔥蔥的木棉樹叢中。他身著西裝,消瘦的臉上架一副近視眼鏡。身后是女兒瞿獨伊親手種植的一棵柏樹,日夜陪伴父親,為他遮風擋雨。
走近瞿秋白,總抹不去淡淡的憂傷。魯迅先生送他一句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令多少后人羨慕追尋。他短暫的一生,無論詩詞、繪畫、書法、篆刻、吹簫、昆曲、翻譯,任哪一個領域,其非凡的藝術造詣都令人驚嘆。這位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卻如同火花,擦亮了星際,瞬間墜入無垠。
他最后的囚禁地,是我曾經每日必經的上學之路——宋代汀州試院,今名長汀博物館。他或許聽過,清代學者紀曉嵐也曾下榻于此,巡考秀才的鄉試。就是這間小得不能再小的囚室,他待了四十個日夜。臨窗的庭院,常年盛開著石榴花。小小的書桌前,他每日看書寫作。“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道盡了當年的落寞。“中國的豆腐很好吃,世界第一。”這,該是他對世間難舍的眷戀吧?
才子成為了領袖,在生命的終結點,又還原為才子。“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善良的人總是相信來年春花再放、馨香依舊。如今,長汀一中的“秋白亭”前,在這里讀書、嬉戲的孩子們,總有一天會想起,當年那個氣質優雅的文人領袖,曾靜靜地走過這個八角涼亭,輕哼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生命的終點。
“人愛自己的歷史,甚于鳥愛自己的翅膀。”這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時代終究要歸還他的公正。10年前,崔永元寫下了《1935·犧牲》:“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輩,總是選擇清白、鎮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卻永遠活著。”5年前,廈門百名知青來汀,迷蒙細雨中,舉行了緬懷他的詩詞朗誦會。而他85歲的女兒,更有她獨特的方式寄托思念。為感恩老區人民對他的熱愛,自小在蘇聯長大的她,哼著俄羅斯民歌《紅莓花兒開》,在長汀火車站臺前翩翩起舞。
80年過去了,在汀州云驤閣,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院。巧合的是,古樸的庭院,也種著一株郁郁蔥蔥的石榴樹。枯瘦的樹干,勃勃生機的綠葉,沉甸甸的石榴敞開心扉,清香四溢,熱烈而安靜地綻放著。如果說,汀州試院的石榴,見證了他寬闊的胸襟、真實的靈魂。那么,今日火紅的石榴,是否昭示著他思想的沉淀、堅守,以及后繼有人?從此,紛沓而至的人們,到汀州追尋的,不再是他生命的歸宿,而是精神的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