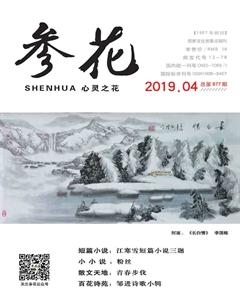自畫像與他畫像
邰貫虹
摘要: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多數人通過對他作品的閱讀以及對他事跡的了解,腦海里多半會浮現出一個愛憎分明、一絲不茍、憂國憂民、以筆為刃的中年魯迅形象。本文擬通過對魯迅《藤野先生》中那個留學日本的青年魯迅形象與太宰治《惜別》中的青年魯迅形象的對比,真實再現青年魯迅形象。
關鍵詞:魯迅 青年 太宰治 《藤野先生》 《惜別》 比較研究
一、魯迅《藤野先生》中的青年魯迅形象
增田涉和佐藤春夫翻譯《魯迅選集》前,曾征求魯迅意見,魯迅說,其他篇目任憑挑選,“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這足以證明多年以來,魯迅對藤野先生懷有的深深感佩之心。
在《藤野先生》中,魯迅提到在仙臺時受到過日本具有狹隘民族觀念的學生的排斥,也受到過“幻燈片事件”的刺激,他獨自一人遠離家鄉前往異國求學,唯獨藤野先生對他的筆記認真仔細指正批改,對他的學業關心且臨別贈送照片贈言,給年少的他帶來了一絲溫暖。
由魯迅在《藤野先生》開頭描寫的“清國留學生”來看,其明顯對這一類人持有貶斥的態度,以辮子為榮,學習跳舞,被國外的生活迷惑了雙眼,這是魯迅所不屑做的,可見青年時期的魯迅是一個淳樸且目標堅定的人。他從國內來到國外,沒有被國外較國內更開放的風氣所浸染,也沒有被新奇事物吸引走注意力,平時想得最多的還是學習的事,“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體現了魯迅青年時期就是個認真嚴謹、心志堅定、愛讀書的人,留學就努力學習,不學那些“清國留學生”的不務正業、玩物喪志。
留學時的魯迅內心是存在自卑的,就如有同樣經歷的郁達夫,他對當時國家的弱小而產生的悲哀、苦悶、自卑的心理,是必定存在的。魯迅先生曾在《藤野先生》中寫道,“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這里固然能看出魯迅的憤怒與苦悶,可往深里品味,能隱隱感到留學時的魯迅——這個淳樸又敏感的青年,當時情況下,其內心是對自己“清國留學生”身份感到自卑的。
而之后的“幻燈片事件”,更是給魯迅年輕的心上增添了一道傷,數十年都不能愈合,汩汩流血,這是青年魯迅的悲哀,是所有留學生的悲哀,更是那個年代背景下,地大物博、人口繁多卻窮困落后的祖國的悲哀。“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觀看的片子里,被槍斃的是中國人,圍觀時拍掌歡呼的也是中國人,這深深刺痛了魯迅,他意識到僅僅保持身體的強壯康健,對國人來說毫無用處,精神上若不醒悟便一直如同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一個為祖國憂心,為民眾感到悲憤、屈辱,決意為祖國做出些貢獻尋求出路的青年魯迅形象隨著作者沉痛的敘述,便勾勒出雛形。
從后來藤野先生寫的《謹憶周樹人君》也可依稀想象出青年魯迅的形貌,“周君身材不高,臉圓圓的,看上去人很聰明”“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的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的聽、說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可是周君并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只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這些都可以看出青年魯迅對待學習的用心程度,他是懷著一顆赤誠報國之心去認真學習醫學以造福民眾的,魯迅的恩師對魯迅的形容,讓青年魯迅的形象更加豐滿、立體。
二、太宰治《惜別》對青年魯迅形象的想象性充實
《惜別》這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本政治小說。但是,它仍然具有研究價值,太宰治別具匠心地選擇將青年魯迅寫入小說,而并不選擇中年魯迅,雖對魯迅的認識遠遠比不過竹內好與池田,可他拉近了魯迅這一形象與讀者的距離,在閱讀了魯迅的相關作品后,他將對魯迅的一些細致入微的推測與判斷寫入《惜別》,體現了他近乎敏銳的觀察力。
竹內好是與太宰治同時代的學者,他在《惜別》出版第二年對此表達了不同的觀點,認為太宰治“對魯迅所受的屈辱共鳴不足”。然而,藤井理三卻支持《惜別》中對青年魯迅形象的表達,認為是“在充分尊重事實關系的基礎上,發揮太宰治式的豐富想象力,描繪出了淳樸的中國留學生形象,并成為一種優秀的‘初期魯迅論”。
不同學者的看法各異,許多學者也對《惜別》創作的背景頗為詬病,認為其塑造的魯迅形象帶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是“太宰式魯迅”。但筆者認為,《惜別》固然有種今人寫李白,寫孔子,寫阮籍時的“隔靴搔癢”之感,也帶入了自己的感情,給所塑造的魯迅形象增添了自己最熟悉的“大庭葉藏”式人物的性格特點,可是太宰治以田中卓的口吻與眼光描寫并觀察魯迅,以口音問題和孤獨為切入點,這是他匠心的體現,很有研究價值。
譬如《惜別》中有一個場景——敘述者“我”在仙臺名勝松島因為偶然的機會聽到魯迅唱《云之歌》,便懷有這樣的感想:“說是跑調兒吧,或者是什么吧,實在是糟糕。” 這兒寫了一個唱歌跑調的魯迅,不得不佩服太宰治的細致與敏銳,魯迅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對美術懷有濃厚的興趣。辛亥革命后,他也曾經在新生的中華民國教育部擔任美術教育方面的工作,同時還設計了北京大學的校徽,這都是基于他熱愛美術的精神。他還翻譯了《近代美術史溯論》以及日本少女雜志插畫家落谷虹兒的精裝本詩畫集。除此之外,魯迅先生還非常喜歡好萊塢電影。奇怪的是,魯迅先生對視覺藝術表現擁有非常濃厚的興趣,但幾乎沒有表現出對音樂藝術的喜歡。因此,太宰治的“魯迅五音不全說”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敏銳的觀察力,讓青年魯迅形象在讀者的腦海中更加飽滿、立體。
創作《惜別》時的太宰可能不會有接觸留學生魯迅照片的機會,他僅憑卓越的想象力就寫出了“像商家少爺一樣俊雅”的棉和服形象的魯迅,這與現在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張魯迅在東京寄宿旅館里穿著裙裝和服,端坐在榻榻米上的照片竟不謀而合。
通讀《惜別》全文,太宰治塑造了一個“五音不全”“像闊家少爺一樣俊雅的”,淳樸而親切的青年魯迅形象。與竹內制造的、隨后長期支配日本讀者階層的“苦惱著的魯迅”形象相比較而言,太宰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描繪出的親切地微笑的魯迅形象,無疑給讀者展現了另一個青年魯迅,拉近了讀者與文豪魯迅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