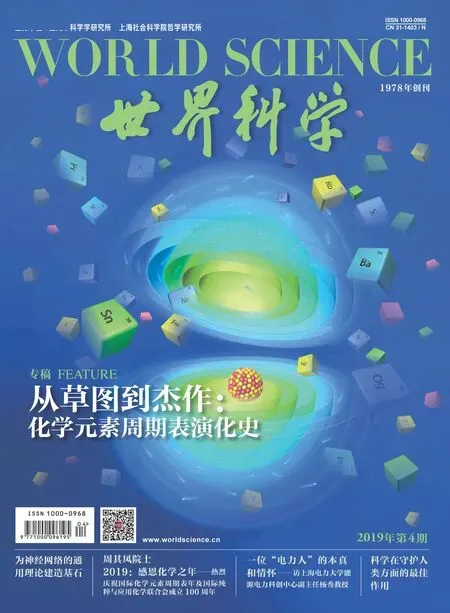極端化學:元素周期表邊緣的實驗
編譯 博衍
隨著新元素探索的腳步放緩,科學家們將工作重點放在加深對已知超重元素的理解上。

如果你想創造世界上下一個未被發現的元素——元素周期表中的第119號元素,下面的方法也許能夠助你一臂之力。首先,取出幾毫克锫,這是一種稀有放射性金屬,只能在專用核反應堆中制造出來;然后用鈦離子束轟擊樣品,其速度大概需達到光速的1/10。堅持一年左右,要有耐心,而且要非常有耐心。鈦離子每轟擊锫靶1018次——大約一年的射束時間——可能會產生1個第119號元素的原子。
在這種罕見的情況下,鈦和锫的原子核會發生碰撞并合為一體,碰撞的速度超過了它們的電斥力,從而創造出地球上甚至宇宙中從未見過的物質。但新的原子會在大約1/10毫秒內分解。在衰變過程中,它會爆發α粒子和γ射線,落在放置于锫靶周圍的硅探測器上,從而證明轉瞬即逝的第119號元素的確存在過。
研究人員已經開展過該實驗。2012年,德國的化學家花了數月時間對其進行研究,但最終一無所獲。日本科學家曾嘗試過其他的光束和標靶組合;他們還曾與和俄羅斯的一個研究團隊合作,共同尋找第120號元素,但運氣欠佳。
擴展元素周期表的努力還未結束,但正在慢慢停止。自從俄國化學家門捷列夫在150年前首次發表元素周期表以來,研究人員一直在以平均每2~3年增加一種元素的速度往周期表中添加元素。在發現了所有自然存在的穩定元素后,研究人員開始創造元素,如今已經發現了第118號元素。盡管他們仍然希望找到更多元素,但同時也一致認為,發現第120號之后的元素的前景不容樂觀。加州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研究重元素化學的杰克林·蓋茨(Jacklyn Gates)表示:“在新元素合成方面,我們已經到了回報遞減的階段,至少以我們目前的技術水平來看是這樣。”
因此,在元素周期表邊緣進行的研究正在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科學家們不是去尋找新的元素,而是重新加深對已經發現的超重元素的理解。粗略地說,超重元素就是那些原子序數超過100的元素。通過研究這些元素的化學性質,可以看出質量最大的元素是否遵循元素周期表的組織規則。周期表則根據化學反應的周期性重復模式,將具有相似性質的元素歸為同一家族。盡管最重的元素在轉瞬之間發生衰變,但研究人員仍然希望他們可能到達傳說中的“穩定島”:一個假想的元素區,其中的一些超重元素同位素(原子核中質子數相同,但中子數不同的原子)可能存在幾分鐘、幾天甚至更長時間。
創造新元素在概念上非常簡單,但在技術上既困難又緩慢。研究在不到一秒內衰變的原子的化學和核物理性質,將計算和實驗工作都推到了極限。到目前為止,該領域取得的成果已經對這些極端元素的化學周期性提出了疑問。85歲的俄羅斯核物理學家、歷史上第二位健在時便擁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元素()的科學家尤里·奧加涅相(Yuri Oganessian)說:“發現超重元素有時就像打開一個潘多拉盒子,從盒子里扔出來的問題比發現更多的元素要復雜得多。”
元素發現時間
自從門捷列夫在1869年發表周期表以來,研究人員發現或創造新元素的平均速度是每2~3年一個。

稀有成果
對超重元素的研究始于20世紀40年代的戰時科學。第一批非自然元素是在原子彈試驗的放射性塵埃碎片中發現的,還有一些是在粒子加速器中制造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研究要么在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進行,要么在奧加涅相所在的位于俄羅斯杜布納的聯合核研究所(JINR)進行,而超重元素的研究工作是在冷戰競爭的氛圍中進行的。20世紀80年代,德國加入了競賽,位于達姆施塔特的一個研究所(現亥姆霍茲重離子研究中心,GSI)制造了第107號至第112號的元素。
GSI超重元素部門負責人克里斯托弗·杜爾曼(Christoph Düllmann)認為,早期的競爭優勢已經減弱,如今,研究人員經常合作開展一些實驗。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西奈山加速器科學中心的一個日本團隊被認為制造出了第113號元素。后期元素(至第118號元素)的創造很多時候共同歸功于來自德國、美國和俄羅斯的團隊。
學生譯文1: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this project cost will exceed 30%of the budget.
在GSI從事元素合成工作40年的馬蒂亞斯·沙德爾(Matthias Sch?dell)認為,現代尋找超重元素的工作類似于小規模的粒子物理實驗,需要具有不同科學專業知識的團隊從大量碰撞數據中篩選出非常罕見的事件。他說:“在控制室里坐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周,僅僅是為了尋找探測器發出的期待已久的信號。這項工作非常無聊,令人精疲力盡。然而,首次觀察到期待中的事件會令人激動不已,身心愉悅,同時給人以巨大安慰。”

2015年,森田浩介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他領導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團隊發現了第113號元素
奧加涅相表示:“人工元素的合成從來都是一項困難而艱苦的工作。將元素周期表擴展到118號以后的元素會消耗大量時間,而且回報也會不斷遞減。在發現第117號元素的過程中,每周可獲得1個原子;第118號元素則每個月只能獲取1個原子。沒有理由相信第119號和第120號這兩種未知元素的產量會增加。”瑞典隆德大學的核物理學家德克·魯道夫(Dirk Rudolph)認為,如果研究人員能夠增加原子束的強度或標靶的厚度,這將會有所幫助,但是這兩項工作“在技術上都極具挑戰性”。
杜爾曼說,GSI目前已經停止了尋找新元素的工作,因為這家機構正在安裝一臺反質子和離子研究設備的加速器,用于研究天體物理現象,超重元素研究工作因此被擱置下來。
奧加涅相說,與此同時,JINR的研究人員也在2014年底“幾乎停止了”對元素的探索。在過去的5年中,他們集中精力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奧加涅相稱之為超重元素工廠,生產已知元素的數量可以是原來的數十倍或數百倍。奧加涅相表示,該實驗室可以同時開展5項實驗,還計劃從2019年4月開始進行兩項為期50天的演示,生產第114號和第115號元素。
幾年前,伯克利研究小組就放棄了尋找元素。蓋茨說:“人們經常討論我們是否應該嘗試制造一種新元素,但是我認為,通過對目前已知元素進行更詳細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利用現有的束流時間。”
理化學研究所仍在尋找元素,但同時也在鞏固我們對現有元素的了解。該中心超重元素生產團隊的負責人寬宏光表示,他的團隊將研究第104號、第105號和第106號元素的化學性質。
周期性的終結?
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探索已知元素的化學性質和核物理性質與制造新元素一樣有價值。一個關鍵問題是,超重元素在多大程度上維持了構成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基礎的化學性質的周期性。元素的化學性質取決于其最外層電子的反應性。在原子中,電子占據著不同的軌道。這些軌道環繞著原子核,而能量最高的軌道在形成化學鍵和離子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同一列的元素(同族物)具有相似的化學性質,因為它們的電子構型相似,最外層的電子數也相同。
然而,一些更重的元素被證明可以用于其他類型的化學研究。例如,用一種相對簡單的技術來探測超重元素,可以測量原子在周圍氣體中附著在物體表面的強度。GSI的實驗表明,(第114號)在金表面可形成類似于其同族物鉛的金屬-金屬鍵,但這種鍵要弱得多。換句話說,超重元素的反應性更低,更穩定。與此同時,(第112號)與金的相互作用遠不如它的同族物汞強烈。(第113號)更難進行實驗研究,但JINR的初步觀察以及珀什納的計算表明,它與金表面形成的化學鍵相對較強,盡管要弱于其同族物鉈。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族元素中,隨著原子的增大,化學鍵的強度減小。但是要充分解釋超重元素的化學性質,珀什納的計算還必須考慮相對論效應。在原子量非常大的原子中,位于最里層的電子和原子核之間有超強的相互作用,其電子的運行速度非常快(可能超過光速的80%),從而導致它們的質量增加——狹義相對論預測到了這一點。這使它們更靠近原子核,也意味著它們可以更有效地屏蔽外層電子。這改變了外層電子的能量,從而改變其化學反應性。
相對論的極端
相對論效應已經為人所知。例如,金的微黃色和汞的低熔點均是因為相對論效應所致。超重元素表現出這些極端效應很難根據基本原理精確計算。沙德爾說,研究人員在2002年發現了相對論效應如何導致(第105號)的性質與同族物鉭大相徑庭。這一發現令科學家興奮不已,它為我們繼續探索超重元素的化學性質提供了巨大動力。
杜爾曼說,化學家們并不認為到目前為止觀測到的相對論偏差可以否定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即同一族元素具有使其有別于其他族元素的相似性質。在他看來,研究人員在找到第120號之后的元素前,不會發現明顯的化學周期性消失。對此,他這樣解釋:“幾個軌道的能量開始變得非常接近,以至于不再出現有規律的模式。”這一趨勢似乎已經在2018年的計算中得到了證實。該計算表明,可能不像它的同系物氙和氡那樣是一種惰性氣體。它最外層的電子軌道已變得模糊,因此它的反應性可能比它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位置所顯示的還要強。
長期以來,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一直利用光譜直接測量電子能級。從本質上說,這涉及向原子發射光,以測量當粒子躍遷到高的能級或低的能級時,電子吸收光子和發射光子的能量。但是在單個壽命很短的原子上做這個實驗極具挑戰性:在標靶消失之前,如何以足夠的靈敏度進行測量?但在2016年,GSI的一個團隊測量出了半衰期為51.2秒的第102號元素锘的單個原子的電離勢。研究人員用鈣離子束轟擊鉛靶,然后減慢氬氣中原子的速度,使它們聚集在鉭絲上,以每秒4個左右的速度制造了諾原子。研究人員周期性地采用二步法將電子激活:先加熱鉭絲,使其釋放出的锘原子變成氣相,然后用激光將其激發,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幾秒鐘之內。在后來的工作中,他們利用這種光譜測量數據來推斷三種锘同位素的原子核的形狀和結構,最后得出結論:它們不是球形,而是橄欖球形——一種影響電子結構的畸變。目前,該團隊正在努力將測量范圍擴大到第103號元素鐒。
日本原子能機構(JAEA)的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不同的電離能測量方法。在他們的裝置中,超重元素的原子從標靶中反沖出來,在氦氣載體射流通過一根加熱鉭管時被捕獲。原子將電子轉移到金屬表面,然后被送到一個驗證其特性的α粒子探測器中。日本原子能機構重元素核科學研究小組成員詠裕一郎表示:“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可以測量半衰期只有幾秒的元素的電離能。”詠裕一郎和他的同事用這種方法測量了從鐨(第100號)到鐒(第103號)的電離能。正如計算所預測的那樣,相對于原子量較輕的同族元素镥,相對論效應使鐒的電離勢比通常的周期趨勢所表現的要低。詠裕一郎介紹說,他的團隊目前正在開發一種新的方法來測量鐒之后的元素的電離勢,因為這些元素的揮發性不足以使這種表面技術得以應用。
元素分解
即使第118號元素之后的元素可以被制造出來,研究它們的化學性質也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人們預計它們會很快分解。奧加涅相表示:“我不會說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目前我還不知道如何完成這項任務。”
然而,核科學家推測,能夠長期存在的超重同位素可能存在。和電子一樣,原子核中的質子和中子也以殼層構型排列,這使得它們的結構或多或少容易被破壞。根據預測,填滿殼層的粒子數量是特定的“神奇數字”,這使其具有穩定性,從而在原子衰變之前延長其存在時間。這一效應大致類似于惰性氣體的相對穩定性和非反應性,因為其電子殼層被填滿了。

卡特里納·烏爾曼(Cathrina Ullman)站在德國GSI重離子研究中心加速離子儀器內
有時,研究人員會討論元素周期表會在什么地方終止。這種事可能會發生,因為原子量非常大的原子的最外層電子可能不存在任何與原子核實際結合的狀態,所以根本沒有真正的化學性質可言。或者原子核一旦形成就會分裂。2018年5月,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重申了其立場:一種元素至少應該存在10-14秒。但一些化學家質疑:沒有時間相互作用的原子能否被賦予有意義的化學性質,從而成為一種元素?
這實際上是在問: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元素周期表是否會像當初門捷列夫所理解的那樣,仍然是一個以化學為基礎的體系?或者它是否會變成一個以非常高的核子密度為基礎的物質物理學體系?新元素必須排列在周期表的某個位置,但它們的位置可能會變成一種擺設,而不是用來表示有關其化學性質的有用信息。
然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化學家們需要創造出那些更重的元素。盡管技術難度很大,但尋找工作仍在繼續。理化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英人伊島說:“我們從去年6月開始尋找第119號元素。這肯定要花很長時間,也許是年復一年,每年100天或更長時間,但我們仍然會繼續開展相同的實驗,直到我們或其他人發現它為止。”
杜爾曼說:“我非常樂觀地認為,第119號和第120號元素將在未來10年內被發現。長期前景看起來似乎不那么光明,但在20世紀90年代我還是一名博士生時,看過該領域的‘大牛’們發表的一些關于解釋為什么第112號元素已經接近極限的論文。而在20年后,我們有了第118號元素,所以我想我們不應低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