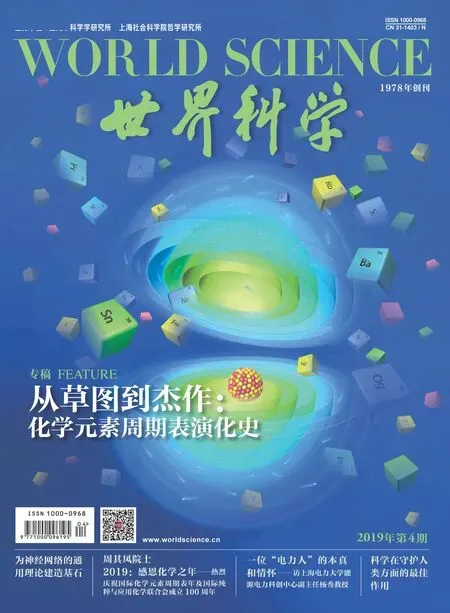科學和體育一樣,場外工作同樣重要
編譯 喬琦
2 019年2月14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以及英國研究和創新中心高調公布了一項總金額為3 000萬美元的項目,旨在將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臺(LIGO)探測天線的靈敏度提高1倍。2016年,LIGO因探測到黑洞相撞發出的時空漣漪(引力波)而震驚世界。
就在前一天,美國宇航局(NASA)公布了他們的最新天文計劃:一顆衛星將以三維和96種顏色繪制整個天空的地圖,其中包括數百萬的星系、恒星和行星。這個預計耗時2年的項目叫作“宇宙歷史再電離時期光譜光度計和冰層探測器”(Spectro-Photome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Epoch of Reionization and Ices Explorer,簡稱“SPHEREx”),旨在尋找大爆炸背后至今仍不為人所知的神秘力量。
這兩項計劃的公布都不算什么大新聞,新計劃總是層出不窮。就在這一周,NASA還宣布成立跨學科研究網絡,名為“生命起源前化學和地球早期環境研究聯盟”,旨在指導未來搜尋其他星球生命的行動。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特朗普總統簽署了“國家量子計劃”,旨在投入更多資金和人力將量子力學中最精深的部分應用于計算和加密之中。
“經典版”LIGO會在2019年春天的某個時間重新投入使用,尋找宇宙中的引力波,但升級版LIGO,也就是更加先進的LIGO+,在2024年之前都無法面世。而NASA的SPHEREx 最早也要等到2023年才發射。
但這些公告的結束時機提醒人們,科學的一個方面很少引起關注。特別是在諾貝爾獎期間, 我們為幾位英勇的愛因斯坦的靈感和發現時刻鼓掌。然而,科學研究中的許多實際行動其實是發生于科學之外,常常比實驗室的神奇成果早上數年,其中的部分工作還是由一群名字不為人知的人員完成的。還有一些參與者往往是知名政治家,例如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總統在1961年公布了登月計劃,他們也因此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對很多棒球迷來說,這項運動最激動人心的部分莫過于所謂的“熱爐聯盟”(hot stove league,即休賽期)。這個時候,英雄是精明的球隊總經理,他們招募、交易、交換、簽約、安排球員,球員就像棋子。比如布蘭奇·里奇(Branch Rickey),他在1947年為道奇隊簽下杰基·羅賓森(Jackie Robinson)并把他放到了一壘的位置,從而邁出打破棒球大聯盟黑白球員種族隔離政策的第一步。然而,在此之前,里奇故意用言語激怒羅賓森,在確認后者心理足夠強大,不會因為必然出現的謾罵、羞辱而還擊后才做出了上述決定。最近的例子則是現芝加哥小熊隊總經理西奧·艾普斯坦(Theo Epstein),他因重建波士頓紅襪隊以及芝加哥小熊隊而聲名鵲起,成為傳奇總經理。
這出戲碼在大多數職業體育聯盟中都會上演,就比如在NBA,總有大量球迷關注著紐約尼克斯隊,看著這支球隊每年尋找改變選秀權順位的機會或是苦苦追逐自由身超級巨星加盟。
在科學“熱爐聯盟”中,情況也是如此。
未來的諾貝爾獎是在國會委員會的聽證房間以及莊嚴的美國科學院專題討論會上,由手握預算的官員討論出來的;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會有實驗室,也不會有研究經費。這是著名作家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代表作《弱點》《說謊者的撲克》《魔球》等)在他的最新著作《第五種風險》(The Fifth Risk)中強調的一點。該書講述了美國能源部、商務部和農業部這樣的官僚機構中的公務員維護國家核武器庫和氣象衛星編隊的故事,同時還描述了他們在特朗普政府管理下的痛苦生活。
2019年夏天是人類登月50周年,屆時,全世界都會向阿波羅11號以及像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巴茲·奧爾德林(Buzz Aldrin)和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這樣的宇航員的勇氣與技藝致敬。然而,還有一個人同樣居功至偉,那就是1961—1968年間擔任美國宇航局局長的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

1967年,阿波羅1號的艙內大火直接導致3位宇航員喪生,此后,韋伯全權負責事故調查,制定了更加嚴謹的安全標準,之后又批準了阿波羅8號在1968年圣誕節期間執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繞月計劃。韋伯于1968年10月卸任,就在尼克松的總統大選之前,但至少有一架望遠鏡以他的名字命名,那就是屢次推遲發射的詹姆斯·韋伯空間望遠鏡,這架空間望遠鏡最后或許等到2021年才能上天。
政治、經濟、官僚、地理、歷史等因素將決定下一個大型望遠鏡或大型對撞機建造在何處。在過去的10年,攜帶筆記本電腦的物理學家不停在日本、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海洋上穿梭,游說同行和他們背后的政府將數十億美元投入到未來物理學研究之中。等到基本粒子在大型對撞機中呼嘯穿行時,推動這些項目的許多科學家都退休了。正如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加速器主管弗雷德里克·博德里(Frederick Bordry)2018年所說:“我現在的工作是在為年輕人鋪路。”
2016年2月,LIGO團隊的天文學家宣布他們聽見了黑暗深處的黑洞之舞,之前鮮有人聽說過LIGO的大名。這項發現震驚了世界,首次證實了引力波以及那些“時空死坑”(黑洞)的存在。而LIGO項目的倡導者和領導者、麻省理工學院的雷納·維斯(Rainer Weiss)、加州理工學院的基普·索恩(Kip S.Thorne)和巴里·巴里什(Barry C.Barish)也因此榮獲諾貝爾獎。
當然,在公布發現之時,LIGO其實已經工作了30年,消耗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0億美元。LIGO的成功是面對自然和專業懷疑時堅持、獨創和勇敢的傳奇。LIGO的雙子天線(位于華盛頓漢福德以及洛杉磯利文斯頓)本質上就是L形的真空管。在真空管內部,科學家利用激光束時刻監測相距2.5英里的兩面鏡子之間的距離是否發生了變化,以此來尋找引力波存在的證據。引力波會縮小兩面鏡子之間的距離,盡管這種變化連質子的直徑都不到。

LIGO兩個真空室之一,約有2.5英里長

巴里·巴里什(左)、基普·索恩(右)以及雷納·維斯因他們在LIGO和黑洞方面的研究,獲得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說服別人相信這個方法不是簡單、快速的任務。LIGO團隊將其諾貝爾獎的部分歸功于對這個項目持懷疑態度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他們不喜歡把一項物理實驗稱作“天文臺”),后者非常反對這項計劃,反復在研究中和研討會上詰問LIGO團隊,并要求拿出項目有效的實際證據。2016年2月10日,當LIGO團隊公開宣布他們記錄到黑洞相撞產生的引力波時,全世界看到了他們的回答。
當諾貝爾獎宣布的慶典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時,我就坐在LIGO項目最猛烈的批評者之一理查德·加爾文(Richard Garwin)身旁,這位在IBM供職、人脈廣泛、頗有影響的著名物理學家,他當時高興得眉開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