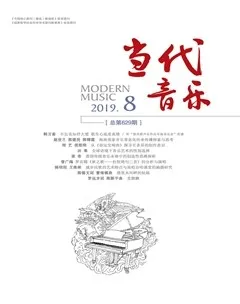藝術歌曲《木馬》中的印象派音樂技法
[摘 要]
《木馬》選自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彪西早期創作藝術歌曲集《被遺忘的小抒情曲》中的第五首,此套曲寫于1887—1889年間,屬于德彪西早期的藝術歌曲創作,歌詞選自魏爾倫詩歌集《無言的心曲》之《布魯塞爾:木馬》。本曲是套曲當中風格極為詼諧、膾炙人口的一首。本文將通過分析歌曲的創作背景、曲式結構、和聲技法以對這首作品所體現的印象派特征音樂語匯進行深刻了解。
[關鍵詞]木馬;德彪西;印象派;藝術歌曲
[中圖分類號]J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19)08-0112-03
一、背景
法國藝術歌曲的起源、發展和繁盛時期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是印象派繪畫、象征主義詩歌和戲劇藝術在法國得到極大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德彪西在藝術歌曲創作領域上逐漸走向成熟,印象主義音樂風格浮現發展的重要階段,他善于運用印象派繪畫技法般虛無縹緲、稍縱即逝的音樂描畫技巧,因此被認為是“印象主義”音樂的先鋒人物。“印象主義”起初被作為貶義詞用于音樂,是一種由于和聲線條不精確和曲式結構模糊而不受歡迎的寫作手法。一般來說,傳統和聲的使用手法體現在于在西洋大小調上進行創作,而印象派的和聲則打破了這種規則,以全音階、五聲音階、中古調式為代表,全音階的實質是在寫作時通過設置臨時變音使調式中的每個音居平等地位,從而削弱調中心感以體現更多可能性的和聲色彩。在《木馬》這首作品中,鋼琴聲部基本上維持著半音的連續進行,右手重音與左手低音層層呼應,甚至有同步的情況,弱化了傳統和聲的功能性,避免給出明確的終止式。
在那個文學藝術繁盛的時代,原有的學術型或古典型的美學定義被打破,新的美學流派破繭而出。印象主義摒棄浪漫主義重視宏大題材,以繪畫激起人們感情的觀念,將視覺重心移到凡人瑣事,從平凡的題材中透露出對生活和大自然的喜愛[1]。印象主義繪畫追求刻畫實物周圍的色彩與光影在瞬間的迷離變換,在對事物進行創作時總是考慮很多客觀因素,使得本位思想被模糊。因此對于印象主義的音樂作品而言,富有色彩效果的和聲遠比旋律重要。
在本作品中,我們能見到許多充滿“印象風格”特色的音樂寫法,如在寫作歌曲插部時和弦連續以三全音和弦關系進行、尾聲處使用低音減五度進行做色彩性上的遞進,造成不協和的音響效果,凸顯旋轉木馬的風趣幽默。德彪西堅信,法國音樂的要義,首先就是能帶來快樂[2]。《木馬》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歌曲中描繪的形形色色的人們:無論貧困、饑餓的人都在木馬的旋轉中獲得了快樂,而聽眾也從中獲得別致的享受。
二、歌詞來源
德彪西一生中公開發表了藝術歌曲六十余首,常以文學元素為中心素材進行創作,《被遺忘的小抒情曲》是其繼《華麗盛宴》后出版的第二部藝術歌曲集,根據法國詩人保爾·魏爾倫一八七四五年出版的第四本詩集《無言的心曲》而作,此集代表了魏爾倫詩歌創作的高峰,此時身陷囹圄的魏爾倫已徹底擺脫了巴那斯派的影響,以一個成熟的象征派詩人的創作面貌出現在公眾之前。《木馬》講述的是一個挨餓的窮漢強顏歡笑地騎在游樂場的旋轉木馬上,試圖忘卻自己的貧困、饑餓、煩惱和孤獨。
《木馬》在全曲一開頭就采用了毫不猶豫的快速有力的顫音進入,營造出猶如撥浪鼓一般充滿童趣的音色,讓人暫且跳離前曲音樂呼吸間傳遞的壓抑感并獲得別致另類的
風格感受。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數次轉換調性并使用了增減不協和音程,使調性徘徊游離,就像風吹過時樹蔭下冰冷的光與影疊致在一起,不規則而色彩斑駁。就木馬這首作品而言,旋律不是十分突出,情感相對套曲中的其他歌曲而言似乎也比較單一,但當中所涉及的和聲技法和調式調性卻極為豐富,和弦結構的多樣變幻使歌曲似一幅色彩繽紛的印象派畫作。
三、歌曲曲式結構分析
本曲可劃分為引子A、B、A1、C、A2、D、A3(尾聲)。采用回旋曲式進行創作,但其并非典型的回旋曲式,因為疊部的每次再現都變換了調性,但在A、A1、A2的主題句的和聲功能都是保持一致的。
引子從主調E大調的下屬音進入并一直在低音聲部以顫音的形式持續,描繪了木馬正在蓄力、為旋轉做準備的過程,右手節奏均等,皆是三連音+二八的組合,旋律和織體由高到底呈波浪狀起伏流動,預示了旋轉木馬的永不停休。
A段(1-16)主題材料“轉呀,轉呀”旋律音“B-E”屬-根四度跳躍的進行標志著木馬開始旋轉了,這是判斷疊部出現的重要依據。整段的伴奏織體都在使用均等型的三十二分音符旋轉式下行,快速短促的分解和弦使音樂充滿童趣,描繪了木馬正在快速旋轉的熱鬧場面;在和聲的運用上,第11、12小節前三拍均使用了連續的大三和弦的半音關系向上進行,前一小節分別運用A、bB、B上的大三和弦,后一小節分別運用F、#F、G上的大三和弦,和弦根音之間做半音級進并與旋律聲部同步,這種連續的大三和弦平行進行使和弦沒有立刻解決到穩定的音級上,因而調性色彩朦朧不清,如騎在旋轉木馬上般令人產生眩暈模糊之感,卻又令人陶醉,調性飄移恰恰呼應了旋轉木馬的本質,直觀表現出印象主義風格特征。
B段(17-26)轉入了F大調,宣敘、朗誦式的音樂語調將鏡頭拉近至游樂場的多個角色,臉蛋紅潤的孩子、疲倦的母親、黑衣的小伙子、紅衣服的姑娘……本段銜接緊密、以持續不斷下行、旋轉的三十二分音符烘托出游樂場熱鬧的氣氛。值得注意的是第17小節的和聲進行是屬功能到下屬功能的進行,這在傳統和聲學中被稱作“反功能”,原則上是不提倡使用的。作者卻借此巧妙地營造出了一種怪異的音響效果,貼切地描繪出“孩子”與“母親”“小伙”與“少女”角色之間的矛盾對立。在將這種“D-S”的進行重復了兩小節之后,緊接著和聲向下方級進進行到三級-二級-一級上,從整體上看此句的低音走向是Ⅴ-Ⅳ-Ⅲ-Ⅱ-Ⅰ的音階式布局,旋律則恰恰相反是上行的,與低音形成反向。隨即又轉入了F大調的屬調C大調,并與a小調不斷交替,本段最后兩小節的和聲進行是從二級七和弦進行到bB上的大小七和弦,與第26小節低音“bB”和右手聲部“C”構成的一個大九度音程共同構成一個復合性質的和弦。即此小節既延續了前小節的SⅡ和弦又是在為疊部A1作屬準備。大小調式交替、復合和弦滲透的手法運用大大豐富了本段和聲的色彩性,也生動表現了在游樂場的性格迥異的不同角色。
A1段(27-38)沒有依從典型的回旋曲式疊部調性回歸統一的傳統,而是將主題材料“轉呀,轉呀”作下方一度轉調模進至bE大調,場景隨木馬主題的再現切換到正在旋轉的木馬上,描繪了正當人們陶醉在嬉戲的時光中時,陰暗處的小偷已經看準目標蠢蠢欲動的畫面,第35-38小節處轉入了B大調,伴奏的右手聲部使用了前八后十六、四個十六分音符、兩個八分音符的前緊后松的節奏型,使氛圍高漲而緊張,左手聲部則是持續的二分音符顫音,表現木馬仍在繼續旋轉。低聲部屬九和弦的七音“E”與根音“#F”疊致成大二度并在左手一直持續著,大二度不協和的音響加劇了緊張的色彩,產生戲劇沖突感,表現了對在木馬上縱情玩樂的人們的擔憂焦慮之情。
C段描繪了饑腸轆轆、疲累的人們仍身處游樂場當中沒有離去,他們因為木馬的旋轉感到頭暈目眩,但另一面卻又為這種幼稚的把戲興奮不已,身體雖不舒適但精神上又很愉快。本段主調性是B大調,第一小節的T6也可以看作是同主音小調b小調的下屬六和弦,具有同主音大小調色彩的滲透,旋律與低音都是連續的半音化進行,同時做有兩個聲部的主音持續,又在兩個主持續音下方聲部形成了小三度音程關系,并以小三度關系作連續半音進行,連續的半音化寫作導致了連續的不解決,這種半音化色彩性進行豐富了和聲色彩的交織變幻,運用了印象主義色彩性的作曲技法。有趣的是第43、44小節,旋律以同音加不協
[HJ2.3mm]和的四度大跳的方式進行,“B”-“F”對應的和聲功能分別為B上的大三和弦及F上的大三和弦,兩個大三和弦之間以三全音關系進行,折射出不協和的色彩,又加以重音與歌詞巧妙結合,形象地講述了腹中空空的人們的快樂與低落交織在一起;第45小節使用了降六級和弦,折射了同主音小調色彩,本段結尾無明顯的終止式收束,旋律音停在G大調屬音上,低音則還是B大調的屬音持續,這里可以看作是復合調性,表現了人們陶醉游樂的同時卻感到迷惑不解的矛盾心情。
A2段調性為G大調,織體回到了旋轉式的三十二分音符分解和弦,主題再現,表示木馬仍然機械地旋轉著,本段的音區最高到“G”,是全曲高潮部分,結束部分的和弦性質是bB上的大小七和弦,與D段銜接。
D段描繪了天色漸漸變暗,晚餐的鐘聲響起,人群漸漸散去,而木馬還得繼續旋轉。本段旋律舒緩連貫,和聲色彩逐漸豐富,從bB上的大小七和弦進入,低聲部是大小七和弦的七音持續,穿插G上的小小七和弦,67、68小節的和聲是bB上的增三和弦,69-74小節是D上的增大七和弦和#D上的小三和弦的交替,上述和弦的使用令調性處于游離狀態,和弦之間相互獨立且不屬于任何一個調式的調內音,沒有功能性的進行和解決,使調性披上一層朦朧縹緲的色調,為原本輕松諧謔的音樂氛圍增添了一絲黯淡憂傷的色彩,將印象主義色彩性進行發揮到極致。
A3段是全曲尾聲,描繪了夜幕降臨,群星璀璨,教堂敲響了喪鐘,但在游樂場里旋轉的木馬卻感受不到悲傷,它不停歇地旋轉著,帶給人們忘卻一切煩惱的快樂時光。“轉吧,轉吧”主題原樣再現,調性回歸至E大調,但速度變慢,旋律音符時值擴大一倍,伴奏織體變為左手震音、右手波音的形式,力度極弱,烘托出夜晚的靜謐安寧;主題句的和聲也發生了變化,原本“E”音和“B”音下方對應的和聲應是T-D,而此處使用的則是S6-DTⅢ,同時低音“#C”-“#G”為#C大調主-屬功能性進行,可看作復合調性的寫法,為主題添了一絲夜空的朦朧神秘,豐富了調性的色彩性。84小節還原調式導音作小導和弦,滲入同主音小調色彩,下一小節又用升五音的大調導七和弦,通過大小調的色彩交替來鋪墊美麗的星空下教堂鐘聲的清冷透徹。91小節處歌曲回原速,歌詞寫到“轉呀,和著快樂的鼓聲飛奔”,此處的織體再次使用了顫音,表現木馬將在游樂場日復一日地旋轉。91、92小節可看作同主音小調降三音的導五六和弦,調性色彩再度變化,值得注意的還有93-96小節伴奏的內聲部進行“C”-“#F”、“E”-“#A”運用了減五度進行,是德彪西特色的印象主義色彩音樂的創作技法,尾奏織體以長音為鋪墊模仿鐘聲敲響,右手間歇性出現前奏三連音素材,使音樂結束得更自然,令人沉醉在夜色中充滿遐想。
總 結
德彪西在這首作品中頻繁借助半音化色彩性進行、同音調色彩交替、復合調性等創作技法來達到其描繪虛無縹緲的印象主義色彩音樂的效果。光與色彩是他注意的核心,冷色調與暖色調交匯,與印象派繪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際上疊部的印象派因素相對較弱,主題句的和聲功能和和弦結構變化較少,而插部的展開性更強,抒情處充滿幻想,似以音符描繪一幅畫,色彩初逐漸加深,間隙里還使用了過渡的顏色,色彩斑斕貫穿全篇。以B段舉例,模糊調性,徘徊在F(六級關系離調)C-a(關系大小調五級)迷幻絢爛的音響效果。疊部的諧謔與D段的抒情對比,邊緣化調式,回旋曲,帶有奏鳴性回旋曲式(戲劇性的沖突)。既滿足了回旋曲的題材,又在其中增加了戲劇性、斗爭性與畫面感。通篇用很多印象派的技法包住了主干音,使主干音既能體現出來又囊括了印象主義音樂色彩斑斕的和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