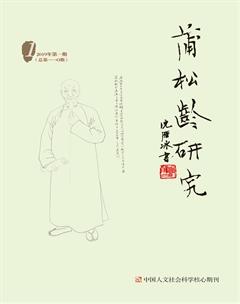在借鑒與繼承中求新變
王青
摘要:尚繼武的新著《〈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在對《聊齋志異》進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合理借鑒了西方敘事理論的有關理論觀點,批判繼承了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的有關成果,并融入著者獨特的學術眼光和多維的藝術思考,是一部在借鑒與繼承的基礎上實現了新變的力作。其開闊的理論視野、全面的研究范圍、嚴謹的論證邏輯和細實的文本解讀反映了尚繼武具有兼收并蓄的學術眼光和扎實樸素的治學態度。
關鍵詞:聊齋志異;敘事藝術;書評
中圖分類號:I207.41? ? 文獻標識碼:A
自《聊齋志異》問世起,人們就開始關注它的敘事藝術。清代馮鎮巒、何守奇、但明倫等人為《聊齋志異》所作的評點、題辭、序跋,零星地涉及了這一論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敘事學被引介到中國,一批學者“認真地翻譯了英、法、美諸國的一些重要的敘事學著作,令人視野大開” [1]1,打開了中國小說理論研究與小說批評的新視窗。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研究《聊齋志異》的敘事藝術,推動了《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向新范式的轉型。尚繼武在這一領域執著探索,歷經十余年而不懈,獲得了頗為豐厚的研究成果。最近,他的新著《〈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批判繼承了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的有關成果,借鑒了西方敘事學的理論觀點和批評方法,融入了他獨特的學術眼光和多維的藝術思考,對《聊齋志異》敘事藝術做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是一部在借鑒與繼承的基礎上實現了新變的力作。
一、對西方敘事學理論的借鑒與改造
誕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敘事學理論迅速占據了文學批評理論的重要領地,在深刻影響了現代文學理論的同時,也為小說藝術研究帶來了新轉機。美國文學理論家阿伯拉姆指出,“這些年來,批評界對敘事小說的理論和技巧有著極大的興趣,興起了‘小說學或者(用一個日益廣泛地被采用的術語來說)‘敘事學” [2]119。華萊士·馬丁一度言稱,“在過去十五年間,敘事理論已經取代小說理論成為文學研究主要關心的論題” [3]7。在我國小說批評理論領域,西方敘事理論的影響也相當深遠——雖然我國有悠久的敘事傳統,但是當代中國敘事學無疑是在西方敘事學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
既然討論的是《聊齋志異》的“敘事藝術”,《〈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自然就繞不開西方敘事學這一“顯學”。該書共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其他五章圍繞時空敘事、敘事序列、敘事修辭、人物群像和敘事情境等方面對《聊齋志異》的小說文本做了深入分析,從嶄新的角度評述了蒲松齡在小說敘事藝術上取得的成就。從后五章的內容看,該書顯然借鑒了西方敘事學的理論框架、核心觀點和批評方法。西方敘事學“在故事層面,理論家們聚焦于事件和人物的結構;在話語層面,敘述者與故事的關系、時間安排、觀察故事的角度等成為主要關注對象” [4]5。圍繞上述研究主題,西方敘事學理論家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敘事文本、故事結構和敘事技巧的批評術語和概念范疇。該書大部分章題使用了西方敘事學的批評術語,對作品的闡釋也借鑒了西方敘事學的研究視角和批評方法。如第二章《時空敘事:變幻中的奇正相生》重點分析《聊齋志異》時空敘事的作用和效果,第三章《敘事序列:與文體形態的肌理共存》從敘事序列角度探討小說文體的分類問題,第四章《敘事修辭:體豐意腴的獨特生成》論述了《聊齋志異》的反復、隱喻、懸念、反諷等敘事辭格的構成機制和藝術效果;第六章《敘事情境:多重視角與敘事介入》剖析了《聊齋志異》的敘事情境、敘事轉換和敘事介入。其實,《緒論》一章也帶有鮮明的西方敘事理論色彩。這一章將《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整體性創新概括為四點:(1)師法史傳模式,大膽突破創新;(2)眾體兼備,新在傳奇;(3)人物中心轉移,敘事切近民間;(4)融情志入敘事,提升小說品格 [5]4-18。其中,第一點是在分析《聊齋志異》敘事時序、敘事情境、敘事空間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第二點是將《聊齋志異》與唐代傳奇的敘事序列進行比較后得出的結論,第三點則建立在對《聊齋志異》敘事日常化、民俗化等特征體認的基礎之上。
借鑒異域文學批評理論容易出現的弊端之一,就是簡單移植、“穿靴戴帽”。西方敘事理論體系的建構基礎是西方現代敘事文本,用它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文言小說,很容易引發質疑。比如:借鑒西方敘事理論體系研究文言小說,能否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者是否僅僅借用其名詞術語,而沒有改變批評實質。該書著者對這些質疑有充分的預估和思考,力求避免在研究中出現上述弊端。著者認為,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與敘事學理論在思維模式、操作方式上既有共性,又有鮮明的個性,這決定了研究《聊齋志異》的敘事藝術不能完全照抄西方敘事理論分析模式和批評方法,應該吸收其中有助于深化對《聊齋志異》敘事藝術認識的營養成分,甚至在某些時候僅把敘事學理論視為具有參考價值的認識工具、批評工具 [5]44。正是基于這樣的借鑒眼光和研究思路,著者對西方敘事理論的部分概念、觀點做了適當改造,使之本土化、個性化,更適于用作觀照《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視鏡。
著者對西方敘事理論的改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敘事時空功能的改造。西方敘事理論關注敘事時空的角度和目的具有特殊性。在西方敘事理論家看來,“敘事文作為本文只具有一種時間性,那就是從閱讀過程中獲得的間接時間性”,研究時間的目的是理清“故事和文本之間年月日的次序關系” [6]79-80;空間“可以靜態地或動態地起作用。靜態空間是一個主題化或非主題化的固定的結構,事件在其中發生。一個起動態作用的空間是一個容許人物行動的要素” [7]109,研究空間的目的是“發現確定、重復、積聚和轉變的初步結合,以及不同空間之間的相互關系” [1]108。著者將“敘事時空”一詞的語序調整為“時空敘事”,將“時空”元素視為推動小說敘事的藝術手段,而不是視為簡單揭示事件次序的手段(時間)或者故事發生的自然背景(空間)。于是,在西方敘事時空研究處于中心位置的“時序、錯時、節奏”等論題,在該書中被《聊齋志異》時空敘事的“拓展、敘事功能、敘事效果”等論題所取代。其二,對人物角色功能的改造。在西方敘事理論家看來,人物只是行動的符號,是“行為者”,而不是具有豐富情感和獨特個性的生命體。“行為者的類別我們稱之為一個行動元。……一個行動元就是其成員與構成素材原則的目的論方面有相同關系的一類行為者。” [7]28因此,西方敘事理論對人物的分析往往忽略了人物思想性格對行動的指導、調控或決定作用。該書著者吸取了西方敘事理論的合理成分,著重分析了《聊齋志異》的人物群像及思想性格,歸納了人物的行動特征,揭明了人物思想性格對故事情節和自身行動的推動作用,發掘了人物群像的文化內涵。其三,對敘事序列功能的改造。從敘事邏輯的角度研究故事的深層結構,是西方敘事理論家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法國敘事學家布雷蒙使用“敘事序列”這一概念指稱敘事的基本結構單位之間的邏輯關系,希望通過對敘事序列的分析“畫一張為數比人們想象要少得多,而一個故事敘述者必在其中進行選擇的典型序列的圖表” [8]156,并為所有敘事文本找尋隱藏在復雜多變的故事情節背后的敘事通項(模式)。著者雖然借鑒了西方敘事理論的有關方法和視角分析《聊齋志異》的單一敘事序列和復合敘事序列,但是其目的不在于找出《聊齋志異》的敘事通項,而是創造性地將敘事序列與小說文體類型這一問題關聯起來,嘗試為研究、厘清《聊齋志異》作品的文體類型提供切實可行的新思路。這些對西方敘事理論的“局部”改造,反映了著者善于找尋并把握西方敘事理論批評視界與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創作藝術的契合點,在理論移植方面具有“運用眼光,自己來拿”(魯迅先生語)的科學借鑒理念。
二、對中國傳統小說批評理論的揚棄
在《〈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著者看來,西方敘事理論的基本觀點和批評方法只是審視、評價《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中介和工具,而非研究《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目的所在。正如著者所說的,他既無全面系統地運用敘事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聊齋志異》的意圖,也無創立新敘事理論體系的想法,只是借助西方敘事理論對《聊齋志異》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或作品中有代表性的敘事文本進行分析與總結,力求得出較為全面的、較為系統的結論 [5]45。因此,借鑒西方敘事理論僅是該部著作的“表”或“術”,對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的揚棄才是該書的“里”或“道”。
蒲松齡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蓬勃發展并趨于成熟,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說批評形式與理論體系的時期。在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前后,李贄、葉晝(托名李贄)、金圣嘆、毛氏父子、張道深、脂硯齋等小說批評家對《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作了系統批點。他們的評點和所寫的題跋、讀法、凡例,涉及了小說敘事藝術的一些重要命題。該書著者認為,“雖然目前尚未發現有文獻可以證明蒲松齡研讀過上述小說評論家對這四部奇書所作的評點,但是蒲松齡生活在這樣一個小說評點及小說理論發展的高峰期,《聊齋志異》的創作、匯編成書也處乎其間,要說《聊齋志異》的敘事技巧、敘事謀略絕未受到章回小說的敘述藝術或有關小說評點理論的啟發,似乎難以令人置信” [5]27。因此,著者在對《聊齋志異》的敘事藝術進行分析評價時,非常注重從傳統小說批評理論中汲取營養,使立論根植于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論土壤,不至于被西方敘事理論引向單純注重文本形式的路徑上。
首先,著者從中國古代小說“發憤著述”的傳統入手,分析了《聊齋志異》的創作緣起觀,并對蒲松齡“孤憤”的內涵做了合理拓展。中國文人歷來有將心中的郁結不平、萬端感慨訴諸著述,借以宣泄情感、表達思想、宣明立場的創作傳統。司馬遷將這一創作緣起觀概括為“發憤著述”,韓愈稱為“不平則鳴”。蒲松齡《聊齋自志》所說的“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9]3,表明了他的創作內在動力與發憤著述的傳統有內在的淵源關系。著者認為,蒲松齡將《聊齋志異》的創作緣起上溯至司馬遷的“發憤著述”,能夠憑依史傳的權威與崇高提高小說品位,有推尊小說文體的意味,而且比明初瞿佑“哀窮悼屈”的小說創作觀要深刻得多 [5]19-20。當然,著者沒有為“發憤著述”中“憤”的內涵所拘囿,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延伸,將蒲松齡的“孤憤”理解為“與政治批判有所區別的、屬于蒲松齡對人生與社會的獨特體驗、思想情感”,這一拓展更貼近蒲松齡的思想實際。著者還深刻地指出,蒲松齡融“孤憤”入小說,不僅使《聊齋志異》成為對現實世界的象征與隱喻,具有鮮明的詩化色彩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而且推動了文言小說創作由注重“人奇事奇”向追求“人奇事奇”與“述情之真”完美統一的轉變,扭轉了文言小說的創作重心 [5]23-25。
其次,著者雖然立足于古代小說理論虛實觀的視角考察《聊齋志異》的敘事技巧,但是與古代小說理論重視“實錄”“紀實”不同的是,他更重視《聊齋志異》虛構技巧的運用。受史傳敘事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往往嚴守虛實之辨,作家也大多師法史傳,以尚實抑虛的觀念指導創作,蒲松齡也不例外。著者描述了《聊齋志異》的史傳敘事印跡,分析了蒲松齡崇史尚實的藝術觀念,揭明了《聊齋志異》在突破史學敘事藩籬方面的藝術創新所在。著者認為,《聊齋志異》所寫的是發生在社會現實中的特異之事、有關仙道釋佛的神秘之事、關乎妖狐鬼怪的詭譎之事和純屬處于蒲松齡虛構的無稽之事,屬于“因文生事”,因此蒲松齡可以馳騁文筆,“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10]18,從而獲得了打破史家敘事清規戒律,發揮裁剪素材、虛構故事、敘事寫人的藝術才干的空間和機會,使《聊齋志異》在眾多方面突破了史傳的敘事觀念,敘事技法有了新的變化 [5]7。著者著重分析了《聊齋志異》中人間、仙界、鬼域時間節奏的差異,以及由此構成的非對稱性錯時的藝術效果;分析了《聊齋志異》虛擬空間的敘事功能,并單獨設立節次論述蒲松齡創設的第三敘事空間的特殊文化意蘊和藝術價值;著重分析了《聊齋志異》中完全屬于蒲松齡虛構的作品的深刻隱喻意義與批判價值。著者的這些基本思路和主要做法,既有助于把握蒲松齡對中國古代小說思想觀念的小說本體觀、創作觀和功能觀的繼承與借鑒,也有助于把握《聊齋志異》高明的虛構藝術。
最后,著者在延用古代小說批評家評價人物的尺度的同時,更加重視發掘《聊齋志異》人物群像隱含的文化意蘊。東漢的桓譚、班固對當時所謂的小說文體評價甚低,認為小說為叢殘短語,虛浮淺薄,屬于“小道”,“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11]1746。后世受此影響,遂將小說功能定位為“補史之闕”“裨益教化”。這一小說價值觀與中國古代人物評鑒觀交融一處,促使小說批評家以道德倫理為尺度,分析、評價小說人物形象。如毛宗崗評糜竺、曹操遭遇火燒之事說:“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陽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于燒,天所以留奸雄也。” [12]137張道深評《金瓶梅》人物說:“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個豪杰悌弟。誰謂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為盡滅絕也哉?” [13]42著者還注意發掘人物的道德情操和思想情感,比如,將《聊齋志異》女性人物置于封建社會男權文化的女性期待背景下加以分析,并將她們與其他文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做了對比,指出《聊齋志異》的女性人物具有獨立的人格、過人的才干、超凡的見識和嶄新的愛情觀念,是蒲松齡按照一定的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對女性人物加以詩意化和審美化描繪的結果。著者還以封建社會理想的文士人格風范為參照,指出《聊齋志異》文士人格移位的主要表現是由尚學識修養轉向重科舉制藝、由“心懷天下”轉為“關注自我”、由重義輕利演為趨利重財 [5]238-241。設若一直按照這樣的思路走下去,著者對《聊齋志異》人物形象的分析就會缺乏新意。可貴的是,著者在挖掘了人物形象隱含的文化元素之后指出,《聊齋志異》女性人物帶有伸張女權、沖擊男權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具有堅實的社會現實、文化文學淵源和思想感情的基礎;《聊齋志異》文士人格的移位是封建文人自我意識覺醒、人格走向獨立的表現,也是明代以來文人在啟蒙主義思潮和個性解放意識的影響下人格移位的延續。
由此可見,著者不僅對傳統小說批評理論具有敏銳的辨析力、深刻的判斷力和出色的歸納能力,而且持有獨特的理論標準和價值尺度。著者能立足于傳統小說批評理論而不被它所左右,能汲取傳統小說理論的合理成分而拋棄其僵化成分,體現了一位學者應有的學術品質。
三、《〈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新變
批評方法和理論體系的更新往往是開辟研究新路徑、突破研究“高原現象”的必由之路,但是一味追求方法和理論的新穎,往往導致求“新”的目的遠過于求“真”的目的、“重視橫向的移植或模仿,輕視縱向的傳承和轉換” [14]7的弊端。《〈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借鑒西方敘事理論而有所改造,繼承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而有所揚棄,其具有辯證色彩的理論與方法的取舍策略不僅為著者靈活而自由地歸納《聊齋志異》敘事藝術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也為著者的研究創新準備了有利條件。
首先,研究思路有創新。著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借鑒西方敘事學基本理論框架之內,以文本分析為基石,兼取西方敘事理論和中國傳統小說理論的批評方法,注重橫向比較和縱向探源。這一研究思路具有鮮明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建構了相對全面的考察《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框架。這兒所說的“相對全面”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就現有研究《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成果而言,該書涵蓋的主題最為全面。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借鑒西方敘事理論研究《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成果往往著眼于敘事理論的某一個角度,或僅著眼于《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某一方面,比如專門研究《聊齋志異》的故事類型、敘事情境或某種敘事修辭格。該著作則涵蓋了敘事時空、敘事修辭、敘事序列、敘事情境等研究主題,還將《聊齋志異》和《鏡花緣》的文士、女子做了比較研究。二是就研究所剖析的文本數量而言,該書剖析的作品數量最多。據章培恒統計,《聊齋志異》共收作品491篇,另有附錄9篇 [15],該書對這些作品做了全面解讀和剖析。比如:著者在考察所有作品的基礎上,劃分了《聊齋志異》敘事時間的呈現方式和敘事空間的類型,重點考察了功能型人物的分布情況,準確反映了《聊齋志異》敘事序列的使用情況。上述兩個“相對全面”,反映了該書著者具有的扎實而嚴謹的治學態度。(2)突顯了《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的 “歷史坐標”。任何文學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都是在繼承前人的創作經驗和創作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改造或創新的結果。換句話說,作品只有被置于文學流變的歷程中加以考察,其藝術創新價值才能真正凸顯出來。從這個角度審視《〈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一書,我們完全可以說,該書著者具有歷史的眼光和發展的眼光。為了探明《聊齋志異》時空敘事的創新之處,著者對歷代文言小說的時空敘事策略做了梳理,分析了文言小說形式各異的時空元素的敘事功能,描述了《聊齋志異》時空敘事的藝術淵源和獨特個性;回顧了不同時期小說人物群像的角色分布情況,得出了小說人物中心隨時代的變遷而逐漸“下移”的結論。著者認為,中國古代小說人物中心的前兩次“下移”,分別發生在唐代和宋明時代,而《聊齋志異》實現了人物中心第三次“下移”,主要表現為人物所處社會圈層的下移、人物居住區域的外移和人物行動主題的轉移 [5]223-235。這樣的研究路徑既能找準《聊齋志異》敘事藝術在小說藝術史上的定位,又能使立論基礎更加堅實,論證更加嚴謹而有說服力。
其次,研究策略有創新。在具有引領作用的研究思路確定之后,研究策略的選擇往往影響著研究的深度和成效。《〈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結構布局和行文脈絡顯示,著者采取的研究策略具有以下創新點。(1)文本形式研究與故事內容研究并重。西方敘事學經典批評的基本思路是將文學本文視為自足的、具有內在統一性的符號系統,將批評焦點從文本的外部因素和符號內容轉向文本的內部結構規律及各敘事要素的關系。該書著者對《聊齋志異》敘事時空要素、敘事序列、敘事情景、人物功能的分析和闡述,就是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進行的。但是在具體論述中,著者在文本形式的條分縷析中融入了對故事內容、人物思想性格和作品主旨的闡釋,而這些內容是為西方敘事理論所忽略的或排斥的。正是這種融入反映了著者對中國古代小說批評重作品內容這一傳統的繼承,強化了研究的本土化、個性化色彩,同時使該書平添了扎實穩健、細膩厚重的風格特色,從而免于陷入公式化分析、形式化概括的泥潭。(2)人物的行動功能研究與思想情感研究兼顧。西方敘事理論家大多將人物分為主體-客體、施予者-接受者等二元對立的類型組合,與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劃分人物類型的取向迥然相異。這樣的做法有其道理所在,因為確實有些故事即便更換了人物的身份、性別和思想,也不會改變自身的基本結構和敘事價值。《〈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著者發揮了敘事學人物類型分析的優勢,按照行動特征將《聊齋志異》中的人物劃分為不同的行動元或群體。然而,在著者看來,人物分析從來都不是純粹的符號分析或純粹的行為分析,而是對人物外部行動和內部行動(思想情感及其活動)、外部表現和內在品質的分析。著者在敘事學的框架內研究人物行為結構的同時,注重對人物思想性格及行為社會意義的發掘與闡述,從而確保對敘事框架與人物形象的研究達到和諧與統一。(3)敘事序列分析與文體研究融匯。就其實質而言,敘事序列排斥了故事的豐富內容,只篩選功能性事件并關注事件之間的聯系,其實質是敘事理論家為不同的故事找到的敘事通項。著者運用這一批評維度歸納了《聊齋志異》的敘事序列類型之后,將它與《聊齋志異》小說文體研究嫁接起來,不僅促成了東西方小說研究主題的碰撞,實現了理論借鑒與本土研究的交融,而且為研究《聊齋志異》中作品的文體類型打開了新視角。著者指出,《聊齋志異》中那些不包含功能性事件和有功能性事件但沒有形成敘事序列的作品,其文體特征與博物體小說、志怪體小說或語林體小說相近;那些使用單一序列的作品,有的近乎寓言體或志怪體(敘事簡潔的作品),有的近乎傳奇體(敘事細膩的作品);那些使用了復合敘事序列的作品,文體特征與唐傳奇相類,藝術功能甚至超越了后者 [5]153-155。這一研究“串聯”雖然沒有徹底解決《聊齋志異》作品的文體類屬問題,但是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和借鑒價值。
最后,以上述創新為前提條件和先在基礎,著者實現了研究結論的創新,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1)對《聊齋志異》敘事時空功能的新論斷。能夠體現該書關于《聊齋志異》時空敘事研究的新觀點的,當屬著者對《聊齋志異》的景物描寫、非對稱性錯時、第三敘事空間等時空要素的敘事功能研究所得的結論。著者分析了蒲松齡筆下的自然景物描寫、仙界鬼域景象描寫的特殊價值,認為無論哪一種景物描寫,蒲松齡“均將一股深情滲透其中,‘設身處境地為人物著想,而不是僅以置身景外的方式客觀冷靜地羅列景物”,而且“往往脫離俗套,不以奇幻怪異的景象驚駭讀者耳目,而以鮮明的形象、流暢的文脈和涌動的情意感染讀者” [5]72-73。對于《聊齋志異》的第三敘事空間,著者將之描述為情感自足的世界、情感平衡的世界和禮教隔絕的世界,認為它是蒲松齡拓展藝術空間、提高其敘事功能的創新產物,不僅為消解或顛覆封建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對封建禮教具有強烈的沖擊力,而且為青年男女抒發對生命的滿腔熱愛、實現愛情理想提供了在封建社會中難以存在的人生舞臺 [5]133。著者還結合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考察了《聊齋志異》的非對稱性錯時手段,認為蒲松齡借助“非對稱性錯時的敘事藝術手段,創造性地構建了嶄新的敘事序列,使情節翻轉折進或橫起波瀾,使敘事線條變化萬千” [5]77,使“讀者產生一股以一般自然經驗為基礎的真實順暢的生活感和超越一般時間經驗的奇異新穎的神秘感” [5]80。這些都是著者基于文本細讀得出的切實之論,具有獨創性。(2)該書針對《聊齋志異》的人物角色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觀點。學界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聊齋志異》的女性人物是男權文化的產物,承擔著家庭、婚姻和社會的種種重負,帶有濃郁的封建禮教色彩;男性人物尤其是年輕的書生,或者融入了作者的人生體驗和思想特點,或者是作者復雜的文化心態、微妙的隱秘心理的外化和臆造的產物。《〈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著者通過對大量作品有說服力的分析和歸納,得出了與上述看法有異的結論。在著者看來,《聊齋志異》具有宣揚女權的傾向,主要體現在凸顯了女性追求愛情的主動性、為女性提供新的愛情發生機制和戀愛模式、描寫了女性“文士化”的生活方式和賦予女子超乎男子的特異人格與杰出才干等方面;《聊齋志異》的文士與社會現實中的文士一樣,呈現性別特征矮化、政治理想變異、人格重心轉移和文士風范隱退的群體特點,并非完全充當了作者自我慰藉代言人的角色。這些觀點能否為學界所公認,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最起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人們對《聊齋志異》人物角色的固有印象和刻板看法。(3)針對《聊齋志異》的敘事情境提出了許多新見解。著者拋開了將研究注意力集中在《聊齋志異》第三人稱敘事的一般做法,使用了較多的篇幅對《聊齋志異》的第一人稱敘事和人物敘事做了詳盡論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蒲松齡努力嘗試著使用第一人稱,以改善作品大量使用第三人稱敘事的單調局面,只是技法還不夠成熟;蒲松齡如果能自覺地認識到第一人稱敘事具有兩種不同的敘事眼光,以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對社會的深刻洞察力以及藝術表現力,定能創作出思想內涵更加深邃、故事情節更加豐富的作品 [5]310。這可以說是對蒲松齡敘事情境藝術的客觀而公允的評價。在全面分析敘事情景的基礎上,著者還討論了《聊齋志異》敘事情景轉換的實現機制和敘事效果,深化了對作品敘事藝術的認識。在敘事介入方面,最為精彩內容當屬著者對《聊齋志異》敘事介入時機和“異史氏曰”介入功能的論析和得出的結論。經過細致分析,著者歸納出《聊齋志異》有四種的敘事介入時機,分別是“故事前”介入、“故事中”介入、“故事后”介入和“故事外介入”(以“異史氏曰”的方式介入)。這是他全新的視角和獨創的結論 [5]365。
總之,《〈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一書是尚繼武十余年來《聊齋志異》研究成果的匯總和提煉,更是他辛勤耕耘于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心血的結晶。稱它是《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的集成之作也許有溢美之嫌,但是將它看作是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界借鑒西方敘事理論研究《聊齋志異》敘事藝術歷程的階段性總結,恐怕沒有人會提出質疑。我們期待著者以此為起點,在《聊齋志異》研究方面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參考文獻:
[1]楊義.中國敘事學[M]?蛐?蛐楊義.楊義文存: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阿伯拉姆.簡明外國文學辭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4]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尚繼武.《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
[6]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M].姚錦清,黃虹偉,傅浩,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7]米克·巴爾.敘事學:敘事理論導論[M].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8]克洛德·布雷蒙.敘述可能之邏輯[M]?蛐?蛐張寅德.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9]蒲松齡.聊齋自志[M]?蛐?蛐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M]?蛐?蛐金圣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11]班固.漢書[M].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4.
[12]羅貫中.三國演義[M].毛宗崗,評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張道深.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M]?蛐?蛐蘭陵笑笑生.金瓶梅.張道深,評.濟南:齊魯書社1991.
[14]張伯偉.中國古代批評方法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2.
[15]章培恒.新序[M]?蛐?蛐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