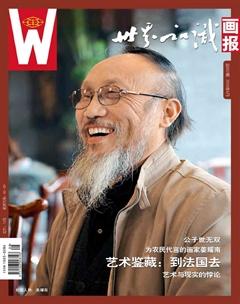寫實的面目
唐詩

Most Chinese artists studying in Fran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dedicated to learn the accurate, graceful and realistic styles of Western arts. A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which encompass a series of precise artistic theories and practice rul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arts. It is the reason why the then young Chinese painters were so obsessed with Western arts. For them, classic realism was not only an extremely fresh and stimulating art form but a kind of future for Chinese arts, though it was on the wane in the Western art world.
說到20世紀初留法的大藝術家,徐悲鴻總是最先被人想到的一位。他不僅是當時留法學子中的優秀代表,更在歸國后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和教育實踐吹響了變革中國繪畫的號角。他既是油畫家,也是國畫家,他的油畫投射出中國藝術的影子,而他的中國畫,浸潤著西方藝術理論與技巧的精華。
徐悲鴻從小學畫,有著深厚的中國繪畫素養和根基,而留法的經歷,則讓他對西方藝術有了系統的了解和認識,并為他之后走向中西融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礎。作為學院派寫實主義油畫的代表性畫家,徐悲鴻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期間,勤學苦練,刻苦鉆研,對于素描、油畫技巧掌握得極為醇熟。同時,他遍游歐洲諸國,去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參觀、臨摹,對西方古典寫實主義的奧義參透極深。
歸國后,徐悲鴻將西方所得運用于中國畫創作中,開啟了近代中國畫的改良之路。他曾在其著名的《中國畫改良論》中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這一論述幾乎成為近代中國畫改良的主旨,影響了當時以至之后的許多畫家。
其實,在20世紀初留法的藝術家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都是沖著西方藝術精準、優雅、寫實的風格而去的。與中國藝術相比,西方藝術就像科學,有著一整套嚴謹、準確的藝術理論和學習、實踐守則。這些不同于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讓當時的年輕中國畫家們心摹手追、動心不已。盡管在20世紀,古典寫實主義在西方藝術世界已經逐漸式微,但對于中國畫家來說,那仍舊是一種極為新鮮、刺激的藝術樣式。那是畫里的真實,也是當時中國藝術的一種未來。
與徐悲鴻同樣技巧精湛且兼容中西的藝術家吳作人,于1930年赴歐洲學習,先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后考入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白思天院長畫室學習。在藝術上,吳作人顯現出非凡的才能,入學第二年,便在全院暑期油畫大會考中獲金獎和桂冠生榮譽。白思天院長稱贊他“既不是弗拉曼畫派,又不是中國傳統,乃是充滿個性的作者”。
與徐悲鴻相比,吳作人的寫實更偏向于中國式的意趣,正是因為對于藝術民族性的思考,讓他走向敦煌,接受中國古代藝術審美與境界的陶冶。西北之行成為他此后藝術創作與理論的基礎,使他的藝術創作觀念更向中國審美體系回歸。
在當時的法國,寫實主義并非主流,但也是不能或缺的一股藝術力量。學習寫實主義的中國畫家,雖然同樣傾心于西方學院派的精湛技巧,但也表現出不同的喜好與風格。如顏文樑、呂斯百、周碧初等人,同樣以寫實技巧見長,同樣受印象主義影響頗深,卻因個人稟賦、氣質的不同而展現出不一樣的風格面貌。
顏文樑的油畫,長于風景、靜物,早年手法寫實,景色逼真,具有高度的造型技巧。留學期間接受古典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影響,作品在結構嚴謹、手法寫實的基礎上,又重視描繪外光和色彩的變化。
呂斯百的油畫長于風景、靜物,早年作品筆觸穩健有力,色彩純化雅致,注重畫面整體的真實性。在巴黎儒里昂油畫研究院學習期間,他選擇了徐悲鴻推崇的以謹嚴畫風著稱的新古典主義畫家、法蘭西藝術院院士勞朗斯為導師。畫風開始轉向對夏爾丹和塞尚的追隨,也研究印象主義的繪畫技術和風格。
周碧初留法師承印象派的藝術方法,在采用對比色并置和反襯技法的同時,更注意細筆觸和點簇的表現力與生動性,同時又融入中國民間藝術夸飾之精華和文人畫的點、線畫法。最終使其油畫別具中國特色和自身的藝術風格。
在當時的留法藝術家中,女畫家群體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支隊伍,如潘玉良、方君璧等人。1920年,方君璧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成為該校第一位中國女生;1924年,方君璧的作品《吹笛女》入選巴黎美術展覽會,這也是中國女性作品第一次參展。
方君璧因其家族與丈夫曾仲明的經歷,被記載于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但歸根結底,藝術才是屬于她個人的信仰與歸宿。
- 世界知識畫報·藝術視界的其它文章
- 宋瓷 低調中的高大上
- 公子世無雙
- 宋清作品欣賞
- 李輝作品欣賞
- 為藝術 為夢想
- 中國飛白書法家——李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