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社會科學方法論二元對立的新嘗試——對索耶社會突現論的研究
磨胤伶
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問題。一旦進入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我們必定會遇到路徑選擇的問題:是以個體及其行動為基礎研究社會及其結構,還是以社會及其結構為基礎研究個體及其行動。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路徑就是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的對立。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這兩種路徑都存在著各自的優點與缺陷,超越二者之間的對立是索耶構建社會突現范式的出發點。
一、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之爭
方法論個人主義是一種還原論,在它看來,個人是社會結構的最小單位,個體性質和規律是社會及其結構形成的基礎,因此,關于社會整體的性質及規律的認識必須依據個體特性的陳述來解釋。并且,只有完全依據個人事實的解釋才是正確的解釋。那些訴諸社會結構、制度因素以及諸如此類的任何解釋都不具有合法性。而與之相反的理論則被稱為方法論集體主義或方法論整體主義。這種理論認為,社會整體具有自身的性質和規律,它與有關它的組成個體的性質和規律具有質的差別。社會整體本身就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它是使個體的描述具有意義的基礎。[注]尼古拉斯·布寧:《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余紀元編,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9頁。
這兩種理論爭議的核心問題是社會存在論問題,即社會性質與規律是否真實存在。在方法論個人主義那里,只有個體是真實的,也只有個體能夠被觀察,因而所有社會現象都應由構成社會的個人來解釋,即使有部分方法論個人主義者承認社會性質的存在,但是,他們也認為這些社會性質只是理論的抽象模式,因而必須將它們還原到個體及其相互關系中。正如波普爾所說:“所謂的社會整體并不是經驗對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會理論的公設;雖然大家公認像這里集合的人群這種經驗對象是存在的,但說像‘中產階級’這樣的名稱代表這種經驗團體則是完全錯誤的。它們所代表的是一種觀念對象,其存在取決于理論假設。”[注]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季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486-487頁。而在方法論集體主義那里,除了個人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之外,社會整體也是一個真實的存在。涂爾干認為,方法論集體主義是“指一種可以或者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注]景天魁,楊音萊:《社會學方法與馬克思》(第1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8頁。。在這一理論中,個體及其活動是于先在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社會或集體是理解社會的主要對象,而個體只能通過它所參與的社會實踐來理解,因此,將有關社會的事實還原到個體的知識上是不可能的。
對于方法論個人主義,沒人懷疑它以個體作為分析單位的重要性。但是,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是否能夠還原為對個體及其相互活動的理解呢?在具體社會實踐中,行動的個體首先處在一定先在的社會制度、結構和規范當中,雖然社會的發展受到個體及其相互作用的影響,但是個體行動不僅受到個體自身因素的影響,而且其行動必然受到社會規則、結構和制度的制約,這些先在的社會實在是個體無法脫離的背景及前提。然而,如果部分方法論個人主義者承認這些先在的社會實在對個人的影響或制約,那么他們就必須解釋這些先在社會實在所依賴的個體及其行動,如此分析,就會陷入無限倒退,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又將停止在何處?
與方法論個人主義相反,方法論集體主義認為除個體之外的社會結構、規范和制度等社會實在也是真實的存在。同時,方法論集體主義也承認社會依賴于個體及其相互作用。但是,這一理論僅僅是強調社會、結構在解釋社會現象上的優先性,對于社會、結構如何既依賴于個體而又保持自身獨立這一問題則沒有進行解釋。因而,方法論集體主義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還原論,它僅用社會、結構諸如此類概念來解釋社會現象,并且,方法論集體主義在本體論上陷入二元論的危機。方法論集體主義過分關注結構、文化或制度等社會實在,弱化了個體,忽略了個體在社會發展與變革中的重要作用,這就使得對社會發展和變遷的理解陷入了先驗決定論。
二、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
霍布斯所提出的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是如何理解社會的經典問題之一。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形成了兩大陣營: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集體主義。兩者進一步發展,就形成了“微觀社會學視角”與“宏觀社會學視角”的對立。在兩者長期爭論的過程中,各自存在的優點與不足逐漸清晰。因此,嘗試將兩種方法論整合,成為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兩大趨勢之一。而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正是建立在復雜適應系統與突現論的基礎之上,對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整合提出新視角。
索耶認為,在任何社會環境中都存在著微觀—宏觀的持續辯證法:社會突現。他依據復雜適應系統的層級性,將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分為五個層級,形成了社會突現范式結構,如圖1所示。
(一)社會突現范式的基本特征——以層級為基本單位
索耶將社會看成一個復雜適應性系統,并把社會實在分為五個層級,這表明在其突現范式中最基本的單位是層級,而整個社會的最低層級則是個體。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結構中,其他層級都是建立在個體這一最低層級的基礎之上,是在個體基礎之上突現出新的層級性特征。每一層級對更高層級來說都起到基礎作用,并且每一層級都具有獨立性。可以說,每一個較高層級都是社會突現的表達。同時,在社會突現結構范式中,個體層級處在社會系統的最低層級,這表明社會突現范式承認個體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元素。而除了個體之外還存在其他的社會實在,這些社會實在高于個體層級,是個體及其行動產生的結果。社會突現范式的多層級性特征還確定了每一層級都具有各自的性質。雖然較高層級建立在較低層級的基礎之上,但是較高層級是與較低層級具有不同性質的層級,因此不能將較高層級的性質與規律還原到較低層級的組成部分的性質與規律上。也就是說,雖然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但是社會及其結構具有自身的性質和規律,而這些性質和規律不能完全依靠人的性質和規律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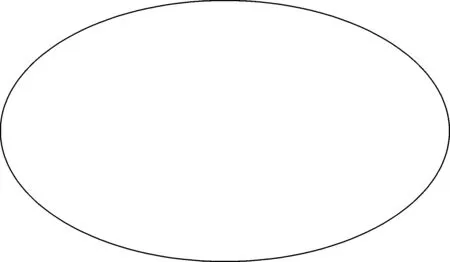

社會結構(層級E)文本(程序、法則、規則);物質系統和基礎設施(建筑、城市設計、通信和交通網絡)穩定突現(層級D)亞文化、俚語和流行語、慣用語、共同的社會實踐、集體記憶短暫突現(層級C)話題、語境、相互作用的框架、參與結構、相關角色和地位、任務相互作用(層級B)談話模式、符號相互作用、合作、商談個體(層級A)目的、主體、記憶、個性、認知過程
圖1社會突現范式結構[注]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5,p.211.
索耶借用心靈哲學突現論中的附生性(supervenience)與多重可實現(multiple realizability)為其社會突現范式的各層級之間的非還原性作解釋。在心靈哲學突現論中,意識是大腦整體有機活動產生的結果,大腦是意識得以產生的必要物質基礎。但意識本身與大腦活動不同,它從大腦活動中突現出來之后就具有自身的規律和法則,而這些規律和法則不能還原到大腦神經運動的規律和法則之上。大多數心靈哲學家把這一特性稱為附生。而從普遍意義上來講,附生表述的是較高層級的屬性必然建立在較低層級的屬性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之上,但較高層級具有與較低層級不同的性質與規律。例如戴維森,他依據附生這一概念解釋了心靈既建立在大腦物理特性的基礎之上而又具有非還原的特性。他認為,心靈的特性附生于物理的特性,如果兩個事物在所有的物理特性上完全一致,那么它們的心靈特質也完全相同。他的經典論述如下:“盡管我所描述的那種看法否認存在心理-物理規律,但它與下述觀點是相容的,即認為心理特性在某種含義上是依賴于物理特性或附生于物理特性之上的。也許可以認為是這樣的附生意味著不可能有在一切物理的方面都相同、只在某個心理的方面不同的兩個事件,或意味著一個對象不可能在某個物理方面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在某個心理方面有改變。不可通過規律或定義從這種依賴性或附生中衍推出可還原性:要是真可衍推出可還原性,我們就能夠把道德特性還原為描述特性,而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一點。”[注]戴維森:《心理事件》,載《真理、意義、行動與事件》,牟博編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251頁。在此,戴維森將心身關系問題與道德—行為關系問題作類比,認為如果道德不能還原為描述性的行為,那么心理特性與物理特性之間也不存在可還原的關系。心靈哲學依據附生解決了心靈或意識如何既依存于大腦,又獨立于大腦獲得獨立性這一關鍵問題,即心靈或意識與大腦具有相同的物質基礎,但心靈或意識與大腦是具有不同屬性的存在,因此,對心靈或意識的理解不應僅通過對其物質基礎的研究而獲得。這也解釋了突現性質與其構成基礎之間的關系,并回應了對突現論在本體論上是二元論的攻擊。
所謂多重可實現性,是指某一個領域所討論的某種事物的性質或狀態,可以由另一個領域所討論的多種不同的事物的性質或狀態來加以實現。[注]范冬萍:《復雜系統突現論——復雜性科學與哲學的視野》,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5頁。心靈哲學家們認為,盡管心理狀態必須附生于一些物理狀態,但是每一心理狀態的表征事例(token instance)可能會在不同的物理狀態中找到根據。例如,在心理上產生的疼痛感,不同的動物都能產生疼痛感,然而不同的物種具有不同的神經結構,因此,疼痛的心理狀態不可能是通過共同的神經結構產生的。如果說附生解決了突現性質與其構成基礎之間的關系,那么多重可實現性進一步證明了突現性質具有其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規律,它們不可能完全還原為組成部分的性質和規律來加以解釋,但多重可實現性依然證明了心理狀態的產生是以物理狀態為基礎的。索耶認為,社會各層級之間的關系與身心關系存在相似性,因此,可以借用附生與多重可實現來理解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解釋了社會及其結構如何既依賴于個體又具有非還原的特性。這就解決了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之間非此即彼的路徑選擇矛盾。
(二)社會突現范式的幾個重要范疇
1.相互作用
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相互作用作為一個獨立的層級,包括談話模式、符號相互作用、合作與商談。相互作用指的是個體的相互交流,它在社會突現中扮演重要角色,索耶甚至認為,相互作用是社會突現范式的核心。[注]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2005, p.170.在索耶看來,個體之間的交流是產生社會突現的關鍵,沒有個體之間的交流就不存在社會突現,個體之間的交流是社會突現產生的根本原因。為了證明個體之間交流的重要性,索耶首先借助了多主體系統模型。他通過計算機模擬建立了三個不同的人工社會,這三個人工社會中包含三種不同的行動主體——反應行動主體、認知行動主體與協同行動主體。這三個不同的行動主體以它們在交流過程中所使用的不同語言相區別。經過實驗,索耶發現,當行動主體相互作用時,宏觀的結構突現,并且在三個不同的人工社會中產生了不同的突現結果。在此,索耶用多主體模擬系統證明了突現產生的關鍵因素是個體之間的交流。同時,這也表明了,隨著多主體模擬系統的發展,復雜適應系統及其突現現象變得不再神秘,我們在理論研究中無法發現的問題以及無法預測的結果可以通過計算機模擬呈現。
作為社會系統的層級之一的相互作用層級,它的獨立存在表明,采用方法論集體主義那種將對社會理解還原為社會及其結構的方法無法獲得對社會微觀層面的理解,同樣,采用方法論個人主義也不能把握潛藏在社會宏觀—微觀結構之間的關系。顯然,索耶關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層級的理解受到了符號互動論的影響。人的社會化、人際互動是符號互動論的研究重點。這一理論認為,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社會。除了承認社會互動具有獨立性之外,這一理論還強調了社會互動對個體的因果力。在互動中,個體必須考慮對方正在進行以及將要進行的行動,且根據自身考慮的結果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并應付即將面臨的處境。當面對他人的行動時,一個人對某一意圖的強化或修改依賴于互動本身。在社會活動中,使得自己的行動方式與他人相適應是個人行動的標準。布魯默說,個人“被卷入一個巨大的互動過程之中,在這里他們必須對不斷變化的行動進行相互的調試”[注]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68.。可以說,相互作用層級是解釋社會宏觀—微觀結構之間如何發生關系的重要環節。
2.短暫突現與穩定突現
短暫突現和穩定突現都是個體通過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并且擁有存在于個體與相互作用之上的因果力。在許多社會理論中,索耶社會突現范式中的層級C與層級D通常被簡單地歸屬于社會結構。這些理論中關于個體如何通過行動形成社會結構的這一過程往往是模糊的,且不能體現出個體形成社會結構的動態過程。而索耶在社會實在中新增短暫突現與穩定突現兩個層級,正是要將社會形成的動態過程呈現出來。
短暫突現指的是在個體發生交談后產生的結果,它關注的是個體及其行動如何產生宏觀結構。方法論集體主義認為個體及其行動是在先在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因而,在對個體及其行動進行分析時必須考慮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突現范式同樣重視社會環境對個體行動的影響。然而,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不同的是,社會突現范式認為,個體及其行動能夠參與社會結構的建構,并對這種先在的社會結構進行改造。索耶以在談話分析中形成的相互作用框架為例,解釋了短暫突現這一范疇。在談話中,相互作用的框架在個體之間的交流中突現出來,并限制個體的行動。這兩個過程是同時發生的,且不可分割,它們不是一個連續過程中相互區別的兩個階段。個體之間的相互交流使得相互作用框架不斷產生,而這樣連續的過程又在那一時刻受到突現出來的相互作用框架的限制。突現出來的相互作用框架是一個動態結構,它隨著相互作用中的每一個個體的行動的改變而改變,它總是受制于繼續交談。
穩定突現是突現的第二種形式,又叫集體突現,它代表的是一個群體共同擁有的歷史。穩定突現與短暫突現之間的區別在于,短暫突現是由參與人數較少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且持續時間短,索耶用不超過一次偶然相遇(encounter)來對短暫做界定,同時,這也表示了短暫突現是在任意時刻發生的。而穩定突現是由參與人數較多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且持續時間超過一個偶然相遇。穩定突現具有穩定程度高低的區分,持續時間較長,則穩定度高;持續時間較短,則穩定度低。索耶把一些關于穩定突現的例子按穩定度由高到低排列:語言、名言警句、流行、同齡人的笑話、關于某部影片的集體觀感。
穩定突現是集體相互作用形成的突現,它與以“集體行動”著稱的社會理論所關注的焦點相同。然而,這些關于集體行動的社會理論認為,集體行動是個體直接產生或是簡單地通過相互作用產生的,忽視了其中關于個體之間的連結而產生的突現過程。而穩定突現所關注的則是通過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生成的自組織如何對社會及其結構產生影響。穩定突現要區分的是行動的微觀與宏觀層面。在社會突現范式中,個體行動屬于微觀層面,而集體行動屬于宏觀層面,二者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存在區別:第一,從形態上來說,二者是不同的現象,集體行動不能用個體行動來解釋。我們可以從語言與說話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語言是宏觀性、結構性的,而說話是微觀性的、隨機性的,我們在實際環境中的說話不可能完全符合語言;第二,從實際后果看,二者也是兩類不同的現象,個體行動完全依賴個人目的,而集體行動則依賴集體目的,個人目的是任意的,而集體目的是統一的。穩定突現就是要區分個體行動與集體行動,并表明由個體行動上升到集體行動的過程。
3.下向因果關系
索耶認為,在社會突現范式中,具有獨立性的每個層級都具有因果力,索耶的下向因果力分為兩個部分:高于個體的層級都能夠產生作用于個體的下向因果力;而作為獨立層級的相互作用,也受到來自較高層級的因果力。下向因果力解釋社會及其結構等宏觀結構如何對微觀行動產生影響。
個體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受到的較高層級的下向因果力是十分明顯的,例如個體在較高層級的限制下做出有限的決定,盡管不存在決定性的選擇,但是選擇組合的有限性本身就是一種限制。同時,較高層級的限制不會因為個體沒有意識到限制的存在而不存在。在社會突現范式中,索耶想要強調的是穩定突現、短暫突現以及相互作用對個體產生的下向因果力,它們與個體通過相互作用形成突現的上向動態過程不同,它們對個體的因果力不需要其它層級的協調而直接作用于個體。
在社會突現范式中,相互作用也是一個獨立層級,存在著較高層級作用于相互作用這個層級的因果力,且這一過程是不需要個體參與的。在一個社會整體中,社會文化結構預先規定了一系列行為方式、行為模式,如法律制度、社會道德、風俗習慣等,就像劇本一樣已經限制了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模式。因此,在新一代人進入社會時,其必須依照既定的模式進行交往。當然,社會突現范式的下向因果關系并不是要強調社會整體對個體層級或相互作用層級的決定作用。相反,社會突現范式認為,在社會整體中,個體的上向因果力與社會較高層級對個體以及相互作用的因果力同時發生。個體可以通過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改變已有的社會結構,這是個體上向因果力的體現,然而,這同時也是社會較高層級對個體因果力的體現,因為這已預設個體受到了下向因果關系的影響。下向因果關系也意味著社會整體具有適應性和自組織性,它能夠對子系統進行調整,以達到不斷發展的目的。上向因果關系與下向因果關系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同時產生、同時發生作用,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兩種因果關系都應被考慮。
4.突現圈
所謂突現圈是索耶為社會突現范式的解釋范圍而劃定的界限。索耶指出,社會突現范式并不能解釋社會科學所關注的所有問題,那些存在于突現圈之外的問題,應當由其他學科進行研究。社會突現范式所要解釋的是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而對那些已經形成固定形式部分的具體研究,則不再屬于社會突現的解釋范圍。這些部分或是突現產生的具體結果,或是當下的突現發生前就已經具有的具體物質結構,盡管它們都處在社會層級中,但是社會突現范式并不涉及對它們內部結構的解釋。
首先是層級E,即具有客觀物質形式的社會結構。層級E是已經固定在客觀物質形式上的穩定突現,它包括一個社會的技術和物質系統以及固定的文本,如憲法等。涂爾干也曾對社會結構與穩定突現做出過區分:涂爾干把穩定突現當作“潮流”,這樣的潮流“產生,消失,在各地傳播,以成千上萬種方式跨越并合作,并且,正是由于它們是不斷移動的,因而不能以客觀形式固定下來。”[注]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Rutledge Press,2002, p.313.涂爾干認為,關于這些“潮流”的例子包括個人主義、世界主義等。而當一種處在不斷變換中的潮流以物質的形式固定下來時,就成為具有具體物質形式社會結構。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社會結構與穩定突現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二者之間所呈現的穩定程度。突現是連續不斷的過程,社會結構是穩定突現生成的具體結果。社會結構是從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突現出來的。突現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動態過程,而由突現產生的具體結果的性質和規律不屬于社會突現的解釋范圍。
其次是層級A,即個體層級。個體在社會突現范式中,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產生突現的必要條件。然而,個體的物理發展,并不服從于來自上一層級的下向因果力。例如大腦的性質及組成完全依賴于有機的遺傳和發展,有關個體的這部分內容不屬于社會突現的解釋領域。社會突現范式感興趣的是相互作用層級、短暫突現層級與穩定突現層級在任意時刻對個體行動的限制以及個體及其行動在社會突現過程中的基礎作用。當個體行動或個體受到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影響和限制時,關于個體的研究屬于突現的一部分。例如,處在成長階段的個體的不斷變化是對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變化的反應,“80后”、“90后”這些標簽背后都包含了時代背景,那么,關于個體的這部分研究就屬于社會突現范式研究的范圍。
三、超越社會科學方法的二元對立
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各自的不足早已被一些社會理論家意識到,并且對其完善做出了有益的嘗試。最先就化解二者矛盾做出努力的是吉登斯,他嘗試用結構化理論超越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之間的對立,用結構的二重性來解釋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但這一結構化理論依然未能化解兩種方法的對立,而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恰好彌補了結構化理論的不足。
(一)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結構“不僅僅指社會系統生產和再生產中包含的規則,還指其中包含的資源”[注]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李康、李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87頁。。這些規則和資源不斷進入社會系統的再生產過程,使時空在社會系統中結合,并使具有相似特性的社會實踐超越時空變化而維持并具有系統形式。[注]于海: 《西方社會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第390頁,第390-391頁。結構自身在時空中不存在,它通過規則和資源實現自身。結構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并不是外在于行動者的事物,它是具有轉換性的規則,這些規則以社會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根基,同時也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這就是結構二重性。結構自身是外在于時空,是主體不在場的,而結構不斷涉入其中的社會系統則是主體在場且由其種種活動構成的。[注]于海: 《西方社會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第390頁,第390-391頁。因此,吉登斯對社會系統的結構化分析可以被認為是對建立在個體活動基礎上的社會系統,通過行動主體在特定系統條件下創造出來的各種規則和資源不斷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行動和結構二重性的辯證互動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核心。在他看來,結構和行動的關系不是“彼此分離和對立的事物,或者是理解世界的彼此相互排斥的思維方式,而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從一方面觀察社會實踐,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和行動;如果我們從另一方面觀察它,則可以看到結構。”[注]Ian Graib. Anchony Giddens,Routledge,1992, p.3.吉登斯通過改變結構在傳統社會學中外在于人的、機械的印象,把行動和結構二重性視為社會結構和個體之間的中間范疇,將二者勾連起來。
然而,吉登斯將行動與結構視為一枚硬幣兩面的結構化理論,并沒有解決行動與結構之間的關系問題。雖然結構依賴于個體行動而存在,但是結構與個體行動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們是不同的實體,并且,結構能夠對個體行動產生限制。在社會實踐中,個體總是處在一定的規則和資源之中,它們為個體行動劃定了范圍。批判者甚至認為“人們不能創造社會。因為社會總是先于人們而存在,它是人類活動的必要條件。”“社會為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提供了手段、媒介、規則和資源,……那么社會是被安排的實踐活動和網狀似的工作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集合體,這種集合體絕不是個體的創造,相反他們的實踐活動總是被預先設定的,在這樣做時到處不過是再制和轉變。”[注]Roy 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mtempaorary Philosophy,Verso,1989,p.4.雖然這樣的觀點本身存在不足,但它強調是的結構是與個體行動相互區別的獨特事物。由于忽視了結構與行動之間的區別,吉登斯在解釋微觀個體行動時帶有片面性。在結構化理論中,吉登斯提出了關于個體行動的結構層次的觀點:第一是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以便行動者能夠了解自己在其中活動的物質及社會環境;第二是行動的合理化過程,這意味著發展出能使行動者有效處理其社會生活的常規來;第三是行動者的動機和動力,這涉及推動行動者去行動的種種愿望。[注]于海: 《西方社會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第390頁,第390-391頁。在此,吉登斯僅僅從行動個體自身去說明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忽視了結構對個體之間作用的影響。
(二)社會突現范式的改進之處
吉登斯理論中的不足正是索耶社會突現范式嘗試做出改進之處。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基于復雜系統理論,索耶采用分層本體論,將社會系統分為五個層級,每一層級都具有獨立性,并具有因果力,而社會的運作則是由這五個不能彼此化約、具有獨立性的層級辯證互動產生的。基于分層本體論,社會結構成為既依賴于個體又高于個體的層級。在索耶看來,個體行動與社會結構不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而是不同的實體,雖然社會結構依賴個體及其行動,但是社會結構是與個體行動相區別的獨特事物,“存在集體社會實在,它們具有關于它們自身解釋的獨立特征。一旦一種框架突現,它就會限制行動的可能性。盡管這一框架是由參與個體通過他們的集體行動建立的,但是那些個體在分析上具有獨立性,并且擁有存在于個人及其行動之上的因果力。”[注]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2005, pp.220-221.索耶對社會結構與個體關系的新理解即社會結構附生于個體,但又是不能化約為個體的較高層級的社會實在,這得益于心靈哲學突現論。這一理論用附生與多重可實現論證了大腦是意識產生的物質基礎,而意識是不同于大腦的存在這一事實。索耶將個體—社會的關系與大腦—意識的關系作類比,認為個體是社會系統中基礎的層級,而社會結構則是由個體及其相互作用產生的。在此,索耶承認方法論個人主義以個體作為社會系統分析最小單位的立場,但是,他也同時認為方法論個人主義是不全面的,因為它僅僅試圖通過分析參與個體的行動或心理狀態,分析這些個體的相互作用,依照“上向”的解釋來獲得對整個社會的理解而忽視了其他社會實在,如相互作用、短暫突現等對個體的限制作用。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社會系統既存在上向因果關系,也存在下向因果關系,且一旦個體之間進行相互作用,兩種因果關系就會同時產生,在時間上沒有先后之分。這就要求在對社會系統進行分析時既要考慮個體是社會結構形成的基礎,又要考慮社會系統各個層級對個體及其行動產生的影響。如此一來,由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集體主義在解釋社會時所造成的片面性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在以往的社會理論中,個體形成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對個體產生限制或是一蹴而就,或是用十分簡單的理論將二者勾連起來,而未能將社會突現過程呈現出來,因而,這些理論都未能清楚地解釋個體如何形成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又如何對個體及其相互作用產生影響。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個體與結構層級之間增加了相互作用、短暫突現、穩定突現三個層級,增加這些層級的目的在于強調探究潛藏在個體—社會關系形成過程背后的各種結構、機制。索耶認為,突現是存在于社會之中基本的、持續不斷的辯證法,個體一旦產生相互作用,就會創造并維持短暫突現和穩定突現,并且這些突現能夠產生作用于個體的下向因果關系。個體—社會結構之間增加的三個層級也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并非所有的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都能夠產生社會結構,例如一場小型的學術會議只不過是一次短暫突現;而在個體之上的各個層級,一旦產生,就會對個體產生直接影響。
關于相互作用、短暫突現與穩定突現對個體—社會結構之間關系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并非索耶獨創。它們是索耶在對其他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受到啟發,將其糅合在一起的結果,并最終形成了社會突現范式,因此,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綜合范式。
對于個體與其他社會實在之間的關系,索耶用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調解。而對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關注,索耶顯然是受到了相互作用范式[注]索耶認為,所謂結構范式是僅僅關注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范式。它主要有三種理論形態:結構決定論,即認為社會結構決定個人,其代表是法國結構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即個人決定社會,其代表是古典微觀經濟學;結構決定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混合,其代表是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而所謂相互作用范式則是在結構范式的個人—社會關系之間加入了相互作用這一范疇,并把相互作用當作一個獨立的事實分析。相互作用范式的典型代表是齊美爾、芝加哥學派、哈貝馬斯等。的影響。相互作用范式在個體—社會結構之間加入了相互作用,并認為相互作用這一層級的性質不是由個體行動或社會結構衍生出來的,它是獨立的層級。把相互作用當成存在于個體—社會之間的獨立層級,這就意味著它同時能對個體與社會結構產生影響,且它是個體—社會之間關系的媒介。哈貝馬斯是相互作用范式的代表之一。在他的交往行為理論中,語言是溝通的媒介。哈貝馬斯所關注的語言不是指一般的語言能力,而是語言的交往能力:語言不僅能傳遞信息,還能用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他認為言語行為作為溝通的媒介,有以下三個作用:(1)建立和更新人際關系,在此過程中,言語者關懷的是生活世界的正當秩序;(2)呈現或設定狀態和事件,在此過程中,言語者關注的是客觀世界的存在事實;(3)表達經驗,表現自我,在此過程中,言語者關切的是他主觀世界中所持有的東西。[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3頁。哈貝馬斯試圖通過解釋語言溝通過程把個體與社會結構聯系起來。然而,這一理論同樣沒有關注到社會突現的過程。雖然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的前提與背景是生活世界,但在解釋生活世界如何形成時,他的觀點是:“在交往行動中,生活世界以一種直接的確定性包圍我們……交往行動之背景的這種既滲透一切又隱匿不明的呈現,可以被描述為一種高強度但同時不完善的知識和能力……我們對這種知識作不由自主的運用,而并未反思地知道我們確實擁有它。”[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家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7頁。在此,交往的前提和背景與個體行動脫離了,成為一種自在的存在。哈貝馬斯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生活世界可以等同于文化世界,而文化的產生正是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產生的社會突現的結果。在索耶看來,哈貝馬斯只是指出了個體行動的聯系,而沒有解釋這些聯系如何產生,以及個體行動的聯系如何導致宏觀結構的出現。因此,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相互作用以及包含文化的穩定突現、短暫突現被置于社會整體之中,它們與個體的關系不是相互分離的,而是附生于個體之上,并對個體產生下向因果關系。同時,索耶也指出,由于相互作用處于社會整體中的獨立層級,因此,相互作用本身也受到來自較高層級的下向因果力,并且這一過程并不需要個體參與。有關相互作用與穩定突現、短暫突現的關系已經由語言學家研究,“語言人類學家與社會語言學家已經證明了各種環境,在這些環境下,相互作用的部分直接受環境的限制,甚至在這些環境是由參與者們的談判而出現,它受到的因果作用也與任何參與個體都不同——因為因果作用直接作用于相互作用的過程,這樣的例子包括對禮貌以及禮節、問候的禮儀以及玩笑的方式等等。”[注]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2005, pp.218-219.
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將社會的模式轉變為各個層級之間的辯證互動,對社會的理解由突出個體或社會結構的優先性轉變為對社會系統各個層級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這樣的社會模式包含著索耶反對經濟學中將方法論個人主義作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的觀念。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實際上制定了社會科學通用的語法”,相信經濟學分析是解釋人類全部行為的統一方法,從而以霸權的姿態君臨其他學科。[注]杰克·赫什弗利:《擴張中的經濟學領域》,《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4輯,第181頁。這種經濟學方法以所謂的“理性經濟人”為基礎,其基本思想是:(1)從自己的偏好出發來追求自身利益是個體活動的根本動機;(2)個人行為動機或偏好是外生的、既定的,即無一例外地追求物質利益(效用)的最大化;(3)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是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個體理性行為的自然結果。[注]沈湘平:《馬克思對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超越》,《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這樣的經濟學方法論個人主義存在著諸多困境,例如,如果要對多個個體理性的形成問題進行追問,就不得不進入實踐的分析,也就是進入社會系統。并且,在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包含著這樣一種假設:個體之間的經濟行為是持續的,經濟行為最終形成社會結構。然而,在社會實踐中,個體之間的經濟行為并非連續不斷。在索耶的社會突現范式中,經濟學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地位被完全顛覆。經濟學方法論所強調的個體理性經濟行為不過是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形式,并且,個體只有參與到相互作用中才會產生突現,單獨的個體并不屬于社會突現范疇。而經濟制度也僅僅是社會突現的某一具體結果,應當屬于層級E即社會結構的范疇,經濟學研究不過是建立在社會突現上的對某一具體結果的研究。因此,在索耶看來,把經濟學的方法論作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是錯誤的,而真正為所有社會科學提供基礎的應當是社會突現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