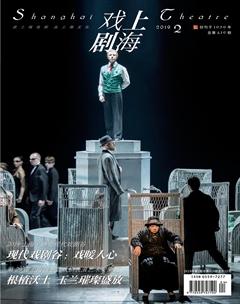中國青年戲劇導(dǎo)演說
曉溪
2019現(xiàn)代戲劇谷中有許多國際大導(dǎo)的名字,但請大家在關(guān)注大導(dǎo)的同時,將目光也投向中國青年戲劇導(dǎo)演,這些當(dāng)今中國劇壇的新銳勢力值得關(guān)注,因為他們的作品或許會給你驚喜和更多的文化共鳴。現(xiàn)代戲劇谷致力于扶持青年戲劇導(dǎo)演,此次邀請了三位中國新銳戲劇導(dǎo)演,帶來他們的最新作品。他們會給中國戲劇帶來怎樣的新鮮能量呢?本刊采訪到了丁一滕、黃俊達(dá),且聽中國新生代青年導(dǎo)演如何回答——
請介紹一下今年亮相現(xiàn)代戲劇谷的作品。
丁一滕:今年我?guī)У氖俏易钚聦?dǎo)演作品《弗蘭肯斯坦的冰與火》,這也是一部與現(xiàn)代戲劇谷聯(lián)合制作的劇目。我在這部劇中啟用了“啟”國際劇團(tuán)的來自法國、波蘭、希臘等國的有舞臺魅力的青年演員。我希望通過這樣一部中外青年戲劇人合作的作品,打破戲劇的文化界限,使人類共通的命運與情感的話題在劇場中得到當(dāng)代的解讀。這部作品是關(guān)乎青春、傷痕與關(guān)懷的,深入探討了人性的復(fù)雜與多面。
黃俊達(dá):每次閱讀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都令我感到生命的無奈,人們?yōu)樯疃疾ǎ詈笾皇窃谏妫畹貌幌褚粋€人。魯迅先生在喚醒,也在吶喊,只求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生命的真諦。這種胸襟和情懷,使我感動。那么我們現(xiàn)在有責(zé)任去延續(xù)這種精神嗎?正因為這一點,我重新開始了探索“狂人”與當(dāng)代社會的關(guān)系,在這個時代,人們還需要追求什么,是物質(zhì)還是靈魂?人的價值又是什么?
在創(chuàng)作中,你是如何看待經(jīng)典又是如何改編經(jīng)典的?
丁一滕:改編經(jīng)典不要囿于平凡地再現(xiàn),要敢于“誤讀”,要使經(jīng)典的血液與當(dāng)代創(chuàng)作者的血液相融,創(chuàng)造出猶如瑪麗·雪萊筆下弗蘭肯斯坦一般的怪物,具有全新活力的“新生命”。
黃俊達(dá):這次創(chuàng)作,對于我來說也是一個新嘗試。我邀請了跟我同樣留學(xué)法國的王婧,以戲劇構(gòu)作的身份加入到創(chuàng)作團(tuán)隊,共同合作。在創(chuàng)作期間,她增添了一種新動力,從敘事的角度讓我更深入地了解故事,了解劇中角色之間的沖突。另外,全劇以外文演繹,看似熟悉又陌生,增添了距離感,令整個故事更有世界性。
你是如何與戲劇結(jié)緣的呢?
丁一滕:我高中同學(xué)的母親是中戲的老師,偶然一次機(jī)會,他帶我去看了中戲表演系的匯報演出,我記得當(dāng)時觀眾席特別暗,舞臺上的演員拼盡全力,但似乎永遠(yuǎn)都不會疲勞。
黃俊達(dá):我第一次正式踏上舞臺,應(yīng)該是因為在課堂上說話比較多,被老師選出來,參加班際戲劇比賽,那時是演繹一個鞋店老板。到中學(xué)階段,我被同學(xué)推薦,加入了戲劇學(xué)會,認(rèn)識了我的戲劇啟蒙老師。他向我介紹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戲劇風(fēng)格,也建議我多從身體表達(dá)方面學(xué)習(xí),大概十四歲,我就開始參加校外有關(guān)形體和啞劇的課程,記得那時候,我最期待的就是下課坐長途車,由香港的新界出發(fā)到港島區(qū)學(xué)習(xí)和排練,每天如是,斷斷續(xù)續(xù)維持了三年多,也許是因為這樣,我喜愛身體鍛煉和創(chuàng)作為主導(dǎo)的表演形式。當(dāng)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戲劇帶給你什么?
丁一滕:不得不說,戲劇在更多的時候帶給我的是一種“痛苦”,它將殘酷的感受與回憶從我的潛意識中偷出來,在創(chuàng)作中發(fā)酵,幻化成一個個畫面、一個個音符、一聲聲嘆息。然后,舞臺上的一切歸于精神,最終消失。
黃俊達(dá):戲劇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論是創(chuàng)作、演出,還是生活。沒有溝通,就沒有交流,沒有交流,就沒有溝通。特別在當(dāng)今社會,很多時候沖突都是缺乏溝通導(dǎo)致的。有時溝通并不是為了找尋一個特定的答案,因為每個人的答案是很個人的,若堅持己見,就會變得自私、自大,所以重點還是溝通。
當(dāng)我們追求生活質(zhì)量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心靈上的生活質(zhì)量,劇場這個空間,是一個可以讓所有人回憶、反思和討論的地方,有了這個空間,人或許能夠活得更單純、更自在。
做戲劇,你快樂嗎?
丁一滕:做戲的過程往往是一個迷失的捫心自問的旅途,會迷茫,會驚喜,會感概,這都是戲劇的一部分。
黃俊達(dá):我很少用“做”這個字,我都保持“玩”這個字,“玩”應(yīng)該比“做”快樂。玩的過程非常快樂,過程包括對于主題的前期研究和探索工作,然后整理探索和研究中所得到的元素,將其安排次序并與主題結(jié)合。這段時間,我們都需要經(jīng)歷痛苦、勞累和迷惘,因為這是創(chuàng)作必經(jīng)的過程,那種快樂是難以形容的,因為它是基于看似負(fù)面的情感堆砌而成的。大概我已經(jīng)習(xí)慣和享受這種矛盾的快樂了。
在你看來,戲劇創(chuàng)作,是為他人,還是為自己?
丁一滕:我覺得命運本不分你我,人性也并無本質(zhì)上的差異。我的戲,例如《弗蘭肯斯坦的冰與火》,是為了關(guān)懷我自己,也是為了關(guān)愛眾生,世上那些殘缺的生命,都應(yīng)該被保護(hù)。
黃俊達(dá):三十歲前的我,大多數(shù)的創(chuàng)作都是以自己出發(fā),我覺得怎樣,我想怎樣。現(xiàn)在我習(xí)慣不停自我告誡,為他人更為重要,放下自己才能更宏觀、更自在地談生命、談生活,我還在學(xué)習(xí)保持謙遜。
戲劇,帶給我們什么?
丁一滕:戲劇是當(dāng)下,所以戲劇教會我們“珍惜”,珍視現(xiàn)在這些珍貴的情感與機(jī)遇,真誠地體味劇場中的呼吸與脈搏,以及從演員血肉中散發(fā)出的溫度與能量。
黃俊達(dá):用一小時,看一次人生的歷程,用一輩子去學(xué)習(xí)。
作為導(dǎo)演,如何保持創(chuàng)作的活力?
丁一滕:我認(rèn)為戲劇創(chuàng)作是生命,生命便有生老病死,旺盛時綻放,枯萎時凋零,這是生命的規(guī)律,也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但每一個階段都是美麗的。
黃俊達(dá):多看跟戲劇無關(guān)的事和物,仔細(xì)看和感受它們。
2019現(xiàn)代戲劇谷的主題是“戲劇溫暖城市”,你如何解讀?
丁一滕:藝術(shù)的發(fā)展能使一個城市充滿活力與人文氣息,我希望劇場的熱度蔓延到城市生活的每個角落。
黃俊達(dá):心靈的富足是要靠藝術(shù)作品來滋潤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和種類增多,證明該城市經(jīng)濟(jì)正在起飛。這時候戲劇就能填補(bǔ)物質(zhì)以外的心靈追求,讓我們反思生活。
你認(rèn)為,進(jìn)劇場,去看什么?
丁一滕:我認(rèn)為進(jìn)劇場就是看那些經(jīng)典中的生命如何與現(xiàn)實中的人們對話,在充滿假定性的空間中,觀眾選擇,并對自己的選擇負(fù)責(zé),觀眾收獲,并從收獲當(dāng)中體悟自己的人生。
黃俊達(dá):我們應(yīng)該保持開放態(tài)度去觀賞,不只求看懂,還要去感受,劇場是一個可以讓觀者把他們的想象放進(jìn)去的地方,是互動和溝通的地方。
你覺得劇場是一個特定場域嗎?
丁一滕: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劇透,《弗蘭肯斯坦的冰與火》這部戲,就不止發(fā)生在劇場。
黃俊達(dá):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劇場,只需要有一個空間,有演員和觀眾存在,并且有意圖去表達(dá)或表現(xiàn)一些東西。
近年來流行“跨界”,在你看來,是戲劇在向其他藝術(shù)跨界,還是其他藝術(shù)在跨界戲劇?戲劇的邊界和范疇是什么?
丁一滕:各個藝術(shù)門類的跨界與交叉是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我認(rèn)為并不存在誰主誰次,各種藝術(shù)之間本就存在相通之處,流動與互文可以使藝術(shù)得到升華。戲劇自誕生之日起,便是在這種相互滋養(yǎng)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在我看來戲劇并沒有邊界與范疇,青年戲劇創(chuàng)作是創(chuàng)造與想象的代名詞,應(yīng)當(dāng)大膽借鑒與突破。
黃俊達(dá):對我而言沒有什么誰跨界誰之分,重點在于說故事,怎樣去說讓人類感受和反思的故事,跨界某種程度上是說故事的手段。
在你看來,戲劇如何與社會、與人的生活產(chǎn)生聯(lián)系?
丁一滕:戲劇不僅僅是少數(shù)人的戲劇,它應(yīng)該更多地走向大眾。例如現(xiàn)代戲劇谷的許多戶外演出,便扎根在靜安的居民社區(qū),讓他們有機(jī)會接觸與感受這個之前看似遙遠(yuǎn)的“小眾藝術(shù)”。
黃俊達(dá):戲劇讓我們重新審視生活,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挖掘生活中觀察到的細(xì)節(jié),從而將每一個細(xì)節(jié)放大和雕琢,讓生活或社會某種現(xiàn)象得以被刻畫,觀者在觀賞的過程中也許有所領(lǐng)悟和收獲。
你如何看中國戲劇現(xiàn)狀,對此你有怎樣的思考和探索?
丁一滕:我更關(guān)注未來。記得在歐丁劇團(tuán)排戲時戲劇大師巴爾巴總是用“未來的戲劇在中國”這樣的話來鞭策我奮發(fā)努力,我在潛移默化中帶著他給我的種種啟示開始了自己的戲劇探索。在異國的思鄉(xiāng)之情促使我翻閱了許多以前都未曾認(rèn)真讀過的中國名著與經(jīng)典,我漸漸萌發(fā)了將中西戲劇觀念與方法融合從而豐富舞臺創(chuàng)作實踐的想法,“新程式”導(dǎo)演與表演方法的提出以及在波蘭創(chuàng)建“啟”國際劇團(tuán)就是對這一理念的嘗試與探尋。
黃俊達(dá):中國的戲劇在短短的十年間迅速發(fā)展,大家對肢體劇或是以身體為主體的劇場訓(xùn)練不再陌生。這些變化對于藝術(shù)作品及表現(xiàn)者的提升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期待下一個十年,期待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的劇場有更多對話,同時邁向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