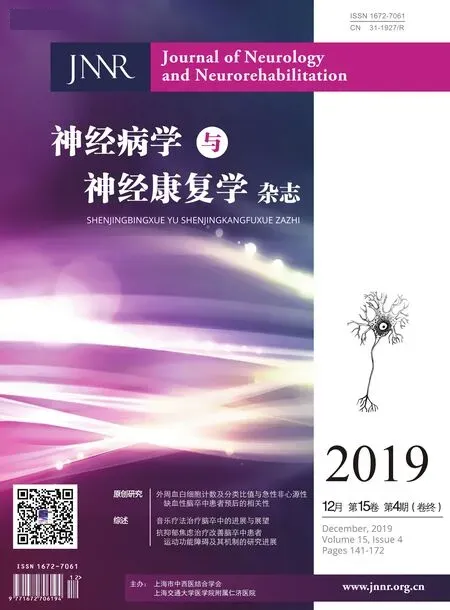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及分類比值與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相關性
承德醫學院附屬醫院神經內科,河北 承德 067000
腦卒中是全球最常見的致死和致殘病因之一[1-2],腦動脈粥樣硬化是其危險因素之一。國內外研究發現,超敏C 反應蛋白、白細胞介素15、腫瘤壞死因子α、基質金屬蛋白酶9 和基質金屬蛋白酶2能夠加快腦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速度以及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破裂速度,而炎癥反應也貫穿于腦卒中的整個病理生理過程中[3]。研究顯示,抗炎治療可以起到穩定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作用[4-8]。然而,由于上述炎癥因子檢測的費用較高,因此臨床可行性較低。
外周血白細胞也是一種血管特異性炎癥因子,通過損傷血管內皮細胞,在動脈粥樣硬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9]。既往研究已發現,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和淋巴細胞與單核細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與急性心肌梗死和惡性腫瘤的預后相關[10-12]。由于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的檢測簡便易行且費用低廉,因此臨床應用前景廣泛。然而,目前少見有關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與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相關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與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相關性,以期為腦梗死的防治提供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1)2017 年6 月1 日—2018 年6 月1 日在承德醫學院附屬醫院神經內科接受住院治療的初發和(或)復發的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2)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8》診斷標準;(3)計算機斷層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發現責任病灶。
排除標準:(1)有明確的惡性腫瘤史、自身免疫性疾病史以及嚴重的肝腎疾病史;(2)住院前1 周內患有明確的感染性疾病,以及在住院期間發生感染;(3)在本次發病前,已存在因病無法生活自理的情況。
1.2 研究對象
2017 年6 月1 日—2018 年6 月1 日在承德醫學院附屬醫院神經內科接受住院治療的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中,323 例符合病例選擇標準。
1.3 研究方法
1.3.1 臨床病歷資料收集
從臨床電子病歷中收集患者的人口統計學及臨床資料,包括血管相關危險因素(性別、年齡、高血壓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腦卒中史、吸煙史、飲酒史等)、相關藥物(抗血小板聚集藥物、他汀類藥物、降壓藥等)使用史、實驗室檢測指標(血常規、血糖、血脂、尿酸、超敏C 反應蛋白、同型半胱氨酸等)、入院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評分、出院時改良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評分以及住院時間等。
1.3.2 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323 例患者均在住院后24 h 內完成血常規檢測。檢測指標包括外周血白細胞計數以及外周血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和單核細胞計數,并計算NLR 和LMR。
1.3.3 預后分組
出院當日由2 位主治醫師級別以上的資深醫師按照MRS 對患者進行評分和預后分組[13],其中MRS 評分≤2 的患者被納入預后良好組(213例),MRS 評分為3~6 的患者被納入預后不良組(110 例)。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R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表示。對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預后進行單因素分析,如果是連續正態分布資料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態分布資料采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分析。按照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分為4 組:≤10.0×109/L、(10.1~11.0)×109/L、(11.1~12.0)×109/L、≥12.1×109/L ;按照NLR 分為3 組:<3.6、3.6~6.5、>6.5;按照LMR 分為3 組:<2.97、2.97~4.83、>4.83)[14-16]。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評價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對預后的預測能力,計算敏感度和特異度,確定最佳截斷值。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
預后良好組213 例患者中有3 例缺失血常規資料,預后不良組110 例患者中有1 例缺失血常規資料。預后良好組與預后不良組人口統計學及臨床資料的比較結果見表1。
2 組的年齡、性別、高血壓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吸煙史、飲酒史、抗血小板聚集藥物使用史、他汀類藥物使用史、降壓藥使用史、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以及血糖、總膽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尿酸水平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 組的腦卒中史、外周血中性粒細胞計數、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NLR、LMR、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基線NHISS 評分以及住院時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見,預后不良組的中性粒細胞計數、NLR、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基線NHISS 評分均顯著高于預后良好組,住院時間也顯著延長,而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和LMR 顯著低于預后良好組。
2.2 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年齡、性別、外周血中性粒細胞計數、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住院時間與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無顯著相關性(P>0.05)。

表1 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

表2 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
外周血白細胞計數(比值比為1.788,95%置信區間為1.119~2.854,P=0.015)、NLR(比值比為1.275,95%置信區間為1.031~1.576,P=0.025)、LMR(<2.97vs2.97~4.83:比值比為0.277,95%置信區間為0.072~0.814,P=0.013)、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比值比為2.389,95%置信區間為1.194~4.799,P=0.014)和基線NHISS 評分(比值比為12.630,95%置信區間為6.115~27.741,P<0.001)是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
2.3 ROC 曲線評價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對預后的預測能力
應用ROC 曲線評價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和LMR 對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預測能力,結果見圖1。
2.3.1 外周血白細胞計數
ROC 曲線下面積為0.545(95%置信區間為0.481~0.609,P<0.05),最佳截斷值為7.22,敏感度為45.1%,特異度為66.0%。
2.3.2 NLR
ROC 曲線下面積為0.597(95% 置信區間為0.537~0.658,P<0.05),最佳截斷值為2.57,敏感度為56.4%,特異度為58.3%。

圖1 ROC 曲線評價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對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預測能力。曲線:深灰色實線代表NLR;黑色短虛線代表外周血白細胞計數;黑色長虛線代表LMR。
2.3.3 LMR
ROC 曲線下面積為0.575(95%置信區間為0.514~0.636,P<0.05),最佳截斷值為3.65,敏感度為51.9%,特異度為52.1%。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LMR、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和基線NIHSS 評分是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MRS 評分)的獨立危險因素。既往研究也發現,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與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不良預后存在相關性。ELKIND 等[14]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納入2 808 例急性腦梗死患者,經校正混雜因素后,白細胞的第2、3 和4 分位組與第1 分位組相比,發生不良結局的比值比(95%置信區間)分別為2.098(0.96~4.58)、4.79(2.24~10.22)和5.59(3.14~9.98);隨著入院后24 h 內外周血白細胞計數的增加,發生不良結局的風險也相應增加(趨勢P<0.05)。有研究發現,NLR 與腦梗死的發生以及疾病的嚴重程度和預后相關[15-16]。REN 等[17]的研究納入512 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經校正多項混雜因素后,顯示LMR 是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獨立保護因素。
迄今為止,尚無法闡明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和LMR 影響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發生和發展以及預后的機制。目前推測可能與以下機制有關。在急性腦梗死發生的早期,由于腦組織水腫等原因使白細胞變形能力明顯下降,引起腦血管微循環障礙,導致側支循環建立受限,并且白細胞沾附于血管內皮細胞表面形成小栓子而阻塞微血管,導致微循環障礙,降低腦血流量[18-19];同時,粘附于血管內皮細胞表面的白細胞與浸潤于腦組織內的白細胞互相激活,產生和釋放氧自由基以及血管活性因子如白三烯和血小板激活因子等,引起血管內皮細胞損傷,誘導血小板聚集,引發血管收縮,導致神經元缺血和缺氧加重甚至死亡,進一步破壞血腦屏障,從而加重腦水腫,導致更為嚴重的腦損傷[20-22]。中性粒細胞是參與腦卒中后早期反應的主要白細胞亞型,能夠引發強烈的炎癥反應[23-25]。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作為炎癥反應的2 個主要參與者,被認為加劇了腦卒中后繼發性腦損傷。根據免疫反應過程的不同,將淋巴細胞分為B 淋巴細胞和T 淋巴細胞。一般認為,腦卒中發生后,T 淋巴細胞發揮激發炎癥反應的作用,分泌的促炎細胞因子包括干擾素γ、腫瘤壞死因子β、白細胞介素4、白細胞介素5、白細胞介素10 和白細胞介素13 等[26]。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下降可以導致免疫抑制[27]。單核細胞是另一種能夠驅動缺血后炎癥反應的重要免疫調節因子,其浸潤于腦梗死區可加重腦損傷。CD14+CD16-單核細胞作為經典單核細胞,主要分泌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 和白細胞介素1β,發揮促炎作用,加重腦卒中后腦損傷[28]。
既往研究已證實,超敏C 反應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是腦血管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并且已在臨床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本研究也證實,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是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這與史帝[29]的研究結果一致。
YAGHI 等[30]的研究發現,NIHSS 評分增加是腦卒中患者腦梗死體積增加的重要危險因素,腦梗死體積越大,預后越差。本研究也證實,基線NHISS 評分是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由此可見,NHISS 評分能夠直觀地反映腦卒中的嚴重程度,NHISS 評分越高,代表神經功能損傷越嚴重,預后也越差。
為了比較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對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本研究采用ROC 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結果顯示在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的曲線下面積中,NLR 的曲線下面積最大,外周血白細胞計數的曲線下面積最小。盡管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與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顯著相關,但鑒于曲線下面積均小于0.7,因此均不是理想的預測指標,而聯合檢測可能對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預后具有更高的預測價值。
此外,腦卒中是一種具有高發病率、高致殘率和高死亡率的疾病。本研究結果顯示,既往有腦卒中史患者的不良預后發生率顯著高于初發腦卒中患者,這一結果與HEUSCHMANN 等[31]的研究結果一致。
綜上所述,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LMR、超敏C 反應蛋白水平和基線NIHSS 評分是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預后(MRS評分)的獨立危險因素。鑒于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 和LMR 的檢測簡便易行且費用低廉,因此適合臨床推廣應用。今后有待開展更大樣本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進一步驗證上述研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