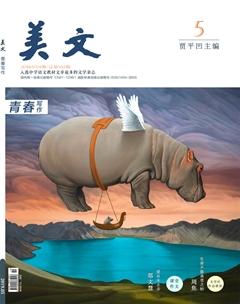凈云
云使
凈云(Den Ven)是一位尼姑,俗名黃梅,來自越南的胡志明市。
或許是一種緣分吧,她的僧名與俗名,都恰好應和了我的名和姓。
注意到她,是在Mess(飯廳)里。那天,她正坐在我的對面,分外潔凈的臉,眉清目秀,隔著長長的餐桌,吸引了我的目光。跳出的第一個念頭便是:這么漂亮的女子,怎么就出家為尼了呢?
從此,格外關注她的身影。
她不愛說話,見人微微一笑,常常一人在Mess里進餐,并不與他人交談。那種沉靜素雅的美,襯托在深色的法衣里,給人一種說不出的超凡脫俗的感覺,有時遠遠望去,在暮靄的暗影中就如同一幅倫勃朗的油畫。
我們雖然都在德里大學,卻不是一個系;住同一棟女生宿舍,卻鮮有來往。相遇,總是在吃飯的時候。
一天,又是在晚飯時分,我們在Mess 里碰面了。
她恰好坐在我旁邊的座位上,靜默中,忽然開口問:“您從中國來?”
“是的。”我答道。
“我想請教幾個關于漢語的問題,可以在飯后見到您嗎?”
“當然可以。”
過后,又是靜默。
我暗暗驚訝這位年輕尼姑英語的純正。
一小時后,凈云敲響了我的房門。看到墻上貼的和桌上擺的我丈夫和女兒的照片,她忽然變得活躍起來,開始問長問短。我索性搬出幾本在印度旅行的相冊給她看,她看得很仔細,有時,甚至會開上一兩個讓我吃驚的玩笑。有一張孟買海濱的照片,是我在礁石間跳躍、不慎墜海受傷后被男同胞抱著上車時照的,她調皮地問:“你打算給你丈夫看嗎?”“當然!”“他會說些什么呢?”她的眼中閃過一絲淘氣的神色。
我不由想起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在晚飯后,我與同室舍友在樓前小道上散步,小道的另一頭,通向女生宿舍的大門。當我們走近大門口時,看見有兩個年輕的和尚等候在鐵門外,在他們身后,停著一輛“大使”牌出租車,黃黑兩色,是印度90年代最常見也是最好的出租車。只見一個小尼姑匆匆跑過去,門里門外,僧尼間急切地商量著什么。很快,小尼姑又飛快地跑回宿舍,當我們再次踱到門口時,她已滿臉帶笑地拿著Special permission(晚間外出“許可證”)交給看門人,然后,與另一位女尼一起跨出了這道晚8點后不得外出的大門。
轟鳴聲中,“大使”絕塵而去……
這一幕,印象深刻。心想,檻里檻外,角色轉換這么方便啊!
莫非那天的小尼就是凈云?依稀也是一副可人的模樣。
看罷照片,凈云拿出一張紙條,問我能不能給上面的漢字注上拼音?
接過來一看,暗暗吃了一驚。
紙條上寫著三行字:
沒有誰能阻止離別
請忘記我吧
勇敢忠恕之士
字寫得稚拙,但看得出,每一筆都很用力,是非常認真地、一筆一劃地寫出來的。字里行間似有一股淡淡的憂傷,我的好奇心被點燃,卻礙于出家人的忌諱,終于什么也沒問。
再后來,每次見面都彼此點點頭。她總是嫣然一笑,風輕云淡。
學習之余,旅行是我最快意的事了。在印度這個神奇的國度,有著太多令人驚嘆不已的古代遺跡和宗教圣地,每當我曬得烏黑地回到“Hostle”——我的“佛國精舍”(女生公寓),總少不了各種各樣的目光與詢問。凈云說,她的學習快結束了,如果可能,想和我一起去佛教圣地走走。不久后,我真的去了鹿野苑、靈鷲山、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和藍毗尼,卻沒有告知她——同行的都是中國人,有男有女。朋友們說,出家人,窮游中多有不便,于是作罷。
東游歸來,我琢磨著怎樣跟凈云解釋。不想一見面,她卻歡喜地說:“我要給你看個東西!”她打開衣柜,取出一個大文件袋,小心翼翼地從里面抽出一張證書。
哇!你拿到博士學位了,祝賀你!
我興奮地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
看著眼前的凈云,我生出想更深了解她的念頭。
“哎,博士,回越南后你打算干什么呢?難道一輩子待在廟里?”我半調侃半試探地問。
“當然,我已獻身佛門。我會在寺中度過一生,不會還俗的,再說,大乘佛教也不主張還俗。我可能會在寺里做一名老師,傳授佛學。”
我不禁好奇:“當初出家,是父母的心愿,還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的選擇。”
“什么時候?”
“中學畢業后。其實,我讀中學時就想出家了。你知道嗎,每當我親近廟宇時,總會有一種心境澄明的感覺,就是我們出家人說的,有大歡喜。父母不愿意我出家。我哥哥在美國讀書、工作,還給我帶來了一個美國嫂子。他們希望我走哥哥的路,我說,我當然要繼續學習,但不是去美國,而是去印度學習佛法。”
“你英語這么好,在哪兒學的?”
“我自己國家。我讀了兩個學位,一個英語,一個佛學。”
“然后呢?”
“然后,我就來印度了呀。”她開心地笑起來,“在這里讀M.A.和Ph.D.,現在拿到學位了,下個月就打算回越南了。”
看著滿臉笑容的凈云,我一時不知再說什么好。
當年,她發下怎樣的大愿,來到這“熱與塵”的國度,在清苦孤寂的學習中,度過自己最美的年華。一個女尼,在這所幾萬學子的大學里,如此出色地完成學業,拿到宗教學博士學位,將來又會成為一個怎樣的高僧大德呢?
凈云也搬出了她的影集,里面有許多有意思的照片:有她論文答辯時的留影,那份掩飾不住的自信與聰慧,給我極深的印象。一張海邊的照片,卻又讓我驚嘆她的美麗:照片上的她,側身斜坐在礁石上,尼衫的前襟在腰部不經意地打了個結,頭上裹著的素色頭巾松松地在脖子后面挽起,那模樣,簡直像極了一個都市味十足的現代女郎!我想討得這張照片,凈云卻一再搖頭,那表情似乎在說:“這張不好,不像出家人。”還有一張照片,是她與本寺高僧的合影,老人已有九十多歲,須眉皆白,秀骨清相,很莊重地坐在一張高椅上,凈云可人地倚立一旁。我問:“寺里有幾人出國學習?”凈云答:“僅我一人。”是啊,如此冰雪聰明,機會不屬于她又能屬于誰呢?
臨別前,我們相約合影。
敲響凈云房門時,她正蹲在地上熨衣服,十分仔細的樣子。見我來了,她頭一歪,略顯調皮地問:“我穿什么好呢?”說著,抱出一摞干凈平整的衣服。我一眼望去,都是些納衣,款式相同,沒有什么區別。凈云卻一件一件地翻撿著給我看:“這是灰的,黃的,棕的,青的……”,我心中忽然掠過一絲難過。對我而言,這幾乎沒什么好挑的,不都是尼衫嗎?可她卻如此認真,在衣物色彩的揀選中,執拗地還原了女人愛美的天性。
我再次感嘆:可惜了,一個美麗的女人!但轉念一想,這想法若被她知道了,說不定也會嘆我“俗而無明”啊。是的,也許在家與出家的區別就在這里吧。我以俗世的眼光看她,悲憫她;而換了凈云的角度,感受肯定大異于我,或許她憐憫我都不一定呢。
“黃色的吧。”我說。
于是,她穿上如今收在相冊中的這件鵝黃色尼衫,配上一條棕色的褲子,與我一起去到女生公寓的門口。
沒有首飾,沒有秀發,沒有描眉涂唇,完全的素面天然。她微微地笑著,靜靜的,眼里有自然如處子般清純的目光,雙手扶在了門口的鐵柵上。
凈云的身影,襯著濃密的綠樹和地上斑駁的方磚,永遠定格在了我的記憶中。

西江千戶苗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