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長城》到《珠穆朗瑪?shù)捻印?/h1>
2019-05-09 03:54:41付如初
西部 2019年6期
付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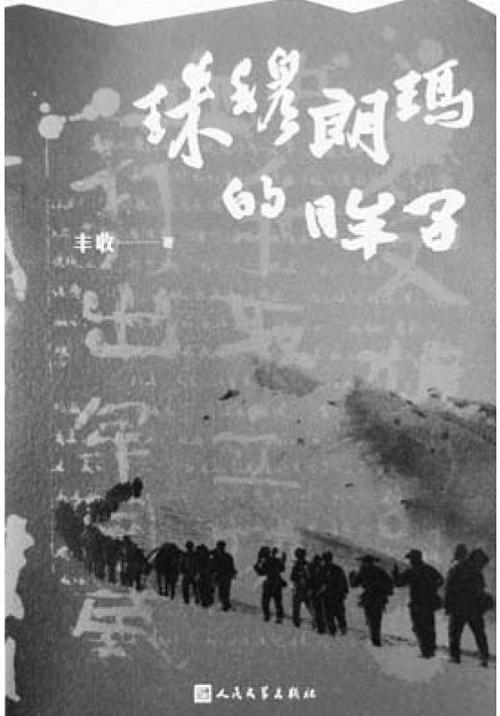
“非虛構(gòu)”的力量與困境
作為一種文體,“非虛構(gòu)”的邊界很寬泛,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歷史文學、口述實錄,甚至包括傳統(tǒng)媒體的特稿、深度調(diào)查報道等等,都可以劃到它的范疇里來。具體到中國文學,一度被稱為“時代輕騎兵”的報告文學是主流,后來隨著王樹增的戰(zhàn)爭系列和歷史系列,隨著《中國在梁莊》《我的阿勒泰》等一系列本土原創(chuàng)作品的走熱,以及以《尋路中國》為代表的引進版“非虛構(gòu)”作品的大受歡迎,報告文學的文體逐漸產(chǎn)生變化,使得“非虛構(gòu)”的概念逐漸生成并漸成主流。尤其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非虛構(gòu)”作家S.A.阿列克謝耶維奇,對這類文體的勃興更是一種提振的力量。
應該說,這是一種創(chuàng)作者充分尊重事實,將“個人”無限“隱藏”在事實和真實之后的文體;也是一種能夠直接記錄時代、直面真實、直面問題,對讀者的認識能夠直接產(chǎn)生作用的文體。如果一部作品,在事實的基礎(chǔ)上,講生動的故事,理性冷靜地看待人與事,并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人文精神,語言表述上清晰而不冗贅,真摯卻不濫情,就可以稱之為成功了。
然而,要獲得這種成功卻很難。因為無論是選材還是敘述角度,都必須在歷史語境和現(xiàn)實語境下。與虛構(gòu)相比,“非虛構(gòu)”寫作面臨的語境壓力似乎更為直接,也更為強勁。于是,“事實”變成了寫作者眼中的事實;“故事”變成了寫作者篩選、截取來的故事;而“理性和冷靜”,或者換句話說,寫作者的見識,也變成了“個人偏見”。至于“人文精神”,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是文藝作品的根基,都有魅力、都有力量,但同時,在發(fā)揮作用的時候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好在,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非虛構(gòu)”寫作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萎靡。社會現(xiàn)象越是復雜多變,知識傳播越是便捷快速,讀者對于理解世界和認識世界的需求越旺盛,作家對真實和客觀的敬畏也越強烈,俯身田野調(diào)查、埋頭真相發(fā)掘的責任感也越迫切。在這樣的作家隊伍中,新疆兵團作家豐收的身影是頗為引人矚目的。
從《中國西部大監(jiān)獄》到《西上天山的女人》,從《夢幻的白云》到《綠太陽》,從《鎮(zhèn)邊將軍張仲瀚》到《王震和我們》,從《鑄劍為犁》到《來自兵團內(nèi)部的報告》,尤其是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豐收堪稱采集新疆故事的第一人。他踏遍了新疆的每一片土地,觸摸了新疆的每一段歷史,交付了自己最旺盛的創(chuàng)作生命。他的采訪對象成百上千,積累的素材浩瀚駁雜。而新近出版的《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职涯抗饩劢褂谥杏∵吘匙孕l(wèi)反擊戰(zhàn),聚焦于那些曾在“世界屋脊”上為捍衛(wèi)國家領(lǐng)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奮戰(zhàn)的普通將士。
可以說,作為兵團二代,豐收一直在自覺地關(guān)注大歷史,關(guān)注大歷史中普通人的命運遭際。同時,他也一直矚目于今天的現(xiàn)實。且不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古至今,幾乎所有專注于歷史書寫的人,無不是在“現(xiàn)實問題不可解”的苦慮焦思中,力圖在歷史中尋求根源和路徑。同時,作為“非虛構(gòu)”作家,豐收在書寫過程中,嚴格保持了一個修史者的敬謹真誠,從未露才揚己;即便在現(xiàn)實語境的重重壓力之下,必須削句減辭,犧牲一些結(jié)構(gòu)布局的匠心,犧牲文學作品以情動人的感染力,他也從未在厚重豐沛的大歷史面前稍有怠慢,更沒有放棄自己作為兵團二代、作為一代中國作家的家國情懷。
兵團家史和西線豐碑
《西長城》序言中寫,解放戰(zhàn)爭打到1949年9月西寧解放的時候,以馬步芳為首的西北“五馬”殘部圖謀撤聚新疆,根據(jù)中共中央關(guān)于解放新疆的戰(zhàn)略布局,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命令第一兵團第二軍挺進南疆、第六軍挺進北疆。兩軍會師酒泉的第二天,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通電起義,第三天,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通電起義。1949年12月17日,解放軍駐疆部隊、三區(qū)民族軍、新疆起義部隊會師迪化,新疆軍區(qū)、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時宣告成立。之后,新疆開始剿匪平叛、建政維穩(wěn)、筑路引水、屯墾戍邊。
隨著局勢的平穩(wěn),中央決定駐新疆部隊除保留一個現(xiàn)役國防步兵師以外,絕大多數(shù)就地轉(zhuǎn)業(yè),“鑄劍為犁”,在新疆落戶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1954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正式成立,首任司令員正是率部起義的陶峙岳。之后,新疆兵團和新中國一起,經(jīng)歷了艱苦卓絕的一段歲月,全國人民熟知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十萬上海知青進新疆、“伊塔”事件之后的“三代”戍邊等都發(fā)生在這期間。
《珠穆朗瑪?shù)捻印分袑懀?962年10月,剛剛完成剿匪平叛不久的130師,返川歸建,突然接到軍委命令,中印邊境吃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即將開始,于是,各路人馬緊急從四面八方集結(jié),奔赴“世界屋脊”。新疆兵團立即向中央請命: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力支援邊防部隊作戰(zhàn)。于是,新疆邊防部隊組成了“新疆軍區(qū)康西瓦指揮部”,同時,西線六百多公里戰(zhàn)區(qū)的戰(zhàn)略物資供應任務落在了兵團汽車第一團,兵團獨立汽車第三營的肩上。盤山路貼山臨崖,冰雪覆蓋,幾乎每一次行軍和物資輸送都是在走“鬼門關(guān)”,就這樣,兵團一千一百二十五名精兵強將,為自衛(wèi)反擊戰(zhàn)輸送軍用物資六千五百噸,組成了名副其實的“生命線”。
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1975年新疆兵團被撤銷,改為新疆農(nóng)墾總局。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lián)合發(fā)出《關(guān)于恢復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的決定》。《決定》指出:“生產(chǎn)兵團屯墾戍邊,發(fā)展農(nóng)墾事業(yè),對于發(fā)展自治區(qū)各民族的經(jīng)濟、文化建設(shè),防御霸權(quán)主義侵略,保衛(wèi)祖國邊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82年6月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正式恢復,直至今天。如今的新疆兵團有14個師,174個農(nóng)牧團場,是“軍政企合一的特殊社會組織”,有37個少數(shù)民族。兵團的發(fā)展也開始從“屯墾戍邊”向“建城戍邊”轉(zhuǎn)變。
多年之后,豐收開始對這些歷史的當事人進行采訪,留下他們的回憶,感受他們歲月足跡中的崢嶸,同時,也為歷史保留驚心動魄和令人五味雜陳的真實瞬間。無論是《西長城》還是《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S收都致力于為歷史尋找更多的見證人。他尋找、探訪、傾聽、記錄,讓歷史在人身上復活,也讓人在回憶和見證中不斷樹立自己的價值和尊嚴。或許,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和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從來就不是問題的兩極,它們水乳交融,難分彼此。
《西長城》:“飄蕩在新疆大地的種子,哪一粒都有一部人生傳奇”
粗略說起來,《西長城》里的故事主角有幾類:一是部隊官兵,二是周總理說的“自動支邊人員”,三是天山湘女,四是上海知青,實際上他們也是兵團的主要人員構(gòu)成。他們的故事,就是一個國家從戰(zhàn)爭狀態(tài)走向和平歲月的全部反映——戰(zhàn)爭是歷史的極端狀態(tài),靠信仰、靠集體主義精神可以激發(fā)不可思議的潛能,正如《珠穆朗瑪?shù)捻印穼懙降哪菢印推綒q月,需要面對的是吃喝拉撒、婚喪嫁娶的日常生活,單純靠信仰、靠意志恐怕不能行之有效。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的初創(chuàng)時期,正是處于兩種狀態(tài)的過渡階段,信仰支撐下的集體主義精神仍舊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guān)懷也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于是四類故事主角之間就發(fā)生了很多或悲或喜的人生傳奇。
首先是部隊官兵。書里講到,王震的三五九旅進疆后變成了六師,進駐大芨芨草灘哈拉毛墩,一坎土曼下去,見不著土,糧食問題首當其沖:進疆部隊二十萬,國家解決不了軍糧的問題,除了自力更生,別無他法。王震說:駐守新疆,兵少了不夠用,兵多了養(yǎng)不起,解決這個難題就是走南泥灣的道路!于是,昔日的戰(zhàn)斗英雄變成了今日的種田能手。
書中講到老兵李洪清,曾在毛主席警衛(wèi)連當過連長,是被聶榮臻元帥贊賞的著名的一一五師的“蠻子”排長。他參加過五次反圍剿,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次,百團大戰(zhàn)、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后七次負傷,靠白求恩的無麻醉手術(shù)才保住了右腿,獲得“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解放獎章”,進疆之后他是巴里巴蓋草原的一名倉庫保管員。在中國最需要糧食的1961年前后,巴里巴蓋人給國家貢獻了上百萬斤糧食。1981年,李洪清和王震在石河子重逢,他對司令員說:“攻打蘭州時,你說,打不下蘭州我要你的頭,現(xiàn)在我的頭還在。”看著書中照片上,昔日的戎馬將軍和士兵相對露出忠貞赤誠的笑容,會讓人感嘆激情燃燒的歲月從未離他們而去,而這種信仰和意志在角色轉(zhuǎn)變過程中所發(fā)揮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如今看來,何其珍貴!
三五九旅唯一的知識分子團長、曾寫下兵團史詩《老兵歌》的新疆軍墾奠基人張仲瀚,用“十萬大軍出天山,且守邊關(guān)且屯田。塞上風光無限好,何須爭入玉門關(guān)”的豪邁詩句勉勵官兵,身體力行,親自拾糞種田。他一生都在倡導的南泥灣精神真正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官兵的血液。而這種精神背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是超出想象的苦難。《西長城》說:“十年、一百年,時間越久歷史越長才越明白,他們的犧牲太大太大,他們的給予太多太多。”1980年,經(jīng)歷了“文革”苦難、無兒無女的張仲瀚在北京病逝,1993年他的骨灰隨王震的骨灰重返天山。
新疆和田有一個四十七團的墓園,叫“三八線”,是以累死在田里的老兵周元開墾的長八百米、寬三百米的田地命名的,而此時,恰逢朝鮮戰(zhàn)爭期間。作家沈從文曾說:“一個士兵要不戰(zhàn)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xiāng)。”天山腳下,有太多如此遙望故鄉(xiāng)的老兵……
關(guān)于八千湘女,早已無需回避歷史的真實。在被命名為“家國 女人”的第三卷,書里寫明了來龍去脈。部隊的婚姻問題戰(zhàn)爭年代就已經(jīng)存在,扎根新疆,這個問題更是嚴峻:“沒有老婆安不下心,沒有兒子扎不下根”,于是,王震給自己的老搭檔、湖南省委領(lǐng)導王首道寫信求助:“……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歲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要她們來新疆紡紗織布,生兒育女……”沒幾天,長沙的報紙?zhí)焯煊刑柾猓盒陆妳^(qū)招聘團征召女兵!參軍去新疆上俄文學校,開拖拉機,進工廠……隨后湖南、山東、河南、四川、湖北、上海的女青年踴躍奔赴新疆……
太多的文學作品寫到了湘女的眼淚,寫到了時代對湘女的索求,豐收也并未回避這一點,但除了這些有代表性的故事,他還找到了其他,比如他寫到我黨早期,和劉少奇、何叔衡、謝覺哉齊名的革命家肖學泰的侄女肖業(yè)群,就因為在新疆找到了“根正苗紅”的婚姻而受到了保護,免遭“文革”中的政治牽連。組織包辦的婚姻在制造了很多悲劇的同時,也成就了很多喜劇,甚至護佑了很多人的命途。歷史從來就不單一和絕對。
除此之外,作者還找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入疆后女兵因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而發(fā)病的《癔病情況報告》,還有《部隊五年來婚姻問題總結(jié)報告》等等。作為報告文學作家,他有更為宏闊的歷史觀:西部的愛情和婚姻,也與所有地方的愛情和婚姻一樣,有悲劇也有喜劇,有感天動地的忠貞和生死不渝的誓言。而且,人生終究不能糾結(jié)和沉湎于苦難,“悲劇前奏、喜劇謝幕的人生長劇”更該被人記住,也更是以“真善美”為宏旨的文學作品應該具有的歷史品格和美學風范。
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點上,一代人的命運應該被記取,但無法被改變。那些美麗的進疆女子和背井離鄉(xiāng)的老兵一起,用青春譜寫了一曲西部悲歌,當然也譜寫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西部血色浪漫。
關(guān)于上海知青,問題顯然更復雜。它不是一時一地的問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全國性的,因而遺留的問題也是全國性的。與魚珊玲同為知青典型人物的楊永青出身書香門第,但她們都積極投身時代潮流,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yè)。作者說:“對于熱血青年,古往今來都是一樣,血親的力量在時代潮流面前蒼白無力。”只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血親也往往會成為她們命運轉(zhuǎn)折的理由。那時候的中國,“唯出身論”制造了多少歷史的悲劇!
楊永青說:“誰也超越不了時代。”如今看來,沒有進疆的老兵、湘女、“盲流”,就不會有新疆的今天,而沒有上海知青,兵團的教育也不會有后來的發(fā)展和改變。“時代導向他們的人生,他們也霧里看花云中望月地影響時代。歷史是一場風云際會,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會裹著你往前走。滄桑世事,潮汐人生,看世事還是看人生,他們都有了過來人的淡然恬靜。”
人生朝露,藝術(shù)千秋。當《西長城》揮筆寫下他們的故事的時候,他們的淡然恬靜早已化為一種鉛華盡洗的境界。而這種境界又反過來直接影響了《西長城》的風格,回顧故事的時候平實家常,甚至略顯絮煩,但評點人生的時候意氣平而旨趣深。這種點到即止、引而不發(fā)的風格,也影響到了《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膭?chuàng)作。當然,后者的題材更難處理,所以也更需要把握歷史和情感的分寸感。
《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p>
“戰(zhàn)爭,終究要由每一個戰(zhàn)士來完成”
與《西長城》的寫法不同,《珠穆朗瑪?shù)捻印芬驗檫x材敏感復雜,所涉歷史對普通讀者來說相對陌生,于是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篇幅,盡可能梳理清楚這場戰(zhàn)爭的來龍去脈。包括中印邊界紛爭的歷史由來、歷史演變,這又涉及到西藏、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歷史,也涉及到英屬印度期間英國在喜馬拉雅一帶的諸多政策和活動;同時,西藏在新中國解放前后的復雜局勢,平叛的艱難,以及中國軍隊在解放西藏前后所做的各種準備等等,也都需要逐一厘清。
對作家而言,歷史既是基于客觀現(xiàn)實的觀察,也是一種敘事,但敘事邏輯的建立總是受制于現(xiàn)實語境的影響,《珠穆朗瑪?shù)捻印凤@然無法超越這樣的影響。于是,豐收只能以“人”為核心,講述普通官兵的戰(zhàn)斗準備,寫戰(zhàn)斗過程中的主要戰(zhàn)役,寫勇敢、寫犧牲、寫骨肉分離、寫幸存者的回憶……借助這些,豐收力圖把歷史的幕布掀開一角,讓有心的讀者窺其一斑,思其可能。
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部分,在人類戰(zhàn)爭史上也具有別樣的意義。以在瓦弄大捷中建功立勛的54軍130師官兵為代表的我軍將士,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敵人,還有大自然。如果說,靠信仰、靠集體主義精神,將士們面對敵人的時候能夠做到視死如歸的話,面對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環(huán)境的肆虐,面對隨時可能粉身碎骨的懸崖峭壁,面對高原缺氧、水土不服、物資匱乏等等直接挑戰(zhàn)人生理極限的困難,意志的物質(zhì)基礎(chǔ)——身體本身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書中不斷寫到,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也不斷感嘆,這次作戰(zhàn),艱難程度遠遠超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書中還寫到了其他復雜的情況,比如趁戰(zhàn)事又蠢蠢欲動起來的叛亂,比如因宗教習俗而產(chǎn)生的與當?shù)匕傩战煌系睦щy等等。至于戰(zhàn)爭本身面對的,地形偵查、敵情偵查上的困難,后勤保障的困難,信息傳達的困難,武器裝備落后的困難,部隊臨時集結(jié)的困難等等,更是讓整個戰(zhàn)事雪上加霜。可以說,這種情形下的戰(zhàn)果,尤為來之不易;這種情形下的犧牲,更為讓人肅然起敬。尤其是那些剛剛?cè)胛榈男卤瑤缀踹€來不及感受青春的昂揚,就倒在了高寒缺氧的“第三極”。所以,當我們讀到為四百七十座烈士墓所建立的紀念碑碑文,尤其是背面的挽聯(lián)的時候,內(nèi)心的感受尤為復雜:“憶當年保家衛(wèi)國血灑邊關(guān),看今朝治邊援藏告慰忠魂。”
書中設(shè)立了一個貫穿始終的被采訪人,就是時任130師師長的董占林將軍。他的回憶和講述,既有指揮員的決策、老戰(zhàn)士為國犧牲的悲歌慷慨,更有作為新中國從成立到建設(shè)的見證者的深入思考。
據(jù)說,豐收采訪的人物有二百八十多位,書中記錄的有名有姓、有確切編制的親歷者不下五十位,兵種涵蓋了騎兵、炮兵、步兵、汽車兵等所有參戰(zhàn)兵種,軍階從普通士兵到將軍。他們除了講述自己的感受,更追憶了那些足以讓整個民族銘記的戰(zhàn)斗英雄。所有人在戰(zhàn)爭面前,都只是血肉之軀;在大歷史面前,也都只是普通人。他們無法看到全局,更無法體會這場戰(zhàn)爭在整個歷史發(fā)展中的意義和作用。如果不是豐收的采訪,不是文學的記錄,他們或許會一直在歷史的角落里沉默。
由此讓人想到諾貝爾文學獎給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頒獎詞:“她以復調(diào)式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紀念碑。”而相對于“紀念碑”這樣中規(guī)中矩的表述,我更傾向于用“文學的尊嚴”這種更道德化的詞語來形容“非虛構(gòu)”寫作。我想,寫《西長城》和《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呢S收,也堪當“文學的尊嚴”的評價。
踏遍青山人未老
如果書是有氣質(zhì)的,那么《西長城》是一本沖淡平和的書,《珠穆朗瑪?shù)捻印穭t是一本欲說還休的書。面對歷史、面對苦難、面對戰(zhàn)爭、面對犧牲,甚至面對成績、面對戰(zhàn)果,豐收都沒有表現(xiàn)得煞有介事,歷史的沉重、復雜,足以讓他冷靜、理性、克制、隱忍。
曾經(jīng),一些主旋律題材的報告文學有過這樣的弊病,即為了弘揚正確的價值觀而一味增加文本的教化作用而不是感動功能,于是原本具有質(zhì)感的故事變得空洞了,原本可親可感的人物變得概念化了。實現(xiàn)文學的真實,不管是小說的還是報告文學,都有一個技術(shù)手段或者說語言方式上的要求,那就是恰如其分、適可而止。《文心雕龍》所謂“夸而有節(jié)、飾而不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西長城》又不是一味地書寫平面化的“感動中國”的故事,它注重故事和細節(jié)的意味深長,擅長在歷史的縫隙中,在超越時代局限的人之常情中展現(xiàn)寫作者的智慧。《珠穆朗瑪?shù)捻印芬膊皇且晃兜貙懹⑿壑髁x,它努力建構(gòu)歷史的邏輯,努力尋找能夠確立歷史見識的空間。在整體“無我”的寫作格調(diào)中,那個充滿洞察力和反省精神的“我”又會適時出現(xiàn)。當然,跟整體風格相匹配,“有我”的時候也是中正持重的。
《西長城》中寫,兵團人榮譽感極強。戰(zhàn)爭中培養(yǎng)起來的集體主義榮譽感是兵團人的精神底色。但同時,又因為拉開了歷史時空的距離,很多一線的勞動者也被動地卷入了歷史大潮之中,經(jīng)歷了命運無常和人生無奈,所以,似乎只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才能讓文學扎根。《珠穆朗瑪?shù)捻印分袑懀瑥目谷諔?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走過來的中國軍隊,早已練就了不怕吃苦、排除萬難的“鐵軍”底色,英雄主義、家國使命早已融注在血液中;但同時,又因為歷史時空往縱深發(fā)展,活下來的老戰(zhàn)士開始從更深層次追憶金戈鐵馬,從更內(nèi)在的角度思考忠誠的意義,所以,似乎只有“英雄永垂,人民不朽”才能讓文學立足。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龍》),所有的人物,都是作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尊信仰的雕塑,站在豐收的文本當中;所有戰(zhàn)士的經(jīng)歷,也總是作為活生生的生活、戰(zhàn)斗場景,而不是抽象的愛國主義信念站在豐收的文本當中。自然,這樣才能夠走進時下讀者的心里。
兩本書里俯拾皆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烽火硝煙中小戰(zhàn)士的精神,書中也試圖捕捉他們的喜怒哀樂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支撐,一種毫無保留的犧牲精神,以及由這種犧牲精神而衍生出來的榮譽意識、集體意識、大局意識,久而久之,這種精神和意識就轉(zhuǎn)化成了信仰。
無論是《西長城》還是《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际窃谥v信仰,講一種與生命、與人文精神血肉相連的信仰。托爾斯泰說:“信仰就是生命。”而對兵團人、對中印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的戰(zhàn)士來說,信仰幫助他們戰(zhàn)勝恐懼和困苦,信仰幫助他們征服自然和敵人。它是時代永恒發(fā)展、歷史永恒輪回的精神底蘊,甚至,它是歷史的各種淘洗和時代的各種篩選中唯一能夠留下來的“真實”,一種永遠能夠在文學中得以保留的、有魅力的“真實”。
豐收在《西長城》的后記《鄉(xiāng)關(guān)何處》中說: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軀喚醒了荒原,用一生的血汗滋養(yǎng)了戈壁,“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離開……”在《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暮笥洝短焯荩粋€古老的傳說》中說:“青山不老,忠魂千古。”當文學記錄下這些無名英雄離開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和絲綢之路,和林公車、左公柳和艾青的詩一起,和雪域高原上的藍天、冰雪、格桑花一起,變成了“中國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組成部分,而這些故事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關(guān),是我們共同的文化積淀。
欄目責編:劉濤
猜你喜歡
兵團記憶綠洲(2022年6期)2023-01-09 10:46:38 兵團記憶綠洲(2022年3期)2022-06-06 08:17:22 在新疆(四首)四川文學(2021年4期)2021-07-22 07:11:54 新歷史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兵團在新疆農(nóng)墾經(jīng)濟(2015年10期)2015-12-20 12:26:22 歷史上的6月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歷史上的八個月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歷史上的4月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4期)2015-05-14 07:25:32 新疆多怪絲綢之路(2014年9期)2015-01-22 04:24:46 用兵團精神凝聚兵團人的夢中國火炬(2014年12期)2014-07-25 10:38:08
付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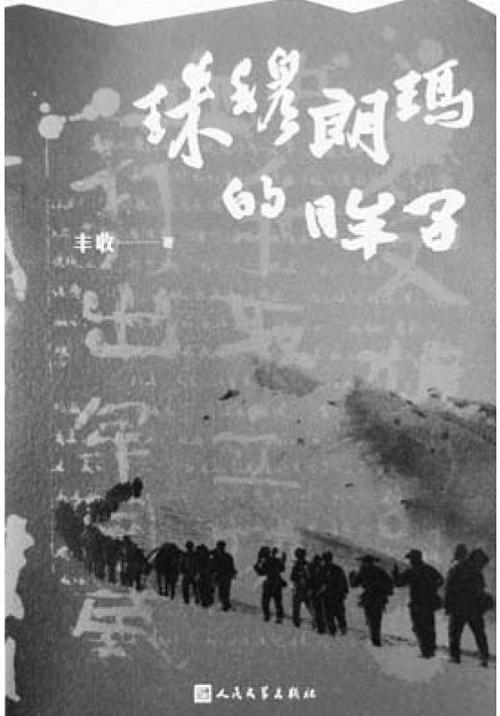
“非虛構(gòu)”的力量與困境
作為一種文體,“非虛構(gòu)”的邊界很寬泛,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歷史文學、口述實錄,甚至包括傳統(tǒng)媒體的特稿、深度調(diào)查報道等等,都可以劃到它的范疇里來。具體到中國文學,一度被稱為“時代輕騎兵”的報告文學是主流,后來隨著王樹增的戰(zhàn)爭系列和歷史系列,隨著《中國在梁莊》《我的阿勒泰》等一系列本土原創(chuàng)作品的走熱,以及以《尋路中國》為代表的引進版“非虛構(gòu)”作品的大受歡迎,報告文學的文體逐漸產(chǎn)生變化,使得“非虛構(gòu)”的概念逐漸生成并漸成主流。尤其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非虛構(gòu)”作家S.A.阿列克謝耶維奇,對這類文體的勃興更是一種提振的力量。
應該說,這是一種創(chuàng)作者充分尊重事實,將“個人”無限“隱藏”在事實和真實之后的文體;也是一種能夠直接記錄時代、直面真實、直面問題,對讀者的認識能夠直接產(chǎn)生作用的文體。如果一部作品,在事實的基礎(chǔ)上,講生動的故事,理性冷靜地看待人與事,并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人文精神,語言表述上清晰而不冗贅,真摯卻不濫情,就可以稱之為成功了。
然而,要獲得這種成功卻很難。因為無論是選材還是敘述角度,都必須在歷史語境和現(xiàn)實語境下。與虛構(gòu)相比,“非虛構(gòu)”寫作面臨的語境壓力似乎更為直接,也更為強勁。于是,“事實”變成了寫作者眼中的事實;“故事”變成了寫作者篩選、截取來的故事;而“理性和冷靜”,或者換句話說,寫作者的見識,也變成了“個人偏見”。至于“人文精神”,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是文藝作品的根基,都有魅力、都有力量,但同時,在發(fā)揮作用的時候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好在,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非虛構(gòu)”寫作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萎靡。社會現(xiàn)象越是復雜多變,知識傳播越是便捷快速,讀者對于理解世界和認識世界的需求越旺盛,作家對真實和客觀的敬畏也越強烈,俯身田野調(diào)查、埋頭真相發(fā)掘的責任感也越迫切。在這樣的作家隊伍中,新疆兵團作家豐收的身影是頗為引人矚目的。
從《中國西部大監(jiān)獄》到《西上天山的女人》,從《夢幻的白云》到《綠太陽》,從《鎮(zhèn)邊將軍張仲瀚》到《王震和我們》,從《鑄劍為犁》到《來自兵團內(nèi)部的報告》,尤其是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豐收堪稱采集新疆故事的第一人。他踏遍了新疆的每一片土地,觸摸了新疆的每一段歷史,交付了自己最旺盛的創(chuàng)作生命。他的采訪對象成百上千,積累的素材浩瀚駁雜。而新近出版的《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职涯抗饩劢褂谥杏∵吘匙孕l(wèi)反擊戰(zhàn),聚焦于那些曾在“世界屋脊”上為捍衛(wèi)國家領(lǐng)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奮戰(zhàn)的普通將士。
可以說,作為兵團二代,豐收一直在自覺地關(guān)注大歷史,關(guān)注大歷史中普通人的命運遭際。同時,他也一直矚目于今天的現(xiàn)實。且不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古至今,幾乎所有專注于歷史書寫的人,無不是在“現(xiàn)實問題不可解”的苦慮焦思中,力圖在歷史中尋求根源和路徑。同時,作為“非虛構(gòu)”作家,豐收在書寫過程中,嚴格保持了一個修史者的敬謹真誠,從未露才揚己;即便在現(xiàn)實語境的重重壓力之下,必須削句減辭,犧牲一些結(jié)構(gòu)布局的匠心,犧牲文學作品以情動人的感染力,他也從未在厚重豐沛的大歷史面前稍有怠慢,更沒有放棄自己作為兵團二代、作為一代中國作家的家國情懷。
兵團家史和西線豐碑
《西長城》序言中寫,解放戰(zhàn)爭打到1949年9月西寧解放的時候,以馬步芳為首的西北“五馬”殘部圖謀撤聚新疆,根據(jù)中共中央關(guān)于解放新疆的戰(zhàn)略布局,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命令第一兵團第二軍挺進南疆、第六軍挺進北疆。兩軍會師酒泉的第二天,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通電起義,第三天,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通電起義。1949年12月17日,解放軍駐疆部隊、三區(qū)民族軍、新疆起義部隊會師迪化,新疆軍區(qū)、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時宣告成立。之后,新疆開始剿匪平叛、建政維穩(wěn)、筑路引水、屯墾戍邊。
隨著局勢的平穩(wěn),中央決定駐新疆部隊除保留一個現(xiàn)役國防步兵師以外,絕大多數(shù)就地轉(zhuǎn)業(yè),“鑄劍為犁”,在新疆落戶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1954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正式成立,首任司令員正是率部起義的陶峙岳。之后,新疆兵團和新中國一起,經(jīng)歷了艱苦卓絕的一段歲月,全國人民熟知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十萬上海知青進新疆、“伊塔”事件之后的“三代”戍邊等都發(fā)生在這期間。
《珠穆朗瑪?shù)捻印分袑懀?962年10月,剛剛完成剿匪平叛不久的130師,返川歸建,突然接到軍委命令,中印邊境吃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即將開始,于是,各路人馬緊急從四面八方集結(jié),奔赴“世界屋脊”。新疆兵團立即向中央請命: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力支援邊防部隊作戰(zhàn)。于是,新疆邊防部隊組成了“新疆軍區(qū)康西瓦指揮部”,同時,西線六百多公里戰(zhàn)區(qū)的戰(zhàn)略物資供應任務落在了兵團汽車第一團,兵團獨立汽車第三營的肩上。盤山路貼山臨崖,冰雪覆蓋,幾乎每一次行軍和物資輸送都是在走“鬼門關(guān)”,就這樣,兵團一千一百二十五名精兵強將,為自衛(wèi)反擊戰(zhàn)輸送軍用物資六千五百噸,組成了名副其實的“生命線”。
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1975年新疆兵團被撤銷,改為新疆農(nóng)墾總局。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lián)合發(fā)出《關(guān)于恢復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的決定》。《決定》指出:“生產(chǎn)兵團屯墾戍邊,發(fā)展農(nóng)墾事業(yè),對于發(fā)展自治區(qū)各民族的經(jīng)濟、文化建設(shè),防御霸權(quán)主義侵略,保衛(wèi)祖國邊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82年6月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正式恢復,直至今天。如今的新疆兵團有14個師,174個農(nóng)牧團場,是“軍政企合一的特殊社會組織”,有37個少數(shù)民族。兵團的發(fā)展也開始從“屯墾戍邊”向“建城戍邊”轉(zhuǎn)變。
多年之后,豐收開始對這些歷史的當事人進行采訪,留下他們的回憶,感受他們歲月足跡中的崢嶸,同時,也為歷史保留驚心動魄和令人五味雜陳的真實瞬間。無論是《西長城》還是《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S收都致力于為歷史尋找更多的見證人。他尋找、探訪、傾聽、記錄,讓歷史在人身上復活,也讓人在回憶和見證中不斷樹立自己的價值和尊嚴。或許,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和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從來就不是問題的兩極,它們水乳交融,難分彼此。
《西長城》:“飄蕩在新疆大地的種子,哪一粒都有一部人生傳奇”
粗略說起來,《西長城》里的故事主角有幾類:一是部隊官兵,二是周總理說的“自動支邊人員”,三是天山湘女,四是上海知青,實際上他們也是兵團的主要人員構(gòu)成。他們的故事,就是一個國家從戰(zhàn)爭狀態(tài)走向和平歲月的全部反映——戰(zhàn)爭是歷史的極端狀態(tài),靠信仰、靠集體主義精神可以激發(fā)不可思議的潛能,正如《珠穆朗瑪?shù)捻印穼懙降哪菢印推綒q月,需要面對的是吃喝拉撒、婚喪嫁娶的日常生活,單純靠信仰、靠意志恐怕不能行之有效。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的初創(chuàng)時期,正是處于兩種狀態(tài)的過渡階段,信仰支撐下的集體主義精神仍舊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guān)懷也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于是四類故事主角之間就發(fā)生了很多或悲或喜的人生傳奇。
首先是部隊官兵。書里講到,王震的三五九旅進疆后變成了六師,進駐大芨芨草灘哈拉毛墩,一坎土曼下去,見不著土,糧食問題首當其沖:進疆部隊二十萬,國家解決不了軍糧的問題,除了自力更生,別無他法。王震說:駐守新疆,兵少了不夠用,兵多了養(yǎng)不起,解決這個難題就是走南泥灣的道路!于是,昔日的戰(zhàn)斗英雄變成了今日的種田能手。
書中講到老兵李洪清,曾在毛主席警衛(wèi)連當過連長,是被聶榮臻元帥贊賞的著名的一一五師的“蠻子”排長。他參加過五次反圍剿,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次,百團大戰(zhàn)、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后七次負傷,靠白求恩的無麻醉手術(shù)才保住了右腿,獲得“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解放獎章”,進疆之后他是巴里巴蓋草原的一名倉庫保管員。在中國最需要糧食的1961年前后,巴里巴蓋人給國家貢獻了上百萬斤糧食。1981年,李洪清和王震在石河子重逢,他對司令員說:“攻打蘭州時,你說,打不下蘭州我要你的頭,現(xiàn)在我的頭還在。”看著書中照片上,昔日的戎馬將軍和士兵相對露出忠貞赤誠的笑容,會讓人感嘆激情燃燒的歲月從未離他們而去,而這種信仰和意志在角色轉(zhuǎn)變過程中所發(fā)揮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如今看來,何其珍貴!
三五九旅唯一的知識分子團長、曾寫下兵團史詩《老兵歌》的新疆軍墾奠基人張仲瀚,用“十萬大軍出天山,且守邊關(guān)且屯田。塞上風光無限好,何須爭入玉門關(guān)”的豪邁詩句勉勵官兵,身體力行,親自拾糞種田。他一生都在倡導的南泥灣精神真正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官兵的血液。而這種精神背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是超出想象的苦難。《西長城》說:“十年、一百年,時間越久歷史越長才越明白,他們的犧牲太大太大,他們的給予太多太多。”1980年,經(jīng)歷了“文革”苦難、無兒無女的張仲瀚在北京病逝,1993年他的骨灰隨王震的骨灰重返天山。
新疆和田有一個四十七團的墓園,叫“三八線”,是以累死在田里的老兵周元開墾的長八百米、寬三百米的田地命名的,而此時,恰逢朝鮮戰(zhàn)爭期間。作家沈從文曾說:“一個士兵要不戰(zhàn)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xiāng)。”天山腳下,有太多如此遙望故鄉(xiāng)的老兵……
關(guān)于八千湘女,早已無需回避歷史的真實。在被命名為“家國 女人”的第三卷,書里寫明了來龍去脈。部隊的婚姻問題戰(zhàn)爭年代就已經(jīng)存在,扎根新疆,這個問題更是嚴峻:“沒有老婆安不下心,沒有兒子扎不下根”,于是,王震給自己的老搭檔、湖南省委領(lǐng)導王首道寫信求助:“……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歲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要她們來新疆紡紗織布,生兒育女……”沒幾天,長沙的報紙?zhí)焯煊刑柾猓盒陆妳^(qū)招聘團征召女兵!參軍去新疆上俄文學校,開拖拉機,進工廠……隨后湖南、山東、河南、四川、湖北、上海的女青年踴躍奔赴新疆……
太多的文學作品寫到了湘女的眼淚,寫到了時代對湘女的索求,豐收也并未回避這一點,但除了這些有代表性的故事,他還找到了其他,比如他寫到我黨早期,和劉少奇、何叔衡、謝覺哉齊名的革命家肖學泰的侄女肖業(yè)群,就因為在新疆找到了“根正苗紅”的婚姻而受到了保護,免遭“文革”中的政治牽連。組織包辦的婚姻在制造了很多悲劇的同時,也成就了很多喜劇,甚至護佑了很多人的命途。歷史從來就不單一和絕對。
除此之外,作者還找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入疆后女兵因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而發(fā)病的《癔病情況報告》,還有《部隊五年來婚姻問題總結(jié)報告》等等。作為報告文學作家,他有更為宏闊的歷史觀:西部的愛情和婚姻,也與所有地方的愛情和婚姻一樣,有悲劇也有喜劇,有感天動地的忠貞和生死不渝的誓言。而且,人生終究不能糾結(jié)和沉湎于苦難,“悲劇前奏、喜劇謝幕的人生長劇”更該被人記住,也更是以“真善美”為宏旨的文學作品應該具有的歷史品格和美學風范。
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點上,一代人的命運應該被記取,但無法被改變。那些美麗的進疆女子和背井離鄉(xiāng)的老兵一起,用青春譜寫了一曲西部悲歌,當然也譜寫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西部血色浪漫。
關(guān)于上海知青,問題顯然更復雜。它不是一時一地的問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全國性的,因而遺留的問題也是全國性的。與魚珊玲同為知青典型人物的楊永青出身書香門第,但她們都積極投身時代潮流,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yè)。作者說:“對于熱血青年,古往今來都是一樣,血親的力量在時代潮流面前蒼白無力。”只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血親也往往會成為她們命運轉(zhuǎn)折的理由。那時候的中國,“唯出身論”制造了多少歷史的悲劇!
楊永青說:“誰也超越不了時代。”如今看來,沒有進疆的老兵、湘女、“盲流”,就不會有新疆的今天,而沒有上海知青,兵團的教育也不會有后來的發(fā)展和改變。“時代導向他們的人生,他們也霧里看花云中望月地影響時代。歷史是一場風云際會,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會裹著你往前走。滄桑世事,潮汐人生,看世事還是看人生,他們都有了過來人的淡然恬靜。”
人生朝露,藝術(shù)千秋。當《西長城》揮筆寫下他們的故事的時候,他們的淡然恬靜早已化為一種鉛華盡洗的境界。而這種境界又反過來直接影響了《西長城》的風格,回顧故事的時候平實家常,甚至略顯絮煩,但評點人生的時候意氣平而旨趣深。這種點到即止、引而不發(fā)的風格,也影響到了《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膭?chuàng)作。當然,后者的題材更難處理,所以也更需要把握歷史和情感的分寸感。
《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p>
“戰(zhàn)爭,終究要由每一個戰(zhàn)士來完成”
與《西長城》的寫法不同,《珠穆朗瑪?shù)捻印芬驗檫x材敏感復雜,所涉歷史對普通讀者來說相對陌生,于是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篇幅,盡可能梳理清楚這場戰(zhàn)爭的來龍去脈。包括中印邊界紛爭的歷史由來、歷史演變,這又涉及到西藏、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歷史,也涉及到英屬印度期間英國在喜馬拉雅一帶的諸多政策和活動;同時,西藏在新中國解放前后的復雜局勢,平叛的艱難,以及中國軍隊在解放西藏前后所做的各種準備等等,也都需要逐一厘清。
對作家而言,歷史既是基于客觀現(xiàn)實的觀察,也是一種敘事,但敘事邏輯的建立總是受制于現(xiàn)實語境的影響,《珠穆朗瑪?shù)捻印凤@然無法超越這樣的影響。于是,豐收只能以“人”為核心,講述普通官兵的戰(zhàn)斗準備,寫戰(zhàn)斗過程中的主要戰(zhàn)役,寫勇敢、寫犧牲、寫骨肉分離、寫幸存者的回憶……借助這些,豐收力圖把歷史的幕布掀開一角,讓有心的讀者窺其一斑,思其可能。
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部分,在人類戰(zhàn)爭史上也具有別樣的意義。以在瓦弄大捷中建功立勛的54軍130師官兵為代表的我軍將士,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敵人,還有大自然。如果說,靠信仰、靠集體主義精神,將士們面對敵人的時候能夠做到視死如歸的話,面對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環(huán)境的肆虐,面對隨時可能粉身碎骨的懸崖峭壁,面對高原缺氧、水土不服、物資匱乏等等直接挑戰(zhàn)人生理極限的困難,意志的物質(zhì)基礎(chǔ)——身體本身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書中不斷寫到,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也不斷感嘆,這次作戰(zhàn),艱難程度遠遠超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書中還寫到了其他復雜的情況,比如趁戰(zhàn)事又蠢蠢欲動起來的叛亂,比如因宗教習俗而產(chǎn)生的與當?shù)匕傩战煌系睦щy等等。至于戰(zhàn)爭本身面對的,地形偵查、敵情偵查上的困難,后勤保障的困難,信息傳達的困難,武器裝備落后的困難,部隊臨時集結(jié)的困難等等,更是讓整個戰(zhàn)事雪上加霜。可以說,這種情形下的戰(zhàn)果,尤為來之不易;這種情形下的犧牲,更為讓人肅然起敬。尤其是那些剛剛?cè)胛榈男卤瑤缀踹€來不及感受青春的昂揚,就倒在了高寒缺氧的“第三極”。所以,當我們讀到為四百七十座烈士墓所建立的紀念碑碑文,尤其是背面的挽聯(lián)的時候,內(nèi)心的感受尤為復雜:“憶當年保家衛(wèi)國血灑邊關(guān),看今朝治邊援藏告慰忠魂。”
書中設(shè)立了一個貫穿始終的被采訪人,就是時任130師師長的董占林將軍。他的回憶和講述,既有指揮員的決策、老戰(zhàn)士為國犧牲的悲歌慷慨,更有作為新中國從成立到建設(shè)的見證者的深入思考。
據(jù)說,豐收采訪的人物有二百八十多位,書中記錄的有名有姓、有確切編制的親歷者不下五十位,兵種涵蓋了騎兵、炮兵、步兵、汽車兵等所有參戰(zhàn)兵種,軍階從普通士兵到將軍。他們除了講述自己的感受,更追憶了那些足以讓整個民族銘記的戰(zhàn)斗英雄。所有人在戰(zhàn)爭面前,都只是血肉之軀;在大歷史面前,也都只是普通人。他們無法看到全局,更無法體會這場戰(zhàn)爭在整個歷史發(fā)展中的意義和作用。如果不是豐收的采訪,不是文學的記錄,他們或許會一直在歷史的角落里沉默。
由此讓人想到諾貝爾文學獎給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頒獎詞:“她以復調(diào)式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紀念碑。”而相對于“紀念碑”這樣中規(guī)中矩的表述,我更傾向于用“文學的尊嚴”這種更道德化的詞語來形容“非虛構(gòu)”寫作。我想,寫《西長城》和《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呢S收,也堪當“文學的尊嚴”的評價。
踏遍青山人未老
如果書是有氣質(zhì)的,那么《西長城》是一本沖淡平和的書,《珠穆朗瑪?shù)捻印穭t是一本欲說還休的書。面對歷史、面對苦難、面對戰(zhàn)爭、面對犧牲,甚至面對成績、面對戰(zhàn)果,豐收都沒有表現(xiàn)得煞有介事,歷史的沉重、復雜,足以讓他冷靜、理性、克制、隱忍。
曾經(jīng),一些主旋律題材的報告文學有過這樣的弊病,即為了弘揚正確的價值觀而一味增加文本的教化作用而不是感動功能,于是原本具有質(zhì)感的故事變得空洞了,原本可親可感的人物變得概念化了。實現(xiàn)文學的真實,不管是小說的還是報告文學,都有一個技術(shù)手段或者說語言方式上的要求,那就是恰如其分、適可而止。《文心雕龍》所謂“夸而有節(jié)、飾而不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西長城》又不是一味地書寫平面化的“感動中國”的故事,它注重故事和細節(jié)的意味深長,擅長在歷史的縫隙中,在超越時代局限的人之常情中展現(xiàn)寫作者的智慧。《珠穆朗瑪?shù)捻印芬膊皇且晃兜貙懹⑿壑髁x,它努力建構(gòu)歷史的邏輯,努力尋找能夠確立歷史見識的空間。在整體“無我”的寫作格調(diào)中,那個充滿洞察力和反省精神的“我”又會適時出現(xiàn)。當然,跟整體風格相匹配,“有我”的時候也是中正持重的。
《西長城》中寫,兵團人榮譽感極強。戰(zhàn)爭中培養(yǎng)起來的集體主義榮譽感是兵團人的精神底色。但同時,又因為拉開了歷史時空的距離,很多一線的勞動者也被動地卷入了歷史大潮之中,經(jīng)歷了命運無常和人生無奈,所以,似乎只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才能讓文學扎根。《珠穆朗瑪?shù)捻印分袑懀瑥目谷諔?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走過來的中國軍隊,早已練就了不怕吃苦、排除萬難的“鐵軍”底色,英雄主義、家國使命早已融注在血液中;但同時,又因為歷史時空往縱深發(fā)展,活下來的老戰(zhàn)士開始從更深層次追憶金戈鐵馬,從更內(nèi)在的角度思考忠誠的意義,所以,似乎只有“英雄永垂,人民不朽”才能讓文學立足。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龍》),所有的人物,都是作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尊信仰的雕塑,站在豐收的文本當中;所有戰(zhàn)士的經(jīng)歷,也總是作為活生生的生活、戰(zhàn)斗場景,而不是抽象的愛國主義信念站在豐收的文本當中。自然,這樣才能夠走進時下讀者的心里。
兩本書里俯拾皆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烽火硝煙中小戰(zhàn)士的精神,書中也試圖捕捉他們的喜怒哀樂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支撐,一種毫無保留的犧牲精神,以及由這種犧牲精神而衍生出來的榮譽意識、集體意識、大局意識,久而久之,這種精神和意識就轉(zhuǎn)化成了信仰。
無論是《西長城》還是《珠穆朗瑪?shù)捻印罚际窃谥v信仰,講一種與生命、與人文精神血肉相連的信仰。托爾斯泰說:“信仰就是生命。”而對兵團人、對中印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的戰(zhàn)士來說,信仰幫助他們戰(zhàn)勝恐懼和困苦,信仰幫助他們征服自然和敵人。它是時代永恒發(fā)展、歷史永恒輪回的精神底蘊,甚至,它是歷史的各種淘洗和時代的各種篩選中唯一能夠留下來的“真實”,一種永遠能夠在文學中得以保留的、有魅力的“真實”。
豐收在《西長城》的后記《鄉(xiāng)關(guān)何處》中說: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軀喚醒了荒原,用一生的血汗滋養(yǎng)了戈壁,“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離開……”在《珠穆朗瑪?shù)捻印返暮笥洝短焯荩粋€古老的傳說》中說:“青山不老,忠魂千古。”當文學記錄下這些無名英雄離開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和絲綢之路,和林公車、左公柳和艾青的詩一起,和雪域高原上的藍天、冰雪、格桑花一起,變成了“中國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組成部分,而這些故事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關(guān),是我們共同的文化積淀。
欄目責編:劉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