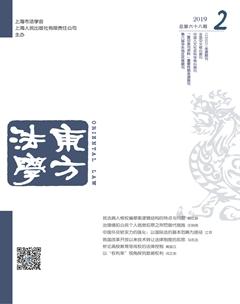羅馬法中的客體作偽型詐騙罪向后世的主體作偽型詐騙罪的演變
徐國棟
內容摘要:羅馬法確立了客體作偽型的詐騙罪,以類推適用盜贓規則的方式處理騙贓,不承認騙子及其后手可取得贓物所有權,但沒有考慮犯罪人把贓物交給誠信第三人的可能,形成法律漏洞,保羅或《學說匯纂》的編訂者填補之,允許此等第三人免受追索,由此打開了贓物誠信取得制度的大門。《法國民法典》采用了19世紀形成的主體作偽型的詐騙概念,同時保留羅馬式的客體作偽型的詐騙概念,由此形成了盜贓、騙贓處理的二元體制,騙贓獲得了獨立。繼承法國的路線,老《阿根廷民法典》同時使用新舊兩個詐騙概念,但只規定了舊詐騙概念涉及的贓物的處理,似乎留有法律漏洞。而且,該法典把老騙贓的處理置于侵權法的框架下,這樣,就把贓物所有人的原物返還請求權降等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惡化了其地位。我國是否要在未來民法典中以及未來的民法理論中區分盜贓與騙贓?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盜竊中無處分行為而詐騙中有,盜贓的流通應受到比騙贓的流通更嚴格的限制。。
關鍵詞:客體作偽型詐騙 主體作偽型詐騙 盜贓 騙贓 動產誠信取得
中國分類號:D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039-(2019)02-0082-93
一、詐騙罪被確立前古羅馬法的詐欺和詐騙
天下無騙是人類的理想,它體現在羅馬法的誠實原則中。誠實就是不講成敗利鈍地追求善,達成了“誠實”的人是好人。西塞羅舉的兩個好人案例中的好人,實際上是不欺之人。
案例一。一個誠實的人從亞歷山大運一船糧食去正在發生饑荒的羅得島。他知道許多商人已裝運糧食上船向羅得島進發,甚至在其旅途中,他還見到了這些商船正在滿帆向羅得島航來。他到達后是否應該把真相告訴羅得島人,還是應保持沉默,把他的糧食賣出一個盡可能高的價錢?西塞羅認為糧商應透露真相,否則構成消極詐欺。〔1 〕
案例二。有一個好人出賣其有缺陷的房子,這些缺陷他知人不知。例如,這所房子不宜于健康,而他人相信這所房子宜于健康。事實上,這所房子的每個房間里都有老鼠和蛇出沒,而且是用不好的建筑材料造起來的,有倒塌的危險。賣主是否必須對買主披露這些缺陷?西塞羅的答案是肯定的。〔2 〕
西塞羅舉的這兩個實例舉輕明重,排除了消極詐欺的正當性,積極詐欺沒有正當性,自不待言。
但理想與現實存在距離是生活的常態。在有人的地方就有騙。羅馬神話中有騙神,她是商業之神墨丘利的助手,惡意之神馬利切的姐妹。騙神的哥哥是詐神。這三姊妹都是黑暗之神Erebus和夜神Nox的兒女。詐神的伴當是假神或謊言之神,其對頭是真理之神。〔3 〕這些說法把每種惡德都賦予神格,并強調它們間的親戚朋友關系,頗有天下壞蛋是一家的理念。不過,把騙神與商業之神掛鉤,有害商業聲譽,但與中國的無商不奸的說法相合。
既然騙術與詐術皆有神掌管,凡界的人有騙有詐就不奇怪了。故維吉爾的史詩《伊尼阿德》就保留了一些欺騙故事。〔4 〕例如,西農騙特洛伊人:如果把木馬拉進城去,就會戰勝希臘聯軍。〔5 〕結果特洛伊人中木馬計而亡。西塞羅鼓吹無欺道德的《論義務》本身就記載了羅馬騎士卡尼烏斯受錫拉庫薩錢莊主皮提烏斯詐騙買房案件:后者在自家宅院里招待前者,雇來漁人在自己房產前的海域駕船來來往往,打魚眾多并獻來做菜,營造出該別墅毗鄰多產漁場的假象。前者遂主動求購這處別墅,最后按后者的報價買下了這塊不怎么值錢的地產。〔6 〕可憐的他發現了真相后卻得不到法律救濟,只能為自己的輕率冒失付出代價。〔7 〕后來,法學家阿奎流斯·伽魯斯創設詐欺程式才改變這種局面。此等程式包括詐欺之訴和詐欺抗辯。前者是一項訴權,獲得者可請求詐欺的實施者補償自己所受損失,并造成后者破廉恥。詐欺抗辯由裁判官依據被告的申請決定是否授予。若認可其異議,便在程式中插入“假如在爭端中沒有發生過原告自己所為的或通過他人所為的詐欺”的條件句,授權法官在裁判審階段探查兩種方式的“詐欺”是否存在,若有,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開釋被告。〔8 〕卡尼烏斯可利用這兩項救濟中的前者,起訴皮提烏斯要求賠償損失,并解除合同。當然,如果卡尼烏斯也騙了皮提烏斯,例如,給付的價金中包含假幣,則皮提烏斯可利用后種救濟。不難看出,阿奎流斯·伽魯斯創設詐欺程式,旨在杜絕包括被告方面,以及原告方面的詐欺,達成天下無騙的美好局面。
二、詐騙罪的確立及其案型
阿奎流斯打造的詐欺程式處理的是民事詐欺,刑事的詐騙罪到3世紀上半葉才開始確立。〔9 〕羅馬人把這種犯罪稱為“毒蝎”,表達了對它的厭惡及其危害性的認知。羅馬法學家從未給這種罪行下過定義,所以還是讓我們根據原始文獻中揭示的這種犯罪的案型來嘗試提煉其定義。
案型1:出質人以銅冒充金作為質物。此時,要按質物是金子的情形讓出質人承擔責任,同時要他承擔詐騙的責任(烏爾比安:《薩賓評注》第40卷。D.13,7,1,2)。〔10 〕
案型2:出質人給付金塊為質,后以銅塊替換之;或在給付的過程中以銅換金。前種情形按盜竊擔責;后種情形按穢名擔責,替換者還要承擔出質人的責任,外加詐騙責任(烏爾比安:《薩賓評注》第11卷。D.13,7,36pr.)。〔11 〕
案型3:出質人一物多質。他在締結最后一個債時隱瞞質物已承受其他負擔的情況,此時他要承擔詐騙的責任,但他提供擔保并償付全部債權人的,除外(232年2月15日亞歷山大皇帝致亞歷山大。C.9,34,1)。〔12 〕
案型4:出質人以已給與他人、出質他人或受公共利益束縛的物出質另一人,此時他仍要承擔質權人之訴,并承擔詐騙責任,但以他明知質物上已存在上述負擔者為限。換言之,不知者不為罪(保羅:《薩賓評注》第29卷。D.13,7,16,1)。〔13 〕注意:這一案型中的第一種情形與案型3重復,這種重復由不同的作者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同一問題造成。
案型5:贈人一物后,又把該物抵押給另一人。具體情節是父親贈兒子一物,辦理了交付,兒子取得了對此等物的所有權,但父親旋即又把該物在兒子不知情的情況下抵押給自己的債權人。此時,抵押無效,但兒子也不能控告乃父詐騙(239年哥爾迪安皇帝致瓦倫斯。C.9,34,2)。〔14 〕換言之,如果這種詐騙并非發生在父子之間,控告可以為之。〔15 〕
案型6:債務人書面偽誓說質物屬于他,實際上并非如此(莫特斯丁:《論刑罰》第3卷。D.47,20,4)。〔16 〕這一案型與案型4的第二種情形相切,都是以他人之物作為自己之物出質,但采用了偽誓的方式。所以,是債務人的偽誓行為導致成立詐騙,出質他人之物不過是偽誓要掩蓋的事情。
案型7:明知法官確認的債務不存在或雖存在但已履行,仍通過執行此等判決獲取金錢(烏爾比安:《論斷集》第7卷。D.17,1,29,5)。〔17 〕這一案型包含兩種子案型。其一是無債索債,發生于羅馬人的法律行為書面化,書面記載之事與實際發生之事可能背離的情境。例如,在借貸合同中,當事人先要訂立書面合同,載明債務人借了多少,應還多少,然后債權人再向債務人放款。書面文件的達成標志著合同的成立,放款是對合同的履行。但如果書面合同訂立了,債權人拒不放款,而且還要求債務人還債。在形式主義的條件下,債權人的此等請求是可以執行的,債務人會敗訴。〔18 〕但利用此等敗訴獲利的所謂債權人要承擔詐騙罪的責任。其二是已還債仍索債,在債務人已還債,但未要回借據的情形下發生。
案型8:繼承人隱瞞遺囑人設定的解放條件出賣待自由人(烏爾比安:《薩賓評注》第28卷。D.40,7,9,1)。〔19 〕待自由人是遺囑人在遺囑中宣布解放的奴隸,他現在仍是奴隸,但具有獲得自由的可能性,所以是奴隸與自由人之間的中介,不能按完全的奴隸對待。但繼承人的解放表示藏于密封遺囑中,可能為繼承人壟斷,如果他隱瞞解放的遺囑人表示不宣,在遺囑人亡故后把待自由人當作普通奴隸出售,這一方面糟蹋了遺囑人的心意,另一方面斷送了一個奴隸的自由,構成本種詐騙。
案型9:與第三人聯合行騙或通謀以損害特定的人(烏爾比安:《論行省執政官的義務》第8卷。D.47,20,3,1)。〔20 〕前文講到的皮提烏斯詐騙卡尼烏斯買房案構成這一案型。這里的詐騙人是皮提烏斯,“第三人”是那些在別墅旁假裝捕魚的人。他們的人數應該不止一個,所以,這里的“第三人”應是復數。
上述9種案型的前6種都關乎擔保,旨在保障擔保秩序以及擔保權人的利益,只有后3種案型與擔保無直接關系。由此我們可以說,羅馬法中的詐騙罪名主要是保障擔保法正常運作的公法手段。其他的案型,很可能是在擔保法案型基礎上擴張形成的。所以,黃鳳和張長綿把Stellionatus翻譯為“交易欺詐罪”,〔21 〕不無道理。
上述9種案型,除第7種和第9種外,都關乎偽造客體的品質或身份。把銅說成是金,是偽造品質,案型1、2屬此;把已承受了負擔說成無負擔,是偽造身份。案型3、4、5、6涉及偽造物的身份,案型8涉及偽造奴隸的身份(對買受人說此等奴隸不享有取得自由的期待權)。在羅馬法中,奴隸主要是客體,所以案型8仍屬于偽造客體的身份。至此我們可以說,羅馬法中的詐騙主要通過偽造客體的品質或身份進行。
9種案型中的詐騙何所指耶?由于古代法學家都以決疑法談論這種罪的各種具體形式,不對它們作抽象概括。所以,這對于今人是一個折磨人的智力的問題。意大利刑法學家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1805-1888年)認為對于詐騙只能列舉,不能定義。〔22 〕所以,中世紀西班牙頒布的《七章律》也沒有給詐騙下定義并劃定它與偽造罪的界限,而是列舉了一系列類似于羅馬人的Stellionatus的行為。〔23 〕有些不畏難的后人嘗試根據上述9種案型給羅馬人的Stellionatus下定義,往往顧此而失彼。例如,上述卡拉拉把Stellionatus定義為不當處分他人之物,〔24 〕這一定義可嚴絲合縫或勉勉強強涵蓋案型3、4、5、6,但不能涵蓋其他案型,盡管《阿根廷刑法典》第173條第9項采用這一定義。〔25 〕維基百科西班牙語版將Stelionato定義為合同詐騙,〔26 〕該定義可嚴絲合縫或勉勉強強涵蓋案型1、2、3、4、5、6、9,但不能涵蓋案型7、8。
正因為Stellionatus難以定義,人們干脆放棄了對之定義的努力,在它之旁另創新的詐騙概念,以避免詐騙罪與其相鄰罪名糾纏不清的狀況。對此問題,筆者將在本文第四部分談論。
不妨看看上述案型是否與我國《刑法》第266條規定的詐騙定義兼容。該定義辭曰:詐騙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這個定義有“占有”“欺騙”“財物”3個要素。占有的要素的達成要求詐騙人把贓物納入自己的囊中;欺騙包括積極的(虛構事實)和消極的(隱瞞真相)作偽。可以被作偽的,可以是主體,例如詐騙犯老百姓一個,卻宣稱自己是高官。也可以是客體,例如把自來水說成是礦泉水甚至神藥;財物是有體物,而且必須數額較大,由此排除了“色”作為詐騙客體。按照這個定義,羅馬法學家提供的9種案型都構成詐騙,前6個案型中的詐騙人通過隱瞞擔保物的事實或法律屬性騙得了相對人的借款或其他給付。案型7中的詐騙人則通過消極詐騙獲得了判決的金錢。案型8中的詐騙人也通過消極詐騙獲取了待自由人的價金。案型9中的詐騙人則通過積極詐騙取得了不良房產與優質房產之間的差價。所以,我國刑法關于詐騙的定義可以適用于古羅馬的詐騙罪,不似許多現代西方國家刑法中的詐騙定義作不到這一點,這主要歸因于我國的詐騙罪定義不以主體作偽為限。
然而,有一種羅馬的詐騙行為不能為我國刑法的詐騙定義包納,那就是債務人轉移財產逃避對債權人承擔責任的行為,通常被稱為詐害債權人行為。它有“欺騙”的要素,卻無“占有”和“財物”的要素,此等要素歸屬于接受財產移轉的第三人。對于為詐騙的債務人來說,他追求的并非自己財產的增加,而是不減少。羅馬裁判官保羅創立了保利安訴權對付這種詐騙。其內容為賦予債權人撤銷訴權,據以讓債務人移轉的財產恢復原狀。〔27 〕但債務人無須為自己的詐騙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西塞羅于公元前65年寫的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提到了適用這種訴權的一個案件。〔28 〕所以,這種訴權的創立時間當在這個時間以前,早于詐騙罪的確立時間。
所以,與我國刑法中的詐騙罪包攬一切騙財(如上所見,騙色被排除 〔29 〕)行為不同,羅馬法中的詐騙是個剩余罪,凡是在前的其他法律不打擊或打擊不了的詐騙都歸這個罪名打擊。〔30 〕這樣的詐騙罪補遺的對象主要有公元前81年頒布的《關于偽造的科爾內流斯法》,其第1條懲治偽造遺囑罪,主要針對代書人在為他人代書遺囑時書寫有利于自己的條款的行為;其第2條懲治偽造貨幣罪。〔31 〕該法從“偽”的角度打擊妄得他人錢財的行為,因為偽造遺囑也好,偽造貨幣也好,最終的目的都是得人遺產,得人財貨。而詐騙罪從“騙”的角度打擊妄得他人錢財的行為。實際上,“偽”不過是積極的“騙”。偽也好,騙也好,都是讓人陷入錯誤而掏腰包。
三、詐騙罪的追究以及贓物處理
富有意味的是,上述9種詐騙案型的直接侵犯客體都是私人利益,但帕比尼安說,相應的訴權并非私訴(D.47,20,1),〔32 〕也并非公訴,〔33 〕即人人可得提起的訴訟,正確的控告人是總督(D.47,20,3)。〔34 〕此乃因為詐騙罪得到確立時,羅馬進入了非常訴訟時期,國家充當起控告犯罪的責任,私訴和公訴這些概念已經作古。然而,詐騙都發生在私人交易中,總督如何得知發生了詐騙從而訴之是個問題。可能是詐騙的受害人先向總督舉報,總督經審查屬實后再提告。
一經坐實確有詐騙,所處刑罰依被告的身份而異。出身低下者,判處礦坑苦役,即當國家公奴;身份高貴者,判處開除出其等級并放逐小島。〔35 〕另外承受破廉恥。相比于我國《刑法》對于詐騙犯的從3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的處罰,夠重的。
處罰完了詐騙犯,接下來的問題是處理詐騙的贓物。
首先要說明的是,羅馬法中并無關于詐騙罪贓物的專門規定,只有關于盜竊贓物的專門規定。按照羅馬人的理解,物被盜后,所有權并不發生變動,仍在所有人手中。他可依據源于盜竊的請求返還訴索回之。此訴的被告既可以是盜賊本人,也可以是其繼承人(D.13,1,5。保羅:《薩賓評注》第9卷),〔36 〕即使其必要繼承人是精神病人或幼兒,也不例外(D.13,1,2。彭波尼:《薩賓評注》第16卷)。〔37 〕提起此訴后,如果盜竊物還在,則索回之;如果已滅失,則索回其估價(D.13,1,8pr.。烏爾比安:《告示評注》第27卷) 〔38 〕或其轉化物,例如被盜的牛已被殺,則索回的對象是牛皮、牛肉、牛角(D.13,1,14,2。尤里安:《學說匯纂》第22卷);〔39 〕如果被盜的葡萄已被加工,則索回的對象是葡萄汁和葡萄渣(D.13,1,14,3。尤里安:《學說匯纂》第22卷)。〔40 〕
以上是所有人知道盜竊物系誰所盜從而訴追的情形,在不知物為誰所盜從而未能提起源于盜竊的請求返還訴的情形,贓物仍在盜賊手中,但他永遠不能取得其所有權,所以他會一直處在非法占有或曰不當得利狀態。即使他把此等物交給其子女繼承或轉讓給他人,他們也會成為源于盜竊的請求返還訴的被告。非獨此也,盜贓也不能由任何受讓人取得,不論他們是誠信還是惡信。它的唯一合法流通方向是回到原所有人手中。這種流通性受限,用取得時效制度的術語表達,是“標的不適格”。〔41 〕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是把贓物定性成了一種不流通物。〔42 〕其體現了絕不姑息盜竊的精神。
但上述精神有一個古老的例外,那就是公元前450年的《十二表法》確立的“已造橫梁之訴”。該制度見諸第六表第8條和第9條。前者曰:偷來用于建筑房屋的梁木或用于葡萄園的架材,不得拆走。但可對盜取它們的人,提起賠償加倍于其價金的訴訟。后者曰:修剪葡萄藤之日,即為取回架材之時。〔43 〕兩者處理所有人的追贓權與公共利益保護的關系。它涉及這樣的情境:某個盜賊盜竊了他人的木料,用來作自己房子的橫梁或搭自己的葡萄架,所有人發現自己的木料或架材被盜及其所在后,并不能用物權之訴追回它們,只能利用損害賠償的債權之訴要求盜賊加倍賠償木料或架材的價值。因為拆除已建好的房子的梁木或正支撐生長中的葡萄的架材,會破壞社會財富,為一個比較小的價值犧牲一個較大的價值。為了避免這種不利后果,所有人的權利就要受到部分犧牲,他只能得到梁木或架材的雙倍價金作為補償。當然,如果地震毀壞了房子,梁木可以抽出來;或者葡萄已被收獲,拆除支架不會影響葡萄生長,梁木、架材的所有人也可取回它們。
《十二表法》的上述兩條考慮的是盜賊本人把他人的梁木或架材用于自己建房或搭葡萄架的情形,顯得對盜賊過于寬仁,后世的法學家保羅不滿于此,對上述規定作出糾偏性解釋。其辭曰:根據《十二表法》,被架入建筑物的他人的木梁是不能被要求返還的,也不能因此提出出示之訴,除非被起訴者是明知還將木梁架入……[《告示評注》第21卷(D.6,1,23,6)] 〔44 〕按照這個法言,被架入他人房屋的梁木是否可被要求原物返還,取決于架入人的主觀狀態。誠信架入的,即誤把他人的梁木當作自己的梁木架入的,不得被要求原物返還,也不得被要求出示;惡信架入的,即明知梁木屬于他人仍然將其架入自己房屋的,則梁木主人既可要求原物返還,也可要求出示。惡信的架入者,顯然是盜賊本人或以明顯的不正常價格從他購得梁木者。誠信的架入者,就是以正常的市價從盜賊購得梁木者。
然而,德國學者經過考證,認為上述法言中的“除非被起訴者是明知還將木梁架入”一語是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編纂班子添加的。〔45 〕這樣的考據并非無理,因為保羅的法言背離《十二表法》的規定十分突然。但保羅未說的就是優士丁尼6世紀的《學說匯纂》編纂班子說的,這些編纂者認為應區分架入者的誠信與否,以判斷是否允許盜贓所有人行使原物返還請求權。
無論如何,通過保羅或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編纂班子的工作,贓物的所有人的追贓權終于在誠信取得人的誠信前止步。保羅生活在2—3世紀之間,《學說匯纂》的編纂者生活在6世紀,那種認為贓物的誠信取得制度起源于13世紀開始形成 〔46 〕的日耳曼法的觀點忽略了保羅或《學說匯纂》的編纂者的貢獻。按照這種觀點,日耳曼法實行“以手護手”原則,意思是“動產沒有后手”或“出了問題只能找你授信的人”,所以,贓物的所有人如發現受讓人占有贓物,他不得訴追后者,只能訴追受讓人的前手盜賊或騙子,以得到損失之賠償,由此保障交易安全。對占有人的照顧并未考慮其是誠信還是惡信,保羅或《學說匯纂》的編纂者倒是考慮到了這一方面,所以,把誠信取得制度的起源歸于他們,似乎更有理由。
但誠信取得制度如果僅僅適用于梁木,則該制度的適用范圍過窄。蓋尤斯進行了擴張,謂:“《十二表法》中的‘梁木指構成建筑物的各種建筑材料”。〔47 〕由此擴張了強制添附制度的適用范圍,也導致了誠信取得制度適用范圍的擴張。
那么,對于詐騙的贓物怎么辦?按照處理盜贓的原則辦。烏爾比安通過以下的法言把對盜贓的處理規則擴用于騙贓:只要所有人不因自身行為而失去物之所有權,就可提起請求返還之訴(D.13,1,10,2。《告示評注》第38卷)。〔48 〕騙贓當然不是所有人因為自身的表意行為喪失的,所以當然是請求返還之訴的訴追對象。這是所有人及其繼承人享有的針對盜賊本人及其繼承人,但不針對盜賊的同謀者的訴權,目的是返還被盜物本身及其從物;在不能返還的情況下,要求賠償所有因為盜竊引起的損害。即使盜賊的繼承人由于各種原因已脫離了對被盜物的占有,仍然要根據此訴承擔責任,此時通常是賠償責任。
四、歐美國家詐騙概念的變化引發騙贓獨立于盜贓
(一)詐騙概念的變化
如前所述,羅馬法對騙贓比照盜贓處理。但羅馬法中的詐騙概念具有過大的決疑性,體現了美索不達米亞方法,即橫向平涂法。其特征是通過列舉一切現象來說明考察對象本身,但不對諸現象的本質進行抽象并定義。與其對立的是縱向的希臘方法:即從諸現象中抽象出定義,再以屬-種的方式圈圍諸考察現象或加以排除的方法。《十二表法》時期的羅馬法采用美索不達米亞方法,〔49 〕從公元前2世紀開始,羅馬人改采希臘方法。但吊詭的是,他們在3世紀前半葉創立詐騙罪時,仍采用了美索不達米亞方法。正因為如此,羅馬詐騙罪的9種案型不能塞進多數按照希臘方法構建的現代刑法的詐騙定義,即使我國主客體作偽兼包的詐騙定義,也不能包納債務人轉移財產詐害債權人的行為。
希臘方法在中世紀得到了加強,當時的學者嘗試歸納羅馬人的9種詐騙案型的本質為偽造,然后把詐騙罪作為偽造罪的一種次級罪名。〔50 〕這樣的處理不無道理,因為如前所述,9種案型中的7種,都可嚴絲合縫地或大致過得去地被定性為客體作偽。然而,有兩種案型涵蓋不進去,這樣的嘗試可以說已經失敗了。18-19世紀的學者們發現,如果自限于羅馬人留下的9種案型進行詐騙罪界定,不可能成功,若想成功,必須另辟蹊徑。所以,法國1791年7月19日的一項法律第35條用Escroquerie一詞取代Stellionnat表示詐騙,把前者定義為:通過用假名或假身份,或通過欺騙性的操作讓人相信假企業的存在或想象的權力或信用的存在,或催生對一個成功、一個事故或任何其他模糊不清的時間的希望或恐懼,以此得到土地、動產、債、處分、票據、允諾的交付或免除交付,或故意促成此等交付或免除交付的行為。〔51 〕簡化一下,這個定義無非說詐騙是制造假象騙人錢財。不過,羅馬人的Stellionatus主要指制造客體的假像,法國法中的Escroquerie主要指制造主體的假象。所以,Escroquerie對Stellionatus的取代,主要是主體描述路徑對客體描述路徑的取代。
這個定義稍加變動成了1810年《拿破侖刑法典》第405條的詐騙定義。該條處在“破產與詐騙以及其他種欺騙”的標題下,所謂“其他種欺騙”,即濫用信任,例如未成年人對成年人的信任、一般人對支票的信任等。現行《法國刑法典》(1994年3月1日生效)第313-1條規定的詐騙定義也大致保留了1791年7月的法律的詐騙定義的內核。〔52 〕沿著法國開辟的路徑,德國、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國的刑法都規定了新型的、主體偽造型的詐騙定義,并用新的術語表示詐騙。例如,德語采用Betruge、意大利語采用Truffa、西班牙語采用Estafa。〔53 〕
但是,法國立法者并未因為新的詐騙概念的確立而拋棄羅馬人的遺產,《法國民法典》在其第2059條等條中仍對Stellionnat進行規制。該條用Stellionnat一詞涵蓋:1、明知不屬于自己的不動產而以之出售或抵押的行為;2、把設有抵押權的不動產詭稱為未設有負擔,或詭稱不動產上設定的抵押權小于其實際負擔的行為。對于這兩種行為,科處行為人民事拘留。而且贓物的所有人仍可追索此等行為的標的物(第2069條)。〔54 〕不難看出,第一種行為是對羅馬法中的Stellionatus的案型4、5、6的概括。第二種行為是對羅馬法中的Stellionatus的案型3的概括。富有意味的是,這里的Stellionnat被李浩培等學者譯為“假冒”,或許反映了中世紀的人們試圖用“假冒”概括羅馬人留下的9種案型的努力。這樣,拿破侖時期的法國,立法者打散羅馬人留下的Stellionatus,分別用刑法和民法調整其中的一些案型。
但《法國民法典》關于Stellionnat的規定已被廢除。之所以如此,乃因為它首先受到了1855年3月23日頒布的關于抵押的公示的法律 〔55 〕的動搖,通過公示抵押權據以設立的法律行為減少了抵押他人之物成立的可能性。盡管如此,抵押他人之物仍然可能給粗心大意的債權人造成損害。所以,Stellionnat并未被廢除。導致它被廢除的是1867年7月22日頒布的關于廢除民事拘留(實際上是債務監禁)制度的法律。債務監禁制度違反了人身利益高于財產利益的原則,因此被廢除,帶動適用民事拘留的關于Stellionnat的條文被廢除。但直到現在,Stellionnat仍可能發生,《法國商法典》和《民事訴訟法》還保留少許關于此等行為的條文,但法律上已無對此等行為的正式制裁。〔56 〕
所以,盡管在法語詞典中,都把Stellionnat一詞解作重抵押罪、重賣罪。〔57 〕但在現行《法國刑法典》卻中找不到這一罪名,只能在曾經是法國殖民地國家(例如幾內亞和貝寧)的刑法典中找到。
(二)騙贓的獨立
1804年版的《法國民法典》有5個條文處理贓物(包括盜贓、騙贓和“假冒”贓)。
首先是處理盜贓的第2279條和第2280條。前者曰:1.對于動產,占有有相當于權利根源的效力。2.但占有物如系遺失物或竊盜物時,其遺失人或被害人自遺失或被盜之日起3年內,得向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但占有人得向其所由取得該物之人行使求償的權利。〔58 〕后者曰:現實占有人如其占有的盜竊物或遺失物系由市場、公賣或販賣同類物品的商人處購得者,其原所有人僅在償還占有人所支付的價金時,始得請求回復其物。
第2279條把羅馬法的無期限限制的追贓體制改為只允許追3年,隱含3年后贓物占有人取得對贓物的所有權的意思,對于誠信的贓物占有人,尤其如此。第2280條未使用“誠信”的術語,但從市場、公賣或販賣同類物品的商人處購得,體現的就是“誠信”。〔59 〕所以,該條規定的就是盜贓的誠信取得人可以誠信取得贓物。
其次是處理“假冒”贓的第2069條:民事拘留的判決,并不阻止或停止對于其財產的追索和執行。〔60 〕按照此條,被以“假冒”方式出售或抵押的不動產,可以追回。
再次是處理騙贓的第1967條:在任何情形下,敗者不得請求返還其自愿支付的金額,但勝者如有詐欺、欺瞞或騙取情形時,不在此限。〔61 〕該條處在博戲及賭博的標題下,處理不誠實賭博的贓物問題,采用原物返還的處理方式。
由于第1967條只處理賭博中的詐騙,范圍狹窄,產生是否可把第2279條擴用于騙贓的問題?巴黎法院在1834年1月13日作出的一個判決中持肯定說。理由是立法者在該條中用的“竊盜”一詞含義寬泛,包括一切類似于盜竊的行為。詐騙的效果與盜竊的效果相同,都是用非武力的方式不法獲取他人財產,故第2279條可擴用于騙贓。但法國最高法院在1835年5月20日的一個判決中持否定說。理由是應按照第2279條所用竊盜術語的嚴格含義適用該條,不應把竊盜混同于詐騙。詐騙的特征是取得相對人的信任,通過后者的出售、自愿的交出等方式占有財產,而這樣的出售和自愿交出在竊盜中沒有。所以,如果把第2279條擴用于騙贓,則誤用了該條。〔62 〕簡言之,盜竊的犯罪侵犯客體是財產,詐騙的犯罪侵犯客體是信任。考慮到最高法院的判決更加權威且產生較晚,應認為它的意見具有支配性。由此,第1967條采用的原物返還的騙贓處理方法可能被擴用于一切騙贓。至此,在法國,騙贓終于獨立于盜贓得到處理。
最后是至今未有人認為具有處理贓物功能的第554條:土地所有權人用不屬于其本人的材料進行建筑、栽種或工程,應當償還按照支付之日計算的材料的價款;如有必要,得被判處損害賠償;但是,材料所有權人沒有拆取這些材料的權利。〔63 〕如果我們認可該條是《十二表法》第六表第8-9條的繼承和擴張(《十二表法》的上述兩條只涉及建筑,該條除此之外還涉及栽種和工程),它的處理贓物歸屬的功能十分昭然。按照該條,贓物(無論是盜贓還是騙贓)如果被納入盜賊、騙子或誠信第三人的建筑、青苗、工程,贓物所有人只能請求賠償,但不能主張原物返還,以此避免社會財富的破壞。
五、舊《阿根廷民法典》對盜贓和“假冒”贓的區別對待
法國區分盜贓和騙贓的做法影響了《阿根廷民法典》(1862年)的起草達爾馬雪·貝萊斯·薩爾斯菲爾德(Dalmacio Velez Sarsfield,1800-1875年),這一民法典的第2766條規定:盜竊物的認定,僅僅適用于對他人之物實施詐害性的竊取行為,并不適用于信任的濫用、寄托合同的違反,也不適用于使某物脫離所有權人控制的任何欺騙或詐騙行為。〔64 〕該條排除了關于盜贓的條文對于騙贓的適用。此條中的贓物包括兩種。其一,受托保管的他人之物,例如監護人管理的被監護人之物,受寄托人保管的寄托人之物等;其二,詐騙得來之物。前者是背信行為的贓物,后者是騙贓。在第2766條,騙贓盡管取得了相對于盜贓的獨立,但又被依附于背信行為之贓,仍然是個配角,它的法律處遇受制于對背信行為之贓的法律處遇。盡管如此,第2766條昭示了《阿根廷民法典》要對盜贓和騙贓以不同的制度處理。對于后者,按照以他人之物締約制度處理。
《阿根廷民法典》關于盜贓設3個條文。第2765條規定:遺失動產之人或其動產被盜竊之人,即使在該物處于誠信第三人權力之下時,亦可請求返還。第2768條規定:自誠信第三人手中收回遺失的或失竊的動產之人,無須償付第三人已支付的價金,但該物是在公共出售場所或出售類似物品的商店,連同其它類似物品一起被出售時,應為例外。〔65 〕第4016條附條規定:在3年期間里對被偷竊的或遺失的動產進行誠信占有之人,因時效取得其所有權。對于被移轉時要求在已建立的或應建立的登記簿上進行登記的動產,在針對偷盜物或遺失物而規定的同一前提下,其所有權的取得時效為2年。在兩種情形中,占有均應為誠信的和持續的。〔66 〕頭兩條允許盜贓的所有人一追到底,即使追到誠信第三人,也可無償取回贓物。例外是從公開出售場所或出售贓物所屬物品的專門店購得贓物的第三人,他們應向其前手支付價金。實際上,從公開出售場所購得是主觀誠信的外部表征。所以,能夠利用這一“例外”的第三人也是誠信的,他們得到照顧的理由是其主觀誠信已經客觀化。所以,上述例外的設立把可以甚至從誠信第三人一追到底的規則打折了。最后一條把一追到底改為只能追3年或2年,它是1968年的第17.711號法律(《民法典改革法》)增加的,是對《法國民法典》第2279條第2款的追加性繼受,并在法國藍本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規定了經登記的盜贓的時效取得問題,由于登記,賦予此等盜贓的誠信占有人時效期間較短的利益。
另外,還可認為《阿根廷民法典》第2587條也處理盜贓。它規定:在自己地產上以他人的種子、植物或材料播種、種植或建筑之人,取得所有此等物的所有權;但他負有支付其價值的義務;若屬惡信,尚須賠償損失和損害,在發生刑事后果時,應對刑事控訴的結果負責。種子、植物或材料若嗣后被分離,其所有權人可在適當時請求返還。〔67 〕該條比《法國民法典》第554條對盜贓的態度更為嚴厲:允許盜贓所有人在盜贓脫離被添附物時行使原物返還請求權。
《阿根廷民法典》為“假冒”贓設兩個條文。第1178條規定:將他人之物作為自己的物而締約之人,如未交付此等物,則構成假冒性的侵權行為,并應對一切損失和所失利益承擔責任。第1179條規定:惡信將爭訟物、質物、抵押物或扣押物作為不受拘束之物而締約之人,在當事人他方誠信接受允諾時,亦構成假冒之侵權行為,并應對一切損失和所失利益承擔責任。〔68 〕不難看出,這兩條是對《法國民法典》第2059條的拆分,但不以民事拘留處置,而是作為侵權行為處理。這顯然受到了著名法國民法學者普蘭尼奧爾學說的影響,他在法國廢除了民事拘留制度的時代寫作,把這一制度的打擊對象之一“假冒”定為一種侵權行為。〔69 〕
既然如此,《阿根廷民法典》第1178條和第1179條處理的就是“假冒”贓而非騙贓,在這部4051條的民法典中找不到關于騙贓的規定,盡管薩爾斯菲爾德在宣告騙贓獨立于盜贓的第2766條中,對詐騙用的是新詞Estafa,但對此無后續規定,能夠視為后續規定的只有關于“假冒”的兩個條文,看來,薩爾斯菲爾德是把“假冒”當作“詐騙”的同義詞使用了。〔70 〕所以,舊《阿根廷民法典》只是形式上確立了Estafa,實際上還處在羅馬法留下的Stellionatus的窠臼中,并留下了對Estafa的贓物無明確規定的立法漏洞。因為Estafa的外延比Stellionatus寬,不以出賣或抵押他人之物為限。即使把該法典規定出賣他人之物的第1329條 〔71 〕解釋為處理騙贓的規定,也存在問題,因為詐騙者對贓物的無權處分不以“出賣”為限,還可以贈與、遺贈等,所以,僅僅以出賣他人之物制度處理詐騙贓,未免引起涵蓋面不足的問題。而且,盜贓與詐騙贓,都是不法取得的他人財產,在本質上并無區別,賦予兩種“贓”過分不同的待遇,并非理由充分。
所以,法國區分盜贓與騙贓的做法是否在舊《阿根廷民法典》中得到了采用,可以爭論,但無可爭論的是,法國開創的區分盜贓和“假冒”贓(就是古羅馬的騙贓)的做法在舊《阿根廷民法典》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說“發揚”,指舊《阿根廷民法典》把“假冒”贓的處理問題從物權法的場域帶到了侵權法的場域,贓物所有人的權利因此從原物返還請求權變成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法律地位惡化了。
結? 語
上述研究對于中國的意義如何?換言之,我國是否要在未來民法典中以及未來的民法理論中區分盜贓與騙贓?這是個問題。首先要承認,盜竊與詐騙的犯罪客體不同,前者的客體是財產,后者的客體是信任,盡管取得信任后還是侵犯了受騙者的財產。我國刑法把盜竊與詐騙都作為侵犯財產罪定性值得推敲。《德國刑法典》把詐騙與背信單列一類罪名的做法值得借鑒。〔72 〕既然盜竊罪與詐騙罪的侵害客體不同,盜贓應不同于騙贓。確實,在我國臺灣地區,是區分兩者的。謝在全教授認為:兩者的區分在于,盜贓的移轉非出于所有人的意思,騙贓的移轉出于移轉人的意思。〔73 〕所以,前者的所有人可按“臺灣民法典”第949條 〔74 〕行使原物返還請求權;后者的所有人則不可。〔75 〕日本學者大谷實也認為:詐騙罪中包括處分行為,由此使它區別于盜竊罪。〔76 〕這樣的觀點值得借鑒并已得到借鑒。2011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規定: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贓物的,不予追繳。這等于說,騙贓的誠信取得人,可在處分行為之后立即取得對此等騙贓的所有權。而盜贓的誠信取得人,要經過一定的時效期間(在法國和阿根廷,都是3年)才能取得贓物的所有權。這樣,騙贓并不被設定為不流通物,而盜贓在一定程度上被設定為不流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