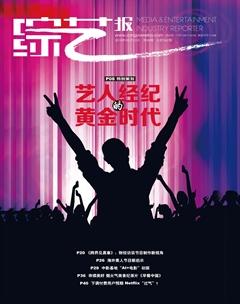《復聯4》“霸幕”里的積極信號
五·一前一周上映的《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以下簡稱《復聯4》),不出意外地稱霸了中國市場6萬多塊銀幕。有評論認為這很可怕,對這種一邊倒的情況也很擔憂——這種聲音在過去幾年里其實一直存在,比如《速度與激情》系列橫掃市場的時候,或是《阿凡達》狂風暴雨般席卷市場的時候,但國產電影并未節節敗退,在持續的競爭壓力之下始終向前、不斷攀高。
當然,對《復聯4》的狂歡保持冷靜和憂思是必要的,但對事物的看法,并非是只有足夠的悲觀才能促進進步,有時候積極的信號也能催人奮進。
就在《復聯4》上映前兩周,《權力的游戲》最終季千呼萬喚始出來。同為系列的收官之作,《權力的游戲》最終季在播出前也是聚合了巨大的關注度。系列劇集因為故事體量較之于系列電影更大,其季與季之間的間隔也較之于系列電影單片之間更短,因此往往會令觀眾留下更加深刻的記憶,對觀眾通常也會有更大的黏性。但這次《權力的游戲》最終季與《復聯4》的同期“對撞”,后者在觀眾關注度和票房直接反映的消費者數量上顯然遠遠勝于前者,從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大銀幕對小屏幕的一次勝利。
包括好萊塢在內,以電視和流媒體為代表的小屏幕已成為觀眾更加青睞的內容載體,同時由于小屏幕幾乎可以貼身于觀眾因此又更加適合劇集類內容的生產——從好萊塢越來越多一線電影導演和一線電影演員投身小屏幕劇集,即可看出流媒體這一顯著的優勢。中國市場亦如是,流媒體的發行窗口正在不斷前壓院線窗口,此消彼長之間正是后者吸引力減弱、市場龍頭地位消減的清楚顯示。對于電影人來說,這還是相當令人憂傷的。
回過頭來說,《復聯4》為什么能在一周內創造出幾千萬人次的觀影熱潮,除了故事本身在11年的長線敘事下的黏性,其對大銀幕視聽技術的最大化利用是其吸引力的關鍵所在。《復聯4》乃至整個從《鋼鐵俠》開始的“漫威宇宙”均是在以當時最大可能的視效技術去展現大銀幕的魅力,這點也代表了好萊塢對電影的某種價值觀——好萊塢眾多導演都對前沿制作技術很有追逐熱情和挑戰欲望,不管是羅素兄弟、溫子仁、諾蘭、阿方索,還是卡梅隆、彼得·杰克遜,或是飽受詬病的邁克爾·貝,他們都是技術癡迷者,他們都像是電影世界的“極客”。
這也是為什么即便今天《復聯4》所獲得的堪稱贏家通吃的市場“統治力”,對于中國電影人而言仍有顯著的積極意義——與《流浪地球》在春節檔殺出重圍的成功有著某種相似的“興奮點”。
中國電影也在迎來“極客”一代,郭帆、烏爾善、韓延、許誠毅、韓寒……不同于過去中國導演普遍對成為“大師”的向往,這些年輕的“極客”導演更有工匠精神,對技術、工藝的興趣乃至信仰更甚于眾多前輩對作品里熔鑄知識分子智慧的迷戀。這可能是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之后最為顯著的對創作者的改變。
過去中國導演深受歐洲電影價值觀的洗禮,不論是“作者電影”還是大師崇拜,都成為中國電影很長一段時間的底色。正在變化的年輕一代導演以及很多技術崗位上的創作者,正在給中國電影注入新的可能。特別是在工業化升級的進程里,他們正在形成的集體性力量和因此獲得的觀眾追捧,是中國電影在整個全球電影面臨劇變和挑戰的時候,仍然葆有生命力和創新力的原因所在。
當然,對于什么是電影、什么更適合大銀幕的價值觀,答案并非止于一種;但對于6萬塊銀幕所依托的電影產業來說,更多追逐視聽技術、銀幕奇觀的創作者,更有可能讓中國電影產業在未來有更多的《流浪地球》《動物世界》《捉妖記》,甚至可期某種中國文化“宇宙”的宏大系列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