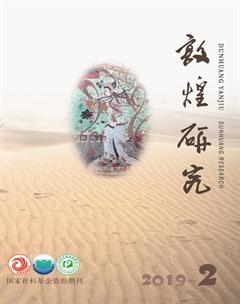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中亞宗教類繪畫
金惠媛 田婧 李貴貞
內容摘要:梳理了大谷光瑞收集品的轉移、散落過程,指出早期研究因出土地混亂而缺乏可信度,后經學者對《西域考古圖譜》的對照研究,對部分藏品的出土地和主題進行了補充和界定,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大谷光瑞;收集品;二樂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西域考古圖譜》
中圖分類號:K8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9)02-0085-09
The Central Asian Religious Painting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On the Background, Research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ion
KIM Hye-won1 Trans., TIAN Jing2 Rev., LEE Kwi Jeong3
(1.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South Korea;
2. Gansu Hongwen Dunhuang Art Training Center,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6200;
3.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US 10027)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how the ?魶tani collection was transferred to various museums and countries and eventually became scattered, and shows that early research on various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may lack credibility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By comparing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is collection with those not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Atla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cholars have clarified the exact sites where some items were excavated, in some cases analyzing the themes depicted in the art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historical accuracy and cataloguing.
Keywords: ?魶tani Kōzui; Collection; Nirakuso;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Archaeological Atla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引言: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
中亞文物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了一批大谷光瑞收集品。這些收集品是大谷光瑞于20世紀初組織探險隊所收集的。大谷光瑞是位于京都凈土真宗西本愿寺的住持。從佛教的角度看,中亞吸引了早期開始活動的歐洲探險隊和大谷光瑞探險隊的關注。《西域考古圖譜》的序文對大谷光瑞的目標有所敘述,由此文可以看出,探險隊最大的目的是闡明佛教東漸的路徑,尋找當時中國求法僧去印度的蹤跡,解決佛教史的各種疑問等。于是,通過收集中亞遺留下的佛經、佛像、佛具等,為佛教的教義和考古學的研究提供材料,可能的話將進一步解決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上的各種問題[1]。
大谷光瑞探險隊在中國新疆境內開展的調查一共有三次,分別是在1902—1903年、1908—1909年、1910—1914年?譹?訛。第一次參加探險的隊員是渡邊哲信(1874—1957)和堀賢雄(1880—1949);第二次參加探險的隊員是野村榮三郎(1880—1936)和橘瑞超(1890—1968);第三次參加探險的隊員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5)。他們根據大谷光瑞詳細的標識進行了調查,在新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譺?訛,同時大谷光瑞及其他成員還對印度、土耳其、蒙古等其他中亞地區進行了調查?譻?訛。因此大谷光瑞的收集品中除了新疆地區的文物,還包含其他地區的文物。
與其他中亞探險隊相同的是,大谷光瑞探險隊在這些收集品被轉移到日本以后,對收集品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展示、出版等?譼?訛。從第一次探險開始,對文物的研究就以京都大學的學者為主。大多數的研究由松本文三郎(1889——1944)、羽田亨(1882——1955)兩位佛教學家和歷史學家來完成,少數部分由專攻考古學和美術學的濱田耕作、瀧精一參加完成[1-2]。這批文物聞名世界,其中以1915年發行的《西域考古圖譜》上下卷為代表。其中一部分文物在之前發表的文章中就有所介紹。濱田耕作在1906年的論文中,對第一次探險時在于闐和庫木土喇出土的佛像、克孜爾出土的壁畫,從美術史的意義方面做了介紹[3]。另外,瀧精一在1910年的論文中也介紹過第二次探險出土的土峪溝佛畫[4]。大谷光瑞探險隊將二樂莊作為活動基地和文物保管地,同時,文物研究和展示也是在這里進行的。二樂莊是大谷光瑞在1908—1910年在神戶郊外六甲山腳下建造的別墅,在1932年毀于火災,現在只能通過圖片資料得知它的樣貌。參與別墅設計的伊東忠太是主張印度和日本建筑物一脈相承的《法隆寺建筑論》的作者,同時也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建筑家之一?譹?訛。橘瑞超首先對出土文物中的佛經進行了研究。凈土真宗的僧侶最關心的是中國關于凈土宗經典的翻譯,經過對新疆出土的佛經和《法華經》相關資料等進行整理后,1912—1913年相繼出版了《二樂叢書》四卷[5]。二樂莊中收藏了探險隊所收集的文物,也向公眾進行了公開展示?譺?訛。
除了收藏在二月莊以外,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正式展出的地方是京都恩賜博物館(現在的京都國立博物館)。這里寄存有一部分大谷光瑞的收集品。京都國立博物館中的中國庫車、和田及西安收集品共249件,其寄存時間為1924年2月1日至1944年3月25日[2]30。但是從濱田耕作和木下奎太郎的文章中所涉及的1906年和1910年前后出土的克孜爾壁畫殘片和庫木土喇等收集品可以得知,展示的記錄在先[3]332-334。
因此,大谷光瑞收集的文物流失在日本、中國、韓國的各個收藏地和個人手中,雖然關于文物流失的過程有很多不確定的部分,但是大概的情況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概括出來?譻?訛,并且,造成文物的大規模流失,是在1914年大谷光瑞從文酒職位上卸任之后。
1914年2月5日,西本源寺的僧人因挪用了寺院附屬財團的資金并且偽造瀆職貪污文件而入監京都監獄,同年5月對此負有責任的大谷光瑞被解除文酒職務[6]。從大谷光瑞卸任時,后任隊長吉川小一郎還在執行第三次探險隊調查的事實可以看出,當時的狀況很混亂。接著,11月大谷光瑞將據點搬至中國旅順,同時帶走了探險隊部分收集品中的藏書。后來,大谷光瑞又將據點重新搬到了上海,并且他將這部分帶來的中亞文物移交給關東廳博物館。根據最新資料顯示,關東廳博物館就是后來的旅順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共1714件,其中文獻110件,26433卷?譼?訛。關東廳博物館保管的文物中有600余件敦煌出土的經文。為了展出這部分文物,1950年先將它們轉移到了北京,后來就由北京圖書館進行保管,現在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另外,在1948年10月大谷光瑞去世后,整理文物時發現了兩個便于長距離運輸而制造的大箱子。這兩個箱子是為了方便運送經旅順至日本西本源寺的文物而特制的。箱子里面有大谷收集品中最有名的李白手稿及其他文書、佛經、繪畫等9000件文物[5]9-10[7]。這些文物后被捐贈給龍谷大學圖書館,成為目前龍谷大學所收藏的大谷收集品的主要部分。同時,這里還收藏了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探險隊隊員的個人收集品和相關照片?譽?訛。
大谷光瑞的其他收集品中,有一部分被收藏在京都恩賜博物館里?譾?訛。1944年3月,根據大谷家族的要求,京都恩賜博物館返還這部分收集品。后來,這部分收集品被木村貞造所擁有,再后來,日本的文化財產保護委員會重新將這部分收集品買回,并自1967年起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后來,京都國立博物館通過木村貞造重新買回國的文物,僅大谷光瑞的收集品,大概就有600件[6]18。這部分收集品除了收藏在日本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日本靜岡熱海岡田茂吉美術館外,還有少量收藏在個人手中?譹?訛。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二樂莊所剩余的文物,現在都收藏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大谷光瑞在向旅順轉移的時候將二樂莊托付給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管理,而九原房之助在1916年1月購買了二樂莊以及里面的文物?譺?訛。九原房之助是當時的政商,之后成為了商工大臣,他跟第一代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1852—1919)是同鄉,后來,他以捐贈的形式將自己買入的大谷光瑞收集品都贈給了寺內正毅。
此后,1916年4月至5月,二樂莊剩余的373件大谷光瑞收集品由神戶運往朝鮮的首都?譻?訛。這些收集品由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放在景福宮修正殿進行展示和保管。從當時的記錄、照片中可以看出,壁畫有30多件,都被固定在木制相框當中,每幅壁畫都分門別類地掛在墻上。還有一部分照片反映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3窟的《誓愿畫》和一些文物在展示時的情形。1945年朝鮮國立博物館建成后,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又將收藏的大谷光瑞收集品轉移到新的博物館進行了收藏[8]。
只有對大谷光瑞收集品的綜合研究完成后,才能了解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大谷光瑞收集品的全貌。但是從現在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學和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大部分大谷光瑞收集品與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收藏品相比較來看,都有缺少文獻資料這一突出的問題。由于先前對文物的整理和觀察都和文物流散的過程有關,因此為了展示、研究和遷移,在篩選文物的時候都應該優先考慮是否有文獻資料。
比如,京都大學的學者們剛開始研究這些文物時,所用的文獻主要是以專家所收集的文獻資料為主,他們最先對二樂莊藏橘瑞超所收集的佛經進行了研究。大谷光瑞將龍谷大學所收藏的文物轉移至旅順的時候,帶走了大部分的文獻資料,可以看出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所以導致了后來二樂莊剩余的文物中幾乎沒有文獻資料。
與文獻資料同樣受到關注的是,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收藏的部分大型壁畫?譼?訛。旅順博物館收藏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2幅壁畫,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了克孜爾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的多幅壁畫[2]。但是這些跟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收藏的壁畫數量相比,數量甚少,而且個別種類的文物形狀較小。
二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
中亞宗教繪畫的研究
大谷光瑞的收集品存在這種情況:同一批的出土文物,會在不同的機構分開保管。如英國斯坦因(1862—1943)探險隊收集的文物,由于當時探險資金由印度和英國政府提供,所以,文物就會分藏在這兩個國家的不同機構。后來,德國組織的吐魯番探險隊發現的文物除了在德國柏林亞洲美術館收藏之外,還收藏在美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很多機構中。勒柯克為了籌集出版大型圖冊的費用而出售的壁畫現在也被收藏在美國和日本的不同機構?譽?訛。
與上述幾種情況相比,大谷光瑞的收集品則是還未被系統整理,就被分散收藏了。在學術界,極少數的頂級文物是能夠被世人所關注的,除了需要對歷史片段的大量整理,還需要研究人員長時間的調查才能得以實現。如英國斯坦因探險隊收集的文物雖然也有惡劣遭遇的情況,但是它們被發現后,英國的博物館對文物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整理,進而出版了文物目錄集和相關研究報告[9]。大谷光瑞的收集品還沒有整理就被分散至各地,甚是遺憾。
對于大谷光瑞收集品的研究還有另一方面的困難,那就是與其他的文物收藏相比,缺少了對大谷光瑞收集品當時挖掘時和出土地的記錄資料[10-11]。大谷光瑞最初的探險隊隊員都是年輕的僧人,雖然他們了解佛教和漢語文獻方面的知識,但是缺少考古學知識和挖掘經驗。他們一邊做著研究,一邊制定第二天需要進行的事項,有的時候還需要對遺址的尺寸和圖樣進行記錄?譹?訛。但是跟格倫威德爾(1856—1935)的研究報告相比,大谷光瑞收集品在考古學、美術史方面和歷史風格的有效資料,顯得非常缺失。
這就造成了無法具體指出大谷光瑞收集品出土地的問題。這個問題是1940年作為個別文物的研究時才得到正式關注和研究的。主要是對大谷光瑞的收集品轉移前的資料做了一些研究。
最初關于介紹大谷光瑞收集品的《西域考古圖譜》共收錄了696件文物。雖然該書中寫到,對文物有所介紹的書,出版后會有計劃地對其進一步研究,但最終因為只能從書中了解到名稱、出土地和大概的年代而使得計劃擱淺。由于這本書是在文物向中國和韓國轉移前出版的,因此里面也包括了17幅收藏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宗教繪畫?譺?訛。由于很多研究材料與該書對文物出土地的描述有所出入,因此該書的可信度無法得到認可。但是關于繪畫出土地方面的信息卻是沒有什么錯誤的。
在1916—1945年,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出版了很多介紹其收藏中亞文物的書籍,其中有《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所藏西域文物圖集》(以下簡稱《圖片集》),《朝鮮古美術大觀》第三卷《京城總督府博物館》、《博物館陳列品圖鑒》和《世界美術全集》的相關內容。從1927年開始出版的10冊《圖片集》共收錄了100張中亞文物的照片?譻?訛,其中包括26件以宗教為主題的壁畫圖片和8件在布料或紙張上完成的繪畫作品圖片。雖然里面收錄了對繪畫整體和細節的圖片,但是一部分文物的細節圖片還缺少學術方面的研究資料。由于文物的材質、出土地等內容出現的錯誤,這部分資料很難成為嚴謹的文物研究基礎材料。
1930年出版的《朝鮮古美術大觀》第三卷中的圖25—82收錄的中亞文物照片中包括了23件壁畫圖片。與缺少基本文物資料的《圖片集》相比,《龍王槃達本生圖殘片》中的圖片明確了出土地。此外,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出版的《博物館陳列品圖鑒》第四卷(1933年)和第六卷(1934年)收錄了在布料和紙張上完成的繪畫作品各一件。1929年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也對部分文物的圖片做了簡略的說明[12]。
上面所提到的初期圖錄與圖片集,因對個別遺物的基本信息記錄不一致以及信息缺失而無法成為學術資料。但是,當時被選入書中出版的遺物,是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收藏的中亞代表性遺物。這些出版物也是研究人員在那個信息傳播閉塞的時期,唯一可以接觸和了解那些文物的資料[13-14]。這樣看來,以圖片的形式記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收藏的中亞文物的初期出版物,也具有一定的意義。
有些文物的正式研究從1940年才開始。其中對研究貢獻最大的就是專門研究日本繪畫的熊谷宣夫。他從1939年就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工作,1942年開始在《美術研究》上發表關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的文章起,到1960年陸續發表了20余篇關于中亞美術的文章?譹?訛。這些文章中涉及的文物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繪畫作品居多,其中又以對壁畫的研究成果最為矚目。
他的研究首先考慮的是對文物所屬地的研究。通過對格倫威德爾等歐洲的中亞探險隊的考古記錄進行詳細的研究,又以文物的樣式和較為表面的考察為基礎進行研究,復原了26件包括柏孜克里克、克孜爾和庫木土喇石窟文物的出土地。他的研究主張后來基本上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在日本,熊谷宣夫之后,專門研究中亞壁畫而出名的有上野秋和平野真完(曾用名村上真完)。他們在1950—1990年發表的著作中,對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文物的研究將中亞繪畫的理解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譺?訛,特別是平野真完在1961年和1984年發表的關于柏孜克里克佛教圖的文章中對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多幅佛教圖的研究觀點成為了日后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
從1970年開始,韓國國內研究者開始對該部分文物進行研究,其中以權永弼、安炳燦、閔炳勛等國立中央博物館出身的研究人員為主。權永弼是韓國中亞美術研究的奠基者,同時也為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中亞文物和其代表文物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15-16],另外,在前總督府遺址上建造的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品常設展覽開始時,擔任了《中亞美術》一書的編輯。《中亞美術》是國立中央博物館最早出版介紹中亞文物代表的文物圖冊,具有重大意義。共介紹了1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18幅壁畫和紙制、織物材質的繪畫7幅,共25幅宗教繪畫作品[17],其中還著重介紹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繪畫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佛教圖畫。雖然沒有對每個文物的圖片進行講解,但是介紹了熊谷宣夫關于文物出土地的研究[10]132-153。
安炳燦作為文物保管學界中后來的一代人,對個別的文物進行了集中研究,奠定了國內關于中亞壁畫研究的重要基礎。他經過對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尤其是數量最多的第15窟壁畫的考察和研究,在1990年發表了一篇文章[18]。文章以格倫威德爾的研究記錄和日本學者的研究為基礎,試圖復原第15窟的壁畫,從而對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文物有了一個更為立體的認識,而且文章中還重新闡明了壁畫的出土地。
專攻中亞歷史并對中亞文物進行研究的閔炳勛,在擴大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收藏的中亞文物的影響力和對文物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不僅關心中亞文物的收藏史和古墓中出土的文物,還關心壁畫的相關資料。1995年他對梅村坦收藏的柏孜克里克壁畫中的回鶻文題記進行了解讀,2000年還和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一起在文物保管學和美術學方面對東京國立博物館和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壁畫進行了研究[19-20]。另外,在2003年舉辦的“西域美術特別展”,向公眾介紹了300余件未公開文物的宗教文化、考古文化和生活文化方面的信息。這次展覽中,介紹了18件宗教繪畫,其中,部分文物的出土地也有了新的發現[21]。
2005年,由于原朝鮮總督府址的建筑被廢棄,從而中斷了中亞文物的常設展示,在龍山新建博物館的中亞館重新開館,在2006年舉辦了“從絲綢之路而來的千佛圖”主題展,作為專攻佛教美術史的我,通過這次機會對目前所介紹的“千佛圖”有了新的理解,這次展覽包括了以前未公開展示的3件文物和19幅壁畫,并對一部分的文物出土地做了新的界定[22]。
除此之外,林英愛作為韓國國內不多的中亞美術專家之一,主要致力于雕塑的研究,除此之外,還發表了關于幡及繪畫方面的研究成果[23]。另外,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中亞壁畫中,有關繪畫資料的研究占巨大比重。近來,世界上許多學者都在關注的柏孜克里克寺院畫研究,宋在熙、趙勝金等韓國研究者也都參與其中[24-25]。
三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
中亞宗教繪畫的現狀
目前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中亞宗教繪畫,實際數量是72件77幅(遺物登錄信息上的數量是72件76幅)。其中,壁畫有60件62幅,紙張或織物上面繪畫的作品有12件15幅。雖然紙張或織物繪畫作品的主題和出土地都得到了明確,但是部分壁畫的相關信息還是沒有把握。根據繪畫的內容可以推定,除了大部分以佛教為題材外,還有一幅是以摩尼教為主題的。
首先,從壁畫方面看,通過現有的研究發現了主題和出土遺址的有31件,其中一部分文物在相同的畫框中,只有一部分的壁畫殘片,但在編裝稿中也會被認定為1件。
《西域考古圖譜》對追加的7幅壁畫出土地提出了異議,并且重新確定了其中1幅繪畫的主題,是1件以“惡鬼像殘片”命名的壁畫,畫面中的惡鬼形象,與“火頭金剛像殘片”壁畫中火頭金剛形象的頭部、下半身樣式相似,并參考柏孜克里克第20窟中唐壁畫的材料,可以推斷出,這幅“惡鬼像殘片”壁畫,原來就應該是第15窟中唐壁畫的一部分。其余6件中的3件應該屬于雅兒湖石窟第4窟中的千佛圖殘片,可以明確的是已經確定為同一出土地的雅兒湖石窟佛像殘片,因樣式相似,應屬于同一石窟的文物。其他3件經確認,應屬于現存的庫木土喇千佛洞第16窟。
同時,通過對現有資料為基礎的研究和進一步科學的調查,對文物又提出了新的解釋。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窟的壁畫殘片,與其他壁畫不同的是,它的底色里帶有綠色(藍色)這一特征。通過對第15窟壁畫顏料的研究,確認出現在大部分變色的文物,原來的底色是綠色(藍色),所以在紙張或織物繪畫作品方面都可以確定大約的出土地和主題。
通過對現有資料里存在的爭議和其他博物館收藏的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從而對各個文物的認識又達到了新的高度。另外還對主要文物在文物保管學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之前一直以為土峪溝出土的3幅繪畫作品即《觀音菩薩圖》《菩薩圖》《繪畫圖片》是以麻料為原料的,而實際上全都是棉料。這與在吐魯番發現的很多棉制繪畫作品的情況可以匹配起來。另外,通過紅外線照片完成的圖片和草圖進行比較得出的差異可以看出現存的繪畫文物都有被拓印的痕跡。
從關于壁畫的出土地問題上繼續研究下去,會看到大量現有的從資料集提出的文物出土地與提供文物基本資料的《朝鮮總督府博館中亞挖掘文物目錄》(以下簡稱《目錄》)不一致的情況[26]。而《新西域記》下卷中所記錄的根據1916年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接收文物時的記錄推斷出的《陳列品納付書》與現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文物記錄的信息是一致的?譹?訛。
通過現有的研究指出《目錄》上記錄的信息有很多的錯誤[2]28[11]282[27]。當然在繪畫文物方面也會存在一定的錯誤。根據《目錄》中的記錄,屬于《須達拏王子本生圖殘片》《佛傳圖殘片》《本生圖和姻緣神話圖殘片》《銘文殘片》《千佛圖殘片》的這幾幅壁畫殘片,其中一部分的出土地都是吐魯番,而實際上《須達拏王子本生圖》出土地是米蘭第5寺院,《佛傳圖殘片》和《本生圖和姻緣神話殘片》出自克孜爾石窟的第219窟和第206窟,剩下的則出自于庫木土喇石窟。
有意思的是,雖然《目錄》上個別文物的信息跟現實研究有出入,但是《西域考古圖譜》上的內容卻有一定的可信度。也就是說,前面提到的《須達拏王子本生圖》等幾幅壁畫在《西域考古圖譜》中都正確記載了出土地。因此,雖然《西域考古圖譜》上的內容有一部分存在錯誤的情況,但是還是有必要像繪畫信息一樣,認真篩選里面的可用信息。
另一方面,和《目錄》相比較,《西域考古圖譜》在出土地方面有詳細的記載。比如說,《千佛圖殘片》在《目錄》中只是簡單地記載了出土地是“吐魯番”,而在《西域考古圖譜》中記載的是“雅兒湖”。還有,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佛教圖殘片》《涅槃殘片》《帷幕殘片》和《銘文殘片》在《目錄》上記載的出土地為吐魯番,而《西域考古圖譜》上記載的是“木頭溝”。
如果根據《西域考古圖譜》里記載的《銘文殘片》和《銘文殘片》出土地是木頭溝的情況來看,那這兩幅壁畫的出土地就有可能是柏孜克里克石窟。
同時,現在還有爭議而沒能具體認定其出土地的《壁畫殘片》,中后排左面起第一和第三幅在《西域考古圖譜》上記載的出土地是庫木土喇。但是從壁畫上人物的表現形式來看都與庫車地區壁畫的形式和樣式等特征相符合,因此對出土地的確認,有了更好的說服力。
通過對剩余的無法明確指出其土地的壁畫的初步觀察,《千佛圖殘片》和《千佛圖殘片》中的佛像類型,反復出現在中國式佛塔內安放的佛像中,在柏孜克里克第9窟也能看到同樣的樣式?譹?訛,而且與前面提到的可以認為出土地為柏孜克里克石窟的《題記殘片》相似。這些壁畫中題記和圖的上下部分都帶有不同的顏色,還有其他部分的圖案都跟柏孜克里克第16窟的窟頂壁畫非常相似?譺?訛。雖然這里反復說了很多,但是也有它的識別度?譻?訛。
從上面反映宗教繪畫出土地的信息來看,其中吐魯番出土的壁畫有53件56幅,占了大部分。明確出土地的以柏孜克里克壁畫最多。其中第15窟的壁畫有13件之多,甬道上畫的佛教圖殘片有9件,中唐壁畫有5件。此外,米蘭地區的壁畫有1件1幅,庫車地區的壁畫有8件10幅。紙張和織物作畫的作品有2件5幅出自吐峪溝,剩下的10件10幅出自敦煌。
結束語
通過以上對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的中亞宗教繪畫文物的觀察,首先是對大谷光瑞收集品的收藏和分散過程進行了介紹,大型壁畫從開始到最后被留存在二樂莊,從而說明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收藏的壁畫,大部分是由大谷光瑞收集的,接著,主要是對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的中亞宗教繪畫在研究上的歷史成果進行了介紹。最后,對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的中亞宗教繪畫目前的大概數量、地區分布、出土地和繪畫主題進行了側面討論,就現存的研究成果對《西域考古圖譜》和《目錄》里關于文物的信息進行了比較。同時,也對沒有明確出土地的文物進行了初步的觀察,并對文物保管科學方面的主要成果進行了論證。以這樣的研究為基礎,期待以后對個別文物能有進一步的研究。
附記:此文原發表于2013年4月30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出版的《國立中央博物館藏中亞宗教繪畫》。
參考文獻:
[1]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上卷[M].東京:國崋社,1915:3-4.
[2]杉山二郎.大谷探検隊による西域調査の意義と成果[M]//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1:9-37.
[3]濱田耕作.希臘印度仏教蕓術の東漸について[J].國華,1906,192:304-307.
[4]瀧精一.新疆の発掘[J].國華,1911,257:93-96.
[5]入澤崇.龍谷大學と西域學[M]//旅順博物館展——龍谷大學所藏西域文化資料.旅順博物館展實行委員會,2007:7-21.
[6]臺信祐爾.大谷光瑞と西域美術[M].日本の美術,東京:至文堂,2002:94-95.
[7]三谷眞澄.佛教の來た道ーシルクロードの探検の旅[M].京都:龍谷大學ミュジアム,讀賣新聞社,2012:190-199.
[8]國立中央博物館60年(1945—2005)[M].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2006:25-26.
[9]Susan Whitfield.Aurel Stein: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Indian Office[M]//The Silk Road:Trade,Travel,War and Faith.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2004:91-96.
[10]權永弼.中亞美術之普遍性與特殊性[M]//中亞美術.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1986:132-153.
[11]閔炳勛.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亞遺物的收藏、轉移經過及展示、調查研究現狀[M]//西域美術特別展圖錄.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03:249-272.
[12]下中彌三郎.世界美術全集:第9卷[M].東京:平凡社,1929:38,40.
[13]熊谷宣夫.クチャ將來の彩畫舎利容器[J].美術研究.1957,191:256-257,260-262.
[14]熊谷宣夫.西域の美術[M]//西域文化研究:第五:中央アジア佛教美術.京都:法藏館,1962:31-170.
[15]權永弼.中央亞細亞壁畫考: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壁畫其關系[J].美術資料,1977,20:10-23.
[16]Kwon.The Otani collection[J].Orientations,1989,
20(3):53-63.
[17]國立中央博物館.中亞美術[M].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1986.
[18]安炳燦.柏孜克里克第4號窟誓愿畫的復原[J].美術資料,1990,46:69-100.
[19]閔丙勛,梅村坦.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柏孜克里克壁畫維吾爾銘文試釋[J].美術資料,1955,55:119-155.
[20]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大谷探検隊將來西域壁畫の保存修復に関する綜合研究[M].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05.
[21]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國立中央美術館收藏西域美術[M].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2003:282-287.
[22]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國立中央博物館60年(1945—2005)[M].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2006.
[23]任英愛.古代中國佛教幡的樣式變遷考[J].美術史學研究,1991,189:69-109.
[24]鄭在勛.維吾爾摩尼教的收容與之性質[J].歷史學報,2000,168:151-187.
[25]趙成琴.維吾爾人們的成佛誓愿:柏孜克里克第20窟《毗奈耶藥事變相圖》[J].中亞研究,2012,17(2):101-122.
[26]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記:下卷[M].東京:有光社,1937:3-10.
[27]任英愛.西域佛教雕刻史[M].日志社,1996:235-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