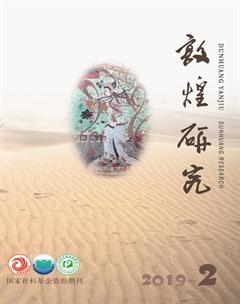敦煌變文詞語零拾
鄧文寬
內容摘要:敦煌變文是敦煌文學的大宗,其研究價值極為廣泛,諸如俗講、文字、語言、佛經和歷史故事的傳播形式等多個層面,都有取之不盡的寶藏。不過,盡管相關研究成果頗豐,但要深入研究的內容依然不少。作者就一些學者們尚未校訂或理解存在偏差的案例,進行了釋讀。
關鍵詞:敦煌變文;敦煌文學;方音;方言
中圖分類號:G256.1;H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9)02-0094-08
Reinterpreting Some Words from Dunhuang
Popular Literature
DENG Wenkua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Popular literature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Dunhuang documents and has extensive research value, including writing containing colloquial speeches, common script and speech, and Buddhist lectures and historical stories written in a form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propagation. Despite of the abundanc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some of these topics, there remains a vast quantity of written material that has yet to be studied in depth. This paper interprets some words from Dunhuang popular literature that have not been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findings or that have been misinterpreted.
Keywords: Dunhuang popular literature; Dunhuang literature; local accent; dialec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變文是敦煌文學的大宗,其研究價值極為廣泛,諸如俗講、文字、語言、佛經和歷史故事的傳播形式等多個層面,都有取之不盡的寶藏。也因此,它就特別吸引敦煌學大家們的眼球,并成為一批后起之秀深挖探寶的淵藪。現如今,可以說是作品層出,成果豐碩。誠然,學術研究沒有止境,需要深入下去的地方依然不少。我在閱讀中,發現了一些學者們尚未校訂或理解存在偏差的案例,故不揣外行和谫陋,繼續貢獻綿薄之力。
這里需加說明是,我在校理和解釋一些詞語時,較多地依靠了華北尤其是西北地區的方言和方音。因為如果不了解某一字的方音讀法,就無法找到與之對應的方音替代字,從而給予正確校理和釋義。事實證明,在校釋敦煌文獻時,僅僅依靠傳統校勘學的方法是不夠的,必須引入方音、方言作為工具,才有可能將一些疑難問題予以破解。而在所據方言和方音之中,我又較多地依靠了山西方言,這在學理上也是成立的。那位因殺豬而成為名人的北大校友陸步軒先生,曾經就讀于北大中文系,他在《北大“屠夫”》一書中說:“由于大山阻隔,溝壑縱橫,延緩了語言的交融與發展,因而山西方言被認為是最古樸,保存古音、古義最完整的北方語言。1987年夏,我們漢85級與漢84級一道,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赴山西呂梁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調研。”[1]這說明對山西方言和方音價值的認識,并非出自陸步軒先生的個人見解,而是北大中文系語言學家們的共識。而我這個來自山西稷山縣的土包子(或者叫農民也可),祖祖輩輩就住在呂梁山前沿的黃華峪口,那里也是我出生和度過少年時代的地方,從而對當地方音和方言俚語比較熟悉,使用起來相對自如。我相信,隨著對這些方音和方言俚語認識的逐步提高,對于相關文本的產生和流傳,我們也將獲得更加深刻的認識。
言歸正傳。
(1)趁趃。《張議潮變文》:“仆射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鏨兇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行經一千里已來,直到退渾國內,方始趁趃。仆射即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鼉,縱八陣,騁英雄,兵分兩道,裹合四邊。”這段文字,黃征、張涌泉二位教授的《敦煌變文校注》(下稱《校注》)[2]、項楚教授的《敦煌變文選注》(下稱《選注》)[3]全同,僅個別標點斷句有異。文中的“趁趃”一詞,《校注》云:“義為追趕。蔣禮鴻云:‘這是說方才追上……趁趃就是趁迭的俗寫。按:《玉篇·走部》:‘趃,徒結切。大走也。又夷質切。故‘趃字非俗。”[2]183《選注》則云:“同‘趁迭,趕上,追及。”[3]313陳秀蘭博士《敦煌變文詞匯研究》(下稱《研究》)[4]云:“(1)追趕。(2)聲音相應和。”[4]28第二義與本文無關,這里不予討論。而第一義“追趕”顯然是接受了《校注》的見解。可以說,對這個詞的理解學者們存在著分歧:《選注》和蔣禮鴻先生主“追上”說,《校注》和《研究》主“追趕”說 。很明顯,“追上”和“追趕”意義有別:“追趕”是指追的過程,“追上”則指追的終止。我們結合上下文字進行對照:原文說“直到退渾國內,方始趁趃”。若解作“追趕”,則是說張議潮和他的兵馬追了一千多里,“直到退渾國內,方始追趕”。這說得通嗎?顯然作“方始追上”才是。由于追上了,以下才是仆射如何排兵布陣。正在追趕的過程中,怕也不能排兵布陣吧?從文字上說,這里“趃”字當校作“迭”。《朱子語類》卷72:“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迭”即“及”“夠”義[5]。若此,上下文義就不再捍格了。
(2)惡紹。《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有一類門徒弟子,為人去就乖疏。不修仁義五常,不管溫良恭儉。抄手有時忘卻,萬福故是隔生。齋場上謝座早從,吊孝有時失笑……產業莊園折損盡,慵懶惡紹豈成人。”[2]975末句“惡紹”一詞,《校注》云:“蔣禮鴻疑‘惡紹是說不能好好承繼父祖的家業,近是。”在同書第791頁,又有一次解釋云:“沒出息,學壞。”《選注》是這樣解釋的:“品行惡劣。敦煌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沒尊卑,少尊敬,我慢貢高今古映。仿習兇粗惡紹名,不歸禮樂謙貢令。友生劉長東見告:現今四川三臺縣方言,仍將行為不端稱為‘惡紹。即唐五代俗語遺存至今者。”[3]1488-1489《研究》則解作“脾氣壞”[4]39。
依據寫本上下文意,“惡紹”是個貶義詞,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具體如何貶,諸家認識卻很有差異。其中認為是“脾氣壞”者,不知依據為何?至于認為“是說不能好好承繼父祖的家業”,怕是依據上下文意進行概括而成的認識。這兩種說法,均距其本來意義相去較遠。《校注》認為是“沒出息,學壞”,《選注》認為是“品行惡劣”,都是極近似的解釋。這個詞,迄今仍存在于晉、陜及關中一代的方言里。朱正義教授《關中方言古詞論稿》列有“惡躁”一詞,當是“惡紹”的異寫。其釋義云:“元雜劇《黃粱夢》第三折,[白]‘天嚛 !這雪住一住可也好,越下的惡躁了!(‘ 嚛,‘喲 )‘惡躁,厲害、兇猛的意思。關中至今還有這種說法,其中‘躁音‘驗……”[6]這個詞在我原籍山西稷山縣民間也存在。如有幾個年輕人結幫去干了一件接近違法的事情,他人閑議時便會說:“■(那)幾個娃真惡紹。”又比如,連續許多天不下雨,老百姓也可以說:“天旱得惡紹的。”這些話都有厲害、過分的意思。補充這些,供語言學者們進一步研究參考。
(3)承領。《伍子胥變文》:“子胥得食吃足,心自思維:‘凡人“得他一食,慚人一色;得人兩食,為他著力”。懷中璧玉以贈。船人畏暮貪錢,與物不相承領。”[2]8末句之“承領”,《研究》解作“答理”[4]29,同時引《漢語大詞典》(下稱《漢大》)所舉元無名氏《氣英布》第二折作證:“哎!隨何也!你怎么不言語,不承領?從今后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如果“承領”是“答理”義,那么,所引《氣英布》末句便是:“你怎么不言語,不答理?”難道“言語”不就是“答理”么?所以這無法通文。其實,在上面所引變文之后幾句便有:“子胥見人不受,情中漸覺不安。”可知,這個“承領”是接受之意。《氣英布》中的“承領”與此義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有句“祇對語言宜款曲,領承教示要參詳”,《研究》即釋“領承”為“接受”[4]72。我覺得,“領承”就是“承領”的倒文,但意思相同,不宜做不同理解。
(4)冒懆。《降魔變文》:“是日六師漸冒懆,忿恨罔知無[口](計)校。雖然打強且祇敵,終將懸知自須倒。”[2]566首句之“冒懆”,《選注》釋曰:“就是毷氉,煩悶。《唐國史補》卷下:‘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3]750“冒懆”這個詞,在今日晉、陜方言里依舊存在。景爾強《關中方言詞語匯釋》曰:“煩惱,關中方言詞中‘氉讀‘cao,系疊韻的音轉。如說‘久雨不晴,人心里毷氉得很。還可以重疊,如說‘他毷毷氉氉的,心中像有什么事等。”[7]在我原籍山西稷山縣,此詞讀音、意義與關中方言全同。如一個商易人因買賣不順而煩躁不安,別人問起時,家里人便說:“商易不順,他心里冒懆的。”再回到前引《降魔變文》“六師漸冒懆”一句,亦即軍隊情緒逐漸變得煩亂不安,氣不忿,才有下句“忿恨罔知無計校”,即憋著氣但又不知如何去做,出這口惡氣。
(5)穴白。《燕子賦》(一):“乃有黃雀,頭腦竣削。倚街旁巷,為強凌弱。睹燕不在,入來皎(挍)掠。見他宅舍鮮凈,即便宂白占著。婦兒男女,共為歡樂。”[2]376句中“宂白”,《選注》釋作“兀自”[3]488。《校注》在注釋“宂白”時云:“甲卷(伯二四九一)字作‘宂白,乙卷(伯三六六六)同,丙卷(伯三七五七)作‘宂自。‘宂即‘穴之常見俗字,‘自為‘白之形訛。唐五代時未見‘兀自一詞之用例……故‘穴白作‘鉆空子,引申為‘乘機。”[2]383《研究》同樣釋作“乘機”[4]122,知其亦本自《校注》。我們知道,敦煌文獻中“白”“自”二字常因形變而混用。愚意以為,此處當以“自”字為是。但“自”亦非其本字,而是“恣”之同音借字。關鍵是那個“宂”字,無論組成“穴白”或“穴自”,都難通文意。《校注》引用了P.3633《沙州百姓一萬人上回鶻天可汗書》中的一段文字:“且太保(按,指張議潮)棄蕃歸化,當爾之時,見有吐蕃節兒鎮守沙州。太保見南蕃離亂,乘勢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趁卻節兒,卻著漢家衣冠,永拋蕃丑。”我注意到,在“穴白趁卻節兒”一句之前,已有“乘勢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一句。若“穴白”乃“乘機”之意,那么與上句“乘勢”云云有何區別?顯然是說不通的。我們需要尋求新解。在我的家鄉山西稷山縣,“橫”字可讀作“穴”。比如一個人長得人高馬大,民間在議論他(她)時會說:“■(那)人橫(音穴)有順(指上下)有的。”若此,這個“穴自”就當讀作“橫恣”,指態度堅決,帶幾份橫霸之氣,不容商量。對于黃雀來說,它強占燕巢,態度蠻橫,不講道理,所以這篇《燕子賦》下文才有“鳳凰云:‘燕子下牒,辭理懇切,雀兒豪橫,不可稱說。”[2]376這個“豪橫”與“橫恣”義近,都有蠻橫、不講理的意味。用在太保張議潮身上,他當年趕走吐蕃節兒時,態度也是十分堅決,強行棄蕃歸漢,“橫恣”在這里就是對他的褒獎之詞了。至于說該卷中為何有“穴”字又有“橫”字,同存并用,這就牽扯到文本的形成與流傳了。是否存在著對寫本的回改而又改之不盡呢?恐怕一時還難以說清。
(6)功課。《秋胡變文》:“其母聞兒此語,喚言秋胡:‘……汝今得貴,不是汝學問勤勞,是我孝順新婦功課。使人往詣桑林中,喚其新婦。”[2]235《選注》文字亦同[3]384。句中“功課”一詞兩書皆失校,當校作“功果”。方言里“課”“果”二字皆讀作kuo。在我家鄉山西稷山縣,上課、課本、課堂、課桌、辦事果利(果斷利索義)等,均讀這個音,故寫本以“課”代“果”,當進行校改。至于其意義,《研究》釋作“功勞”[4]149,當是。“功果”除了指功勞和功德外,也可以是一個中性詞,指功效或結果,可以是正面的,如功勞;也可以是反面的,如罪錯。如某位鄰居出了一件倒霉事,隔壁人可能會幸災樂禍地說:“那是他平時不好好做人的功果。”這在民間口語里是常常能夠聽到的。回到《秋胡變文》,此處的“功果”顯然指“功勞”,是婆婆對媳婦的肯定之詞。
(7)交期。《廬山遠公話》:“死苦者,四大亦將歸滅,魂魄逐風摧[摧],兄弟長辭,爺孃永隔,妻兒男女,無由再會。交期朋友往還,一別無由再見。”[2]260句中“交期”一詞,《選注》同[3]1869,均失校,當作“交契”,寫本“期”乃“契”之同音借字。《漢大》給“交契”列出兩個義項:“(1)交情,情誼。唐王勃《與契苾將軍書》:‘仆與此公,早投交契,夷險之際,始終如一。(2)朋友。元馬致遠《薦福碑》第四折:‘倒招了女嬌娃結眷姻,和你這老禪師為交契。”[8]至于其意義,《研究》釋“交期”為朋友[4]153,當本《校注》和《選注》而來。再看寫本原文是“交期朋友往還”。愚意以為,既已言及朋友,則此處擬作“交契”為勝,指有交情的人。雖然有交情之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但卻與陌生人不同,故死后也就“無由再見”了。
(8)連臂。《張議潮變文》附錄二:“孤猿被禁歲年深,放出城南百尺林。淥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休作斷長(腸)吟。”[2]182此件《選注》未收。第三句“連臂”一詞,《校注》從原文,未改。《研究》釋作“多次”[4]156。按,《校注》失校,當作“連杯”,“臂”乃“杯”之同音借字。《漢大》釋“連杯”曰:“一杯接一杯。北周·虞信《見游春人》:‘連杯勸上馬,亂菓擲行車。”[5]856至于“連臂”,卻是另一個意思。《漢大》釋義云:“手攙手,臂挽臂。舊題漢·伶玄《趙飛燕外傳》:‘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北周虞信《北園射堂新成》詩:‘驚心一燕落,連臂兩猿騰。”[5]873均可參考。
(9)曾寒。《葉凈能詩》:“皇帝便詔凈能,奉詔至殿前。皇帝賜上殿,便言大內有妖[鼓]之聲。凈能奉進止,除妖鼓之聲。索水一椀,對皇帝前便噀之作法,水亦(一)離口,云霧斗暗,化作大蛇,便入地道。眼如懸鏡,口若血盆,毒氣成云,五百人悉皆作曾寒災聲,不敢打鼓。”[2]336《選注》釋文亦同[3]447。“五百人悉皆作曾寒災聲”的“曾寒”一詞,《研究》云“義待考”[4]133,持審慎態度。《校注》則云:“曾,張鴻勛校作‘噤。按,‘曾未見通‘噤之例,恐未確,疑通‘憎。災聲,唱禍聲。”[2]349《選注》云:“曾寒災聲:疑‘曾當作‘增,‘曾寒災聲指寒戰之聲,《翻譯名義集》卷2《地獄篇》:‘頞哳吒嚯嚯婆虎婆婆條:‘義府云:以寒增甚,口不得開,但得動舌,作哳吒之聲,此三約受苦以立名。以其為地獄受苦之聲,故稱‘災聲。”[3]449無論是校“曾”為“憎,”還是校“曾”為“增”,都尚未將變文此處的真實用意講出來。我們知道,唐五代河西方音有“韻母青齊互注”現象。故“曾”(ceng)字失去ng尾,就讀作ce,恰與“著”字的方音相同。進而可知,“曾寒”就是“著寒”也,也就是受寒之意。人們在受寒(或患感冒癥)時,就會渾身哆嗦,以致牙關打顫,氣不成聲,言難成語。正由于此,那五百個鼓手受了大蛇的驚嚇后,才“不敢打鼓”,只怕是想打也打不成了。我想,這樣校理或許才能觸及寫本此處的真實用意。
(10)油瘡。《捉季布傳文》:“皇帝聞言情大悅:‘勞卿忠諫奏來頻!朕緣爭位遭傷中,遍體油瘡是箭痕。夢見楚家猶戰酌,況憂季布動乾坤。”[2]98《選注》釋“油瘡”云:“傷疤。按‘瘡通‘創,謂創傷。《正法念處經》卷6:‘如是利刀,先割其肉,次斷其筋,次割其骨,次割其脈,次割其髓,遍體作瘡。”[3]245《研究》釋作“傷痕”[4]129。而對其中的“油”字,諸家均失校。按,“油”當校作“疣”,“油”乃“疣”之同音借字。《漢大》釋“疣瘡”云:“疣子。唐白居易《和〈李勢女〉》:‘忍將先人體,與主作疣瘡?妾死主意快,從此兩無妨。”[9]而“疣”原本就是指皮膚上的肉瘤。變文此處是說,由于身上多處中箭,肉瘤也就成了箭傷的痕跡。
(11)了事。《降魔變文》:“(須達多)當日處分家中,遂使開其庫藏,取黃金千兩,白玉數環,軟錦輕羅,千張萬匹,百頭壯象,當日登途:‘君須了事,向前星夜不宜遲滯。以得為限,莫惜資財。但稱吾子之心,回日重加賞賜!”[2]553除將“向前”上屬外,《選注》文字相同[3]653。至于“了事”,《校注》未釋,而《選注》則云:“能干,這里是努力的意思。”[3]656在《選注》的另一處,作者又釋“了事”曰:“能干。《太平廣記》卷275《上清》(出《異聞集》):‘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后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3]441今按,“了”字義即明白、清晰。今有“明了”一詞,當是同義復詞。“事”指事情、事理。故,“了事”原意是指頭腦清楚,明白事理。《漢大》釋義曰:“明白事理,精明能干。《南史·蔡樽傳》:‘卿殊不了事。《資治通鑒·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胡三省注:‘了事,猶言曉事也”[10]至于《選注》所引《太平廣記》的故事,上清之所以被唐德宗李適稱贊“大了事”,是由于他“善應對,能煎茶”。從這六個字實在看不出他的能干來。“能煎茶”意思明顯,姑且不論;“善應對”恐怕是指他善于回答唐德宗的問話,說出的道理令其信服,可皇上的心意。所以,將“大了事”理解為“很明事理”或許更妥當一些。《研究》釋“了事”為“努力”[4]157,亦當本自《選注》。回到《降魔變文》,“君須了事”意即“你要明白”,當是叮囑之詞,這樣理解或許更切情理。
(12)遭遭■■。《漢將王陵變》:“項羽帳中盛寢之次,不覺精神恍惚,神思不安,■然驚覺,遍體流汗。人是六十萬之人,營是五花之營,遭遭■■,愇愇惶惶,令(冷)人肝膽,奪人眼光。項羽遂乃高喝……”[2]67句中的“遭遭■■”,《校注》曰:“……項楚校‘■為‘ 簇,釋曰‘遭遭■■,形容密集的樣子,亦恐未確。據上下文意,此句當用以形容項羽神思不安貌。”[2]77查《選注》原校注曰:“原文‘■當作‘簇,遭遭■■,形容密集眾多。”[3]152味變文上下文意,將“遭遭■■,愇愇惶惶”理解成“用以形容項羽神思不安貌”怕是不確。這八個字是緊隨“人是六十萬之人,營是五花之營”出現的。《選注》理解為“形容密集眾多”是成立的。六十萬人還不是密集眾多嗎?這樣龐大的隊伍,加之排為“五花之營”,足以“冷人肝膽,奪人眼光”。愚意以為,《選注》校“■”為“簇”是正確的,但“遭”字當校作“曹”。“簇”字義即“群”,“曹”字義亦“群”,曹曹即群集、成群也。《左轉·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晉杜預注:“曹,群也。”有趣的是,“曹”字這一古義在我家鄉民間依舊在用。如說“這一曹(群)人”;“那家人過不好,是因懶干屬成曹(群)了”。
(13)叉夢、一圣。《太子成道經》:“大王共夫人發愿已訖,回鸞(鑾)駕卻入宮中。或于一日,便上彩云樓上,謀(迷)悶之次,便乃睡著,作一叉夢。忽然驚覺,遍體流汗。遂奏大王,具說上事:‘賤妾彩云樓上作一圣夢,夢見從天降下日輪(下略)。”[2]436《校注》釋云:“‘叉夢下文云‘圣夢,皆即奇異之夢。”[2]449《研究》釋“圣夢”為“吉祥之夢”[4]100。先說“叉夢”。此“叉”當是“詫”之同音借字,即稀奇、罕見之意。《漢大》釋曰:“驚詫、詫異。《新唐書·戴至德傳》:‘閱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11]我原籍民間常常說“稀詫”,“詫”亦“稀”義,均指少見、奇特,故而“詫夢”便是奇夢、少見之夢。再說“圣夢”。此處當讀作“一圣夢”,不宜將“圣夢”當作一個詞去作解。“一圣”即“一晌”,“圣”乃“晌”之音近借字。“一晌”就是一會兒、片刻,指不太長的時間。南唐李煜《浪淘沙詞》:“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玩。”元王實甫《西廂記》:“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一晌”“半晌”今日仍是方言常用語。由此可知。“作一圣(晌)夢”就是做了一會兒夢之意。
(14)依官葉勢。《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次請十方佛為作證明。弟子某甲等合道場人,無始以來,造諸惡業:(中略)毀罵僧尼,用三寶物,依官葉勢,驅逼僧尼,劫奪田水(下略)。”[2]680文中“依官葉勢”之“葉”,《校注》釋云:“徐校:‘葉同‘挾。按‘葉‘挾音近通用。”[2]692《選注》則曰:“依官葉勢:倚仗官勢……‘葉通作‘挾,亦仗恃之義,《孟子·萬章下》:‘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3]1229-1230筆者與諸位大家理解稍異。愚意以為,這里的“葉”字是一個口語詞,是“仰”字的方言讀音。在我原籍山西稷山縣,民間常說:“你自家的事情自家做,你仰(音nie)人家誰呢!”父母責怪幾個子女不孝時也會說:“誰都仰不著。”“仰”即依賴、依靠義。《管子·君臣上》:“夫為人君者,蔭德于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故此,“依官仰勢”就是依官仗勢,似不必尋求別解。這樣,就當將“依官葉勢”校作“依官仰勢”。
(15)商宜。《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于是大王(中略)正念思維,非分憂惶,忸怩反側。今若休罷禮拜,伏恐先愿有違;若乃頂謁參承,力劣不能來往。即朝大臣眷屬,穩便商宜,中內有一智臣,出來白王一計。”[2]1082《校注》釋“商宜”曰:“呂叔湘讀作‘商議,是。”[2]1087這個解釋甚為允當。今再補充如下:在山西稷山縣,“主義”說成“主宜”,“主意”也是“主宜”,“商議”說成“商宜”也就順理成章。可知,這里的“宜”字乃“議”的方音替代字,呂校甚是。《漢大》不僅未作校理,且以“商宜”設詞條進行解釋,并用上引敦煌變文的文字作為書證[8]372,這就未免不達一間了。
(16)一向。《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母子相見處:……口里千回拔出舌,兇(胸)前百過鐵犁耕。骨節筋皮隨處斷,不勞刀劍自彫(凋)零。一向須臾千過死,于是唱道卻迴生。入此獄中同受苦,不論貴賤與公卿。”[2]1033文中“一向”一詞,《校注》和《選注》均未作解釋,《研究》釋作“暫時”[4]171,恐未確。原文是“一向須臾千過死”,須臾即片刻、短時間。如果此處的“一向”是“暫時”義,那么全句就是“暫時片刻千過死”,能這么講嗎?看來此處將“一向”解作“一直”為宜。《漢大》解作“一直”,并引《朱子語類》卷120:“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10]30今日口語有“一向都是”如何,也是“一直”之義,或曰“一直以來”,表示一種常情或常態,與本文此處用法相似。
(17)結綰。《捉季布傳文》:“朱解問其周氏曰:‘有何能德值千金?周氏便■身上藝:‘……若說乘騎能結綰,曾向莊頭牧馬群。”[2]95《研究》列出“結綰”一詞,并云“義待考”[4]61。《選注》釋曰:“結綰,編織打結。按乘騎之事,常與繩韁等索具打交道,故此云‘能結綰,以見其精通多能也。”[3]222所言堪稱的論。兒時在鄉下,父親曾作生產隊飼養員,飼養場院乃我常去玩耍之地,對牲口索具之類比較熟悉,故可為《選注》所釋為一助力也。
(18)辜僥。《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棄德背恩行不孝,貪心逐色縱心懷。三年浮(乳)哺誠堪嘆,十月懷躭足可哀。不念二親恩養力,辜僥棄背也唱將來。”[2]970末句“辜僥”一詞,《校注》釋曰:“蔣禮鴻云:‘這個詞與不孝同意,大概就是辜負的意思;‘辜僥應即‘辜嬈,‘辜指辜負,‘嬈指惱亂,與文意相合。”[2]982《研究》釋作“辜負”[4]46,當是采信蔣禮鴻先生的見解。《選注》作了一條很長的注解,幾近全面論證,今移錄如下:
辜僥:即“辜較”,斤斤計較,分毫必爭。《無量壽經》卷下:“父母教誨,瞋目怒應,言令不和,違戾反逆,譬如怨家,不如無子。取與無節,眾共厭患,負恩違義,無有報償之心。貧窮困乏,不能復得,辜較縱奪,放恣游散,串數唐得,自用賑給。”同本異譯的《無量清凈平等覺經》卷四:“辜較諧聲,放縱游散,串數唐得,自用賑給。”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六《辜搉》:“上古胡反,《說文》:辠也,從辛,古聲。經從羊,不成字。案辜亦固也。下音角,或作較,《考聲》:權專略其理也。從手從隺。經文作較,亦同,通用也。故知“辜較”亦作“辜搉”。《后漢書·靈帝紀》:“(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搉,馬一匹至二百萬。”李賢注:“《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搉,專也。調障余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漢書·王莽傳下》:“如今豪吏滑民辜而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顏師古注:“辜搉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辜罪也。”清黃生《義府》卷下《辜較》:“《孝經》‘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注:‘蓋,猶略也。疏云:‘辜較之辭。因悟前、后《漢書》諸所謂辜較、估較、辜搉、酤榷(辜、酤皆讀為估,較讀為榷),皆即此義,蓋估計較量之謂(注、疏釋蓋字,猶云大略、大較如此耳)商賈殖貨,必估計較量而后賣買。諸書辜榷,皆謂勢家貴戚漁獵百姓,奪商賈之利爾。”友生劉長東見告: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一:“戚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不善沽矯,鄉里之饑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沽矯”亦即“辜僥”“辜較”也。[3]1447-1448
《選注》為解釋“辜較”一詞,收羅資料極為宏富,令人嘆服。這一批資料,最早為漢代,中間又經唐宋,下逮明清,跨度達兩千年。其實,這個詞在我原籍民間現在仍在使用,說明它是一個極有生命力的古詞。
至于其意義,上引文獻多同買賣及經濟生活有關。不過,我特別注意到,在古今人物的解釋中,多用“專”字,如“權專略其理也”(《考聲》);“榷,專也”(《后漢書》李賢注);“獨專其利”(《漢書》顏師古注)。可知,專是“辜僥”一詞的重要內涵。我理解,這個“專”乃謂專橫、霸道、蠻不講理,而它與“斤斤計較,分毫必爭”是有區別的。單就買賣來說,“斤斤計較”是在討論價格時,錙銖必較、寸步不讓;而專橫就是強買強賣了,無道理可講。變文原說“不念二親恩養力,辜僥棄背也唱將來”,恐怕就不限于僅僅同父母在經濟生活中斤斤計較、分毫必爭了,而是不知孝敬與回報,反之態度蠻橫,極為粗暴,以至背棄二親,豬狗不如了。或許這才是作者此處用“辜僥”一詞的本義。至于這個詞的當代語義,據一生都在山西稷山縣工作和生活的摯友彭東旭先生見告,其義是說,講一個人“辜僥”,是說他不省事、好是非、不太講道理,又喜歡背地里說人壞話。但這種人又不是特別壞,只是品行差而已。聊記于此,供語言學者們參考。
(19)楨據。《維摩詰經講經文》(一):“今日經中道我聞,總教各各無疑慮。(中略)長時事事發精勤,不向頭頭生楨據。”[2]755末句的“楨據”,《校注》謂“俟校”[2]779,《研究》云“義待考”[4]135,說明此處尚未讀通。愚意以為,此“楨”同“爭”,蓋因唐五代西北方音有“韻母侵、更互通”現象,韻母en與eng 可以互代也,此處便是zhen 同于zheng 。而“據”字與“取”字音近致訛,故“楨據”當校作“爭取”。《漢大》釋“爭取”詞義之一云:“爭奪,力求獲得。《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法苑珠林》卷17:‘剃已,入河洗浴。時諸梵釋龍王等競來爭取我發。” [8]597變文中之“爭取”即是爭奪義。句中的“頭頭”,指每樁、每件事。唐方干《獻王大夫詩》:“直緣財力頭頭贍,專被文星步步隨。”由此可知,“長(常)時事事發精勤,不向頭頭生爭取”,意思是說,平常在每件事上都要努力勤勞,而不是遇事(每件事)就極力爭奪。這正是佛門倡導的價值觀。若如此,上下文意也就貫通了。
(20)皂大。《燕子賦》(二):“雀兒語燕子:‘何用苦分疏?因(本文筆者疑“因”字衍)何得永年福?言詞總是虛。精神目驗在,活時解自如。功夫何處得,野語誑鄉閭。頭似獨舂鳥,身如七(漆)搕 形。緣身豆汁染,腳手似針釘。恒常事皂大,徑欲漫胡瓶。撫國知何道,閏我永年名。”[2]413-414倒數第四句的“皂大”一詞,《校注》謂:“‘皂狀燕子色黑,‘大則疑為‘袋之借音字。‘皂袋喻燕身。”“‘事皂袋蓋謂逞腹貪食,故下句言‘漫胡瓶也。”[2]418《選注》理解與《校注》相似[3]548,文繁不具引。《研究》持謹慎態度,注明“義待考”[4]132愚意以為,關于雀兒的身體形色,雀兒在“頭似獨舂鳥”至“腳手似針釘”四句二十字中,已描述殆盡,似不必再說平常侍奉自己的“黑袋”。這個“皂”字,《正字通》云:“俗讀若灶,義同。”“恒常”即平常義。“事”則侍奉、供奉義。《易·蠱》:“不事王侯,志則可也。”《漢書·外戚傳·丁姬》:“孝子事亡如事存。”那么下文的“灶大”是什么呢?頗疑是指灶王爺。山西稷山縣民間稱灶王爺為“灶爺(音ya)”,而陜西人稱爹為“大”。但迄今為止,我尚未找到“灶大”是指灶王爺的確證。如果“灶大”是指灶王爺,那么此句的意思便是;平常我侍奉(供奉)灶王爺,下句才說“徑欲漫胡瓶”。“漫”字《漢大》釋云:“放縱,散漫,不受約束。《新唐書·元結傳》:‘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12] “胡瓶”為酒器,《漢大》釋云:“胡地產制的瓶。唐王昌齡《從軍行》之六:‘胡瓶落膊紫薄汗,碎葉城西秋月團。”[12]1213可知“漫胡瓶”即放縱貪飲。“徑欲”乃“直想”義。這樣,此二句的意思便是:平常侍奉灶王爺(祂管吃喝的),只為的是能胡吃海喝。末句的“閏”字當校作“關”,形近而誤。因上文燕子的話里有“縱使無籍貫,終是不關君。我得永年福,到處即安身”,雀兒是接燕子的話說的,所以下文它才說:“撫國知何道,閏(關)我永年名?”意思是說,治理國家,追求功名利祿那些事,我才不管呢。這些能關系到我名垂千古嗎?我才不稀罕這些呢。關于“皂大”一詞,我有如上想法,但不敢自信,僅供研究者參考而已。
(21)不辭。《秋胡變文》:“秋胡重啟阿孃曰:‘兒聞曾參至孝,離背父母侍仲尼……今將身求學,勤心皆(偕)于古人,三二年間,定當歸舍!其母聞兒此語,淚泣重報兒曰:‘吾與汝母子,恩口義重,吾不辭放汝游學,今在家習學,何愁伎藝不成……?”[3]363-364文中的“不辭”《選注》釋曰:“不辭:不推辭,意即愿意,多用在表示轉折語氣復句的上句,如《大唐新語·持法》:‘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因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唐鄭棨《開天傳信記》:‘寬子谞復為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谞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3]368《校注》在注釋“不辭”時,僅是轉述他人包括《選注》的認識,并未提出自己的見解[2]236。《選注》釋“不辭”為“不推辭,意即愿意”是錯誤的,與原卷意思滿擰。其實,“不辭”是“不能”義,在《秋胡變文》中恰恰表示其母不同意秋胡出外求學。如果表示同意,支持兒子出外求學,干嘛下面還要說:“今在家習學,何愁伎藝不成?”
“不辭”一詞,除了上述《選注》所引唐代文獻外,敦煌民間也有使用,意思也是“不能”。S.3877V歸義軍時代《洪潤鄉百姓令狐安定請地狀》原文如下:
1. 洪閏(潤)鄉百姓令狐安定
2. 右安定一戶兄弟二人,惣受田拾伍畝,非常地少
3. 窄狹。今又(有)同鄉女戶陰什伍地壹拾伍畝,
4. 先共安定同渠合管,連伴(畔)耕種。其
5. 地主今緣年來不辤承科,恐后別
6. 人攪擾,安定今欲請射此地。伏望
7. 司空照察貧下,乞公慿。伏請
處分。
8. 戊戌年正月 日令狐安定?譹?訛。
令狐安定與同鄉女戶陰什伍土地相連,“同渠合管,連畔耕種”,有許多方便之處。但近年陰什伍“不辭承科”,意即不能承擔科役了,所以令狐安定才提出要“請射此地”。如果陰什伍仍能繼續承擔“科役”(也叫“課役”),一切都能照常進行,令狐安定為何想由自己來耕種陰什伍這十五畝地呢?“不辭”即是“不能”,其義顯而易見。
關于“不辭”即“不能”義,劉瑞明[13]、江藍生[14]二氏已有解釋,均可參閱。我在上面僅是再提供一條例證而已。
以上所說,如有錯失,仍舊歡迎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陸步軒.北大“屠夫”[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36.
[2]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7:180.
[3]項楚.敦煌變文選注[M].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310.
[4]陳秀蘭.敦煌變文詞匯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5]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10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757.
[6]朱正義.關中方言古詞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29.
[7]景爾強.關中方言詞語匯釋[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209.
[8]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2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333.
[9]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8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286.
[10]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1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723.
[11]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11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210.
[12]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6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84.
[13]劉瑞明.“不道”及“不辭”釋義辨誤[J].貴州文史叢刊,1994(4):83.
[14]江藍生,曹廣順.唐五代語言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