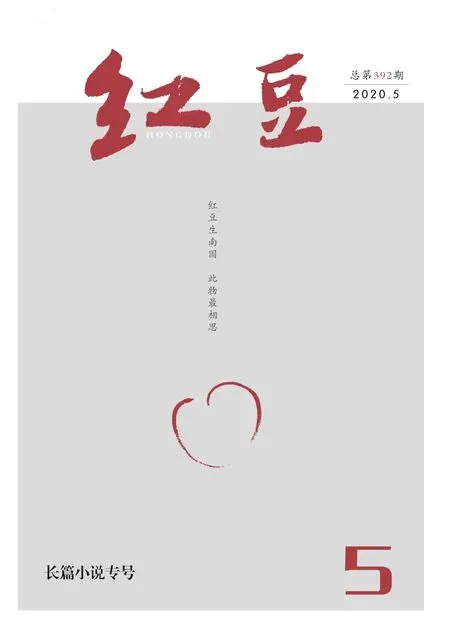被記憶籠罩著(創(chuàng)作談)
邱振剛
人的童年記憶會(huì)跟隨人一輩子,這話我信。
開始寫作的頭兩三年,曾經(jīng)和一位文學(xué)界的前輩聊天。前輩說,你的小說我看了一些,寫得有點(diǎn)雜,以后還是要關(guān)注同一類題材,爭取寫深寫透。我諾諾稱是,前輩接著問我今后打算關(guān)注什么,我脫口而出城鄉(xiāng)接合部。前輩表示滿意,說關(guān)注這個(gè)領(lǐng)域的作家不少,好作品也不少,要寫出自己的特點(diǎn)。我繼續(xù)稱是,等回到家仔細(xì)想想,又覺得所謂的城鄉(xiāng)接合部,不是一個(gè)文學(xué)的概念,我真正想關(guān)注的,還是住在這里的人。
我姥爺(外祖父)曾經(jīng)承包了他們村里的果園多年。這個(gè)果園,比這篇《天上的桃樹》里的果園可大多了,里面北方各種常見水果都有,光桃就有好幾種。那時(shí),我大半個(gè)暑假都會(huì)消磨在那里,熱了就跳進(jìn)旁邊的運(yùn)河,渴了餓了,一抬手就能摘個(gè)果子吃。
后來,整個(gè)村子拆遷了,變成了連綿成片的樓群,我的親戚們喜氣洋洋地揣著城鎮(zhèn)戶口本兒搬進(jìn)了樓房,果園也隨之被夷為平地。再后來,我上了大學(xué)讀了研,在報(bào)刊上看到各路學(xué)者分析著城鎮(zhèn)化過程中農(nóng)民的處境、命運(yùn),各有各的說辭和判斷。但對(duì)于我那些親戚,生活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們的農(nóng)具仍然在家里占據(jù)著一席之地,有的放在陽臺(tái),有的放在客廳,有的則專門騰出了一間房子來放。至于生計(jì),他們有的做著小生意,有的則在更遠(yuǎn)處的村里租了別人的地,繼續(xù)種著自己種了半輩子的各種農(nóng)作物。無論哪一種生活方式,他們都是和當(dāng)農(nóng)民時(shí)一樣,在用體力的付出,換得一日三餐,全家溫飽。
如今,當(dāng)年的城鄉(xiāng)接合部,正慢慢向鬧市區(qū)靠攏。當(dāng)年更加偏遠(yuǎn)的鄉(xiāng)村深處,據(jù)說那里的村民從前每年才進(jìn)城一兩次,都被列入城鎮(zhèn)化的規(guī)劃中。他們的生活已經(jīng)發(fā)生和終將發(fā)生的改變,當(dāng)然不是這樣一個(gè)短篇小說所能說清楚的,我希望的,只是寫出我看到的他們生活的局部。
故鄉(xiāng)那座小城如此,我如今居住的北京亦如是。那年,我剛剛搬進(jìn)后來住過多年的小區(qū),馬路對(duì)面就是一片自搭的棚戶區(qū),典型的城鄉(xiāng)接合部。當(dāng)時(shí)我去附近一所駕校學(xué)車,同一個(gè)師傅帶的學(xué)員里,就有一位三十出頭的同學(xué)住在那片自建房里。他說他自己早就會(huì)開車,可一直沒駕照,北京查得又嚴(yán),自己不敢開車上路,只得在一家裝修隊(duì)里當(dāng)小工。最近手頭稍微寬裕了些,就想著趕緊把車本兒拿了,再貸款買輛“小面”,這樣在北京掙錢的路子就多得多了。他車開得的確熟練,手腳極麻利,普通學(xué)員眼里最難的“倒庫”,對(duì)他都是小菜一碟。就有一樣,他的脖子不知為何,往某個(gè)方向轉(zhuǎn)動(dòng)的范圍比一般人要小,看后視鏡的話,需要把整個(gè)上半身都轉(zhuǎn)動(dòng)起來。好在他也如愿領(lǐng)到了車本兒。有時(shí)我和他偶爾在路上遇到,看得出他的境況的確是越來越好。
再往后,那片自建房拆除了,蓋起了一片南北通透的精致板樓,我不知道這位同學(xué)去了哪里,如今還在不在北京。在寫這篇小說時(shí),回想起他當(dāng)時(shí)的言談舉止,我可以斷定他很樸實(shí),但他是不是和小說的主人公一樣善良,我并不清楚。他是這篇小說主人公的原型,小說里很多細(xì)節(jié),都來自我和他的閑談以及我對(duì)他的觀察。這篇小說是寫給我那些親戚的,也是寫給他的。
我祝愿他生活幸福,無論他在哪里。
責(zé)任編輯 丘曉蘭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