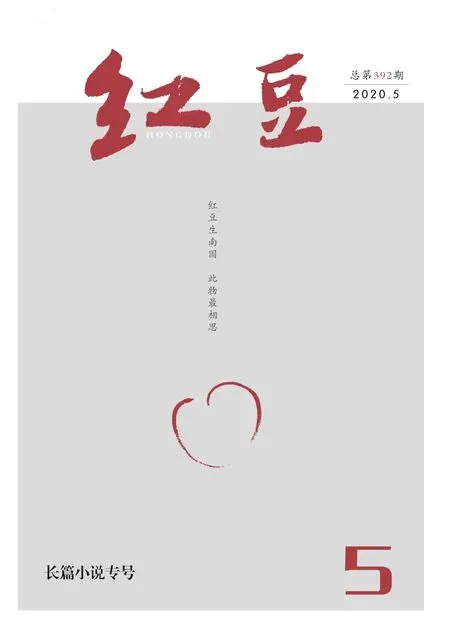汪曾祺是現代的
蘇北,安徽天長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安徽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專家。于《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十月》《大家》《散文》《文匯報》和香港《大公報》、臺灣《聯合報》等發表作品一百五十多萬字,作品入選多種選本。著有《蘇北作品精品集》、小說集《秘密花園》、散文集《城市的氣味》《呼吸的墨跡》以及回憶性著述《汪曾祺閑話》、《憶·讀汪曾祺》(五卷本),主編有《汪曾祺早期逸文》、《四時佳興:汪曾祺書畫集》、《我們的汪曾祺》、《汪曾祺草木蟲魚散文》、《汪曾祺少兒閱讀叢書》(三卷)等。曾獲安徽文學獎(安徽省政府獎)、第三屆汪曾祺文學獎金獎、《小說月報》第十二屆百花獎入圍作品等多種獎項。
1
汪曾祺是現代的。我不是說他是現代派什么的。我是說他是現代的——他的思想、情感、表達方式——都是現代的。
汪曾祺不是士大夫。“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帽子要從他頭上去掉。如果汪曾祺在世(這個“帽子”是他去世后流行起來的),估計他也不會要這頂“帽子”。我過去人云亦云地引用過這句話,但心中總是存一點點疑惑。
歲末年初,在北京參加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汪曾祺全集》首發式,著名學者孫郁先生的一番話,讓我深受啟發。他說,魯迅之后,一個作家的作品可以反復閱讀的并不多,有的作家只有一部兩部或者一篇兩篇能反復讀,但是汪先生幾乎所有文字都可以反復閱讀,所以我個人心目當中覺得《魯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是《汪曾祺全集》。孫先生還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汪曾祺是從沈從文來的,但是汪曾祺更朗然、更大氣,又很自信。他在世俗社會中發現美,而且又超越世俗。在沒有意思的地方發現意味。他創造一種美,他使我們感覺到生活如此美好,面對黑暗,他用一種美的東西去克服黑暗,他是不可復制的偉大作家,真正是我們民族的財富。
這真是見道之言。是的。汪曾祺是朗然的。他的身上完全沒有一點迂腐的氣息。他的人和文都非常地陽光、透亮。這其實也道出了汪曾祺去世二十年,為什么讀者還如此喜愛他,以至產生一大批“汪迷”和“汪粉”的重要原因。
回來翻看《汪曾祺全集》,在“雜著”卷中,有一篇訪談的開頭幾句話十分重要。這個訪談時間是一九九五年,由其家鄉高郵電視臺專門赴京做的。這個視頻資料現在看來真是彌足珍貴的。在這個訪談中提到汪曾祺的小說的寫法是“風俗畫”的方式。汪曾祺在這個訪談中透露,最早提出他的小說的方法是風俗畫的是老作家嚴文井。嚴文井說:“你這種寫法是風俗畫的寫法,這種寫法很難。因為幾乎全都是白描。”
這句“全都是白描”的話非常重要。白描的寫法難嗎?當然難。就像畫畫。八大山人的畫最難畫。它是最簡單的,又是最難的;徐渭、齊白石的畫最難畫,就那么幾筆,枯藤下來,枯荷下來,絕不簡單。
首發式結束回來,坐在車上前排的汪先生的大女兒汪明,忽然模仿汪老頭的口吻,來了一句:“他們說得真好啊!”
大家都笑了。汪明的這一番幽默,真是恰到好處。因為在首發式上,不止一個嘉賓提到:如果汪先生在天有靈,對這套全集的出版,也會感到欣慰的。
這句話典出汪曾祺的散文《名優逸事》。在這一組散文中,汪先生寫到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在擔任北京戲校校長期間,一次講話,念由秘書代擬的稿子,念到高興處,忽然一指稿子說:“同學們啊,他說得真對呀!”
到飯店坐下吃飯,大家說汪曾祺去世這二十年,出了多少書,都無法統計。他在世時,有時酒后狂言:“你們可得對我好點,我將來可是要進文學史的。”(這當然是戲言)可是他的三個子女,要么都不搭理他,要么就齊聲說:“老頭,就你?別臭美了吧?”
我就著大家的話說,老頭走后出了有一兩百本書吧?現在發現老頭的價值了吧?
汪先生小女兒汪朝笑著接話:“是的。是發現了——發現了他的經濟價值。”
大家又是大笑。
2
喜歡汪曾祺的讀者都知道,汪曾祺就讀于西南聯大。他在《汪曾祺自選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的自序中,謙遜地說:“我不排斥現代主義。”他說,“我不大同意‘鄉土文學的提法。我不認為我寫的是鄉土文學。有些同志所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們心目中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現代主義,我不排斥現代主義。”
其實他是受到過現代主義的影響的。在何兆武的《上學記》中,這樣描述:“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這個“學生”其實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早年寫詩。他在自己文章中說過:“因為愛寫詩,他在學校還小有名氣。一次,在路上聽見兩個女生聊天,一個問:‘誰是汪曾祺?另一個回答:‘就是寫那種別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詩的人。”
那些詩后來被研究者發現,當然都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的事了。有一本汪曾祺詩選集,書名叫《自畫像》(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這也是汪曾祺唯一的一本詩集,收錄了一部分汪曾祺寫于西南聯大的詩。現在來看,其中的一些詩,仍然給你一種新潮的感覺,比如《有血的床單》《自畫像》等。在《有血的床單》中他寫道:“年青人有年老人/卡在網孔上的咳嗽,/如魚,躍起,又落到/印花布上看淡了的/油污。磁質的月光/搖落窗外盛開的/玫瑰深黑的瓣子,你的心/是空了旅客的海船。”這完全是一種不知所以然的感覺。大約是一種青春的、落漠的情緒表達吧。
他在《自報家門》一文中說:“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后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沃爾夫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斷。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等。”
汪曾祺在《自選集》重印后記中說:“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上面的夫子自道,是實話。他確實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
3
汪曾祺為什么改寫《聊齋》,過去我一直不太明白。原來他是要賦予《聊齋》以現代意義。
蒲松齡當然了不起,但他由于時代的局限,在他寫下的這些志怪故事中,雖然故事奇異、描寫生動,但其價值觀,是肯定難以逾越他所處的時代的。也就是說,是缺少現代精神的。汪曾祺的改寫或者重寫,其目的就是賦予它新鮮的血液,使其更具現代意義。比如《快捕張三》,在《聊齋志異》中,僅在后附的“異史氏曰”的議論中,也只是三言兩語,與上文也毫無關系。故事寫一個叫張三的捕快,因常在外辦差,又貪酒,新婚的妻子被一個油頭光棍勾搭上了,一來二去,被張三發現,張三于是逼媳婦去死。媳婦說,那我得打扮打扮,穿上娘家的繡花裙襖。于是媳婦到里屋去收拾,張三在外間喝酒。“收拾”了好半天,媳婦出來了,張三見媳婦“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眼淚汪汪的”,媳婦向他拜了三拜……就準備去上吊自盡 。這時張三把最后一口酒飲盡,酒杯往地上叭的一摜,說:“且慢!回來!瞎!一頂綠帽子就當真能把人壓死了!”至此,夫婦恩愛,琴瑟和諧,過了一輩子。
汪先生改寫的目的,主要在此。他看重張三的“頓悟”,欣賞張三的態度。中國這個社會,直到今天,對女性,不同樣是較為“苛刻”嗎?
而《瑞云》呢?瑞云是杭州的一個妓女。十四歲了,“媽媽”叫她接客,瑞云說,錢媽媽定,人我選。結果求見的王孫公子不斷,而瑞云卻看上了一個窮書生賀生。這當然不行。可這日,來了一個秀才,坐了片刻,用手在瑞云額上一指,口中念道:可惜了,可惜了。結果瑞云臉上就有了一塊黑癍,而且越來越大。瑞云破了相,被趕下樓做了粗使的丫頭。賀生得知,賣了田產,贖了瑞云的身,娶回了家。小兩口過得恩恩愛愛。忽一日賀生巧遇秀才,說起這事,秀才說,瑞云臉上的黑癍是他所為。賀生求秀才使法,恢復瑞云的原貌。秀才同意,只端來一盆清水,用中指在水中寫寫畫畫。瑞云掬水洗面,黑癍立刻沒有了,瑞云又美貌如初。
本來《聊齋》原文故事到此就結束了。而汪曾祺改寫的關鍵就在結尾:
這天晚上,瑞云高燒紅燭,剔亮銀燈。
賀生不像瑞云一樣喜歡,明晃晃的燈燭,粉撲撲的嫩臉,他覺得不慣,他若有所失。
瑞云覺得他的愛撫不像平日那樣溫存,那樣真摯,她坐起來,輕輕地問:“你怎么了?”
賀生怎么了?這才是本文的關鍵:賀生原來僅有的一點心理優勢沒有了。他有一種本能的對美的恐懼。現代心理學將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
汪先生非常重視他的《聊齋》改寫工作,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受邀到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活動,只有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在行李中,他還帶了一本《聊齋志異》。他寫信給夫人施松卿說:“還有一個月,我可以寫一點東西。繼續改寫《聊齋》。我帶的《聊齋》是選本,可改的沒有了。聶(華苓)那里估計有全本,我想能再有幾篇可改的。”
他在美國先后改寫了三篇《聊齋志異》,包括《黃英》《促織》和《石清虛》。他給夫人的信中,對自己改寫《聊齋志異》頗有信心:“我寫完了《蛐蛐》,今天開始寫《石清虛》。這是一篇很有哲理性的小說。估計后天可以寫完。我覺得改寫《聊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這給中國當代創作開辟了一個天地。”
他以“開辟”一個“天地”來概括他改寫《聊齋》的意義。可見他對這項“工作”是多么的重視。
汪先生在《七十書懷》中說:“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可是這兩項工作,他都也沒有能夠完成,就撒手離世了。
汪曾祺從一九八七年改寫《聊齋志異》,陸陸續續寫了四年,才寫了《瑞云》《雙燈》《畫壁》《陸判》等十來篇,也只幾萬字,有的一篇才一千多字,多的一篇也不過三四千字(你知道他是一個惜墨如金的作家),不夠出一本書的。可惜了。
如果汪先生能多活幾年,手頭再抓緊些,改出個幾十篇來,出一本《聊齋新義》(改寫時他的篇名副題就叫這個名字)那將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
4
現在從早期作品的角度,來說說汪曾祺的現代性。把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藝術家》《牙疼》《花·果子·旅行》《理發師》《落魄》《小學校的鐘聲》《廟與僧》,放在一起去讀,是件很有趣的事。這些文字完成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那個時候汪先生才二十七八歲。那是怎樣的一個汪曾祺啊?
汪先生在《藝術家》的結尾寫道:“露水在遠處的草上蒙蒙的白,近處的晶瑩透澈,空氣鮮嫩,發香,好時間,無一點宿氣,未遭敗壞的時間,不顯陳舊的時間。我一直坐在這里,坐在小樓的窗前。樹林,小河,薔薇色的云朵,路上行人輕捷的腳步……一切很美,很美。”
汪先生晚年經常說:“我在二十多歲時的確有意識地運用了意識流,我的小說《復仇》《小學校的鐘聲》,都可以看出明顯的意識流痕跡。”
《日記抄——花·果子·旅行》:
我想有一個缾,一個土陶蛋青色厚釉小壇子。
木香附萼的瓣子有一點青色。木香野,不宜插缾,我今天更覺得,然而我怕也要插一回,知其不可而為,這里沒有別的花。
(山上野生牛月菊只有銅錢大,出奇的瘦脊,不會有人插到草帽上去的。而直到今天我才看見一顆勿忘儂草是真正藍的,可是只有那么一顆。矢車菊和一種黃色菊料花都如吃雜糧長大的臟孩子,要經過很大的努力與克制喜歡它。)
過王家橋,橋頭花如雪,在一片墨綠色上。我忽然很難過,不喜歡。我要顏色,這跟我旺盛的食欲是同源的。
我要水果。水果!梨,蘋果,我不懷念你們。黃熟的香蕉,紫赤的楊梅,蒲桃,呵蒲桃,最好是蒲桃,新摘的,雨后,白亮的磁盤。黃果和橘子,都干癟了,我只記得皮里的辛味。
精美的食物本身就是欲望。濃厚的酒,深沉的顏色。我要用重重的杯子喝。沉醉是一點也不粗暴的,沉醉極其自然。
我渴望更豐腴的東西,香的,甜的,肉感的。
紀德的書總是那么多骨。我忘不了他的像。
葛萊齊拉里有些青的果子,而且是成串的。
這是發表在早期上海《文匯報》(載1946年7月12日)上的一組散文里的一篇。這一組文字后來丟失了,是不久前發現的汪的佚文(剛剛收入《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的新版全集》)。說是“日記抄”,明顯看出是從日記中摘錄出來的。這些文字更像是散文詩,意象和文字的跳躍非常強烈。“那種豐滿、精力彌漫”是無與倫比的。這是年輕的生命,這是對未來還不能把握的一個年輕人的彌漫的遐想,也是那種“一人吃飽全家飽”的無所拘束和散漫落拓。
我看過汪先生二十多歲時的一張照片,臉上線條光潔,短發,嘴里叼著一只煙斗,一副故作老成的樣子,完全是一副“愛上層樓”的自負。可是,精神,飽滿,一種旺盛的生命充溢著,眼神清澄極了。
我只坐過一次海船,那時我一切情緒尚未成熟。我不像個旅客,我沒有一個煙斗。(《日記抄——花·果子·旅行》)
我需要花。
抽煙過多,關了門,關了窗。我恨透了這個牌子,一種毫無道理的苦味。《日記抄——花·果子·旅行》)
抽煙的多少,悠緩,猛烈,可以作為我靈魂的狀態的紀錄。在一個藝術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地抽,深深地吸進去,濃煙彌滿全肺,然后吹滅燭火似的撮著嘴唇吹出來。夾著煙的手指這時也滿帶表情。抽煙的樣子最足以顯示體內淺微的變化,最是自己容易發覺的。(《藝術家》)
這是一個怎樣的生命?!汪先生在去世前的兩個多月,為《旅食與文化》寫題記。在文尾汪先生寫道:“活著多好呀。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覺得:活著多好呀!”這跨越了半個世紀的文字對照著去讀。讓我們看到一個怎樣的生命!生命!生命!一個年輕的鮮活的生命,“空氣鮮嫩”。是啊!年輕多好呀!可以那么張揚,那么多的妄想,那么多的不切實際和自以為是!可是,“這一切很美,很美”。
汪先生晚年在文章中說,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其實汪先生晚年的文章,就是疏朗清淡的。這也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讀者喜歡汪先生文字的原因。可是他年輕的時候又是多么的繁復!那些文字黏稠、綿厚,不乏恃才自傲,用詞往險、絕、峻里去。
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從“愛上層樓”到“無事此靜坐”,一個人的一生,總是要變的。這種變化,不妨往書里去找,更重要的,是往生活里去找。“曾經滄海難為水”。一輩子下來,經的事多了。人情練達,無須賣弄。一切歸于蕭疏、俊逸,成就了一派大家風格。
汪先生晚年論語言:我以為語言最好是俗不傷雅,既不掉書袋,也有文化氣息。青年作家還是要多讀書,特別是古文。雅俗文白,宋人以俗為雅,今人大雅若俗。能把文言和口語糅合起來,濃淡適度,不留痕跡,才有嚼頭。
汪先生這是夫子自道。他自己一生的經驗都告訴了我們。
5
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其實是和早期作品一脈相承的,都是充滿了現代精神。有些作品更前沿、更超凡。打開《汪曾祺全集》他最后幾年的作品,如《小姨娘》《仁慧》《露水》《獸醫》《水蛇腰》《熟藕》《窺浴》《薛大娘》,雖然短小,然生氣盎然。《窺浴》寫得多么大膽,可又是美;《露水》寫出了下層人的艱辛和不幸。汪先生晚年對寫性更大膽了,寫得很放開。
比如《薛大娘》。薛大娘是一個極其通俗的故事,而汪先生把它寫得活色生香。薛大娘故事很簡單,薛大娘是個賣菜的,但她有一項“兼職”,是給青年男女拉關系(拉皮條)。街上的“油頭”看上了哪個進城務工的鄉下妹,兩人眉來眼去有了意思,薛大娘就給他們“牽紅”。有一回薛大娘自己看上了保全堂的管事呂三,兩人一人來二去,熟悉了。下面是這么寫的: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門口,對呂三說:“你下午上我這兒來一趟。”
呂先生從萬全堂辦完事回來,到薛大娘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進了屋里。進了屋,薛大娘就解開上衣,讓呂三摸她的奶子。隨即把渾身衣服都脫了,對呂三說:“來!”
她問呂三:“快活嗎?”——“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兒子20歲,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
薛大娘不愛穿鞋襪,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腳穿草鞋,十個腳趾舒舒展展,無拘無束。她的腳總是洗得很干凈。這是一雙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腳。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沒有被扭曲、被壓抑。舒舒展展,無拘無束。這是一個徹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這種寫法當然是很大膽的。人的價值觀并不是二維的:非黑即白。它是復雜的,多元的。
汪曾祺要寫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性的美。
《窺浴》是這樣寫的:
“你想看女人,來看我吧。我讓你看。”
她乳房隆起,還很年輕。雙腳修長。腳很美。岑明一直很愛看虞老師的腳。特別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涼鞋,不穿襪子。
虞芳也感覺到他愛看她的腳。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點暈眩。
他發抖。
她使他漸漸鎮定了下來。
(肖邦的小夜曲,樂聲低緩,溫柔如夢……)
這仍然是寫人,寫人的美。他熱愛美好的東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東西,他用文學加以彌補。他就是這樣倔犟的,不管不顧的,謳歌美,謳歌人,謳歌人性。
6
這篇文章著重討論的是汪曾祺的現代性。談這個問題,也是對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定義的“反叛”。我寫這篇文章還專門查了一下《辭海》關于士大夫的定義。“士大夫”的詞條說:“‘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階層。《考工記·序》:‘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鄭玄注:‘享受其職,居其官也。舊時也指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
顯然汪曾祺不符合上述條款的任何一條,他既不是官僚階層,他一輩子沒有當過官,沒有坐過專車,沒有提拔任用過同僚。雖然離休后有個“局級”待遇,那真只是個“待遇”。讀書人他倒是,他真是讀了一輩子的書。可是他到六十歲之后才成名,真是大器晚成。雖說大家都喜歡他、尊敬他,也只喜歡他的文章,喜歡他的人。“有地位有聲望”,還真是要看用什么樣的標準呢。在生活中,他并不像傳統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他自己說過接受儒家思想多一點。但他接受的,并不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竹籬茅舍、小橋流水式的。他喜歡《論語》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座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其實更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他其實最在乎、最欣賞的,是生活中的美。他總是用一種美的眼光,審視生活,發現生活。又或從經歷來看一個人的一生的話,嚴格地說,汪先生只是做了一輩子的編輯和編劇的讀書人。
如果說汪曾祺是“名士”、是“才子”,是可以的。他身上的確有名士氣,也有“捷才”。在《汪曾祺全集》中,有一卷名為《雜錄》,實際上就是他生活中的應酬、賀贈以及信函(包括給讀者的回信)之類。古人的交往、賀贈,有一些是成為傳世之作的,如蘇軾的《記承天寺夜游》、張宗子《湖心亭看雪》,更有一些成了書法的精品、珍品。比如王獻之的《中秋帖》、楊凝式的《韭花帖》和王珣的《伯遠帖》,等等。但今人確實已經是很難做到了。汪曾祺是個例外,他《雜錄》卷里面的“七零八碎”,你要認真去讀,真是非常有趣,而且文字極好,又富有才氣。這樣的才子文章,誰不喜歡?
在《汪曾祺全集》剛剛出版不久,有學者又發現了一通汪曾祺的殘信,緣起是一位大學教授對汪曾祺小說《異秉》中寫到的鹵菜的做法提出質疑,一連寫了三條。汪曾祺收到來信,不但沒有反感,更談不上反駁,而是心平氣和地和這位楊姓教授(楊汝 )交流起各地鹵菜特色和風味特點來。一封讀者來信,汪曾祺回信卻成了一篇美文:
王二的熏燒制法確實如我所寫的那樣。
…………
這種煮法另有一種香味,肉比較干,有嚼頭,與用醬汁鹵煮的味道不一樣。……這樣做法,現在似已改變。前年我回高郵,見熏燒攤上的鹵味都一律是用醬油鹵過的了。
羊糕有兩種。一種是紅燒后凍成糕。高郵人家制的都是這一種,你記得不錯。上海、蘇州和北京的稻香村賣的也是這一種。另一種是白煮凍實的。這種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時帶皮。凍時把皮包在外面,內層是肉。切成片,外層有皮,形如n,叫做“城門卷子”。“卷”,……讀宣字去聲。這種羊糕也叫“冰羊”,以別于白煮熱吃的“湯羊”。我有時到冬天自己做做“白卷羊”,凡吃過的都以為甚佳。
…………
豬頭肉各部分是有專名的。不過高郵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頭的舌與“蝕”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諱。無錫的陸稿薦叫做“賺頭”,與四川叫做“利子”一樣,都是反其義而用之。廣東人也叫做“利”,不過他們創造了一個字“脷”,我初到廣東館子看到“牛脷”即不知為何物,端上來一看,是牛舌頭!昆明的牛肉館給牛舌起了一個很費思索的名稱,叫做“撩青”!不過高郵人對動物的舌頭沒有這樣一些曲里拐彎的說法,一概稱之為:口條。
結果使這位楊教授大喜,他仿佛又得了一次“美文”的洗禮一般。汪曾祺就是這樣,他即使隨手寫的一個紙條,也許其中就有兩句叫你難忘的話,使你愿意把這個紙條收藏起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有些青年作家,文章寫得不好。主要是語言不過關。一個作家要隨時隨地鍛煉自己的語言,即使寫一個檢查、寫一封信,也要力求做到文字準確簡潔,意思明白通曉。
汪曾祺的文字多是明快通曉的。在他的文字中,大多充滿一種內在的快樂,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當然他也有憂傷的甚至憤怒的時候,但那是極少數的。總體上說來,汪曾祺的調子是明快的、歡樂的。他自己說他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應該說是準確的。
因為汪曾祺特別重視語言。他晚年的作品,多白描,少華麗。表面看起來很“老實”,其實藏在這“文白相夾”的語言背后,是相當富有現代精神的。
這才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他作品經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責任編輯 藍雅萍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