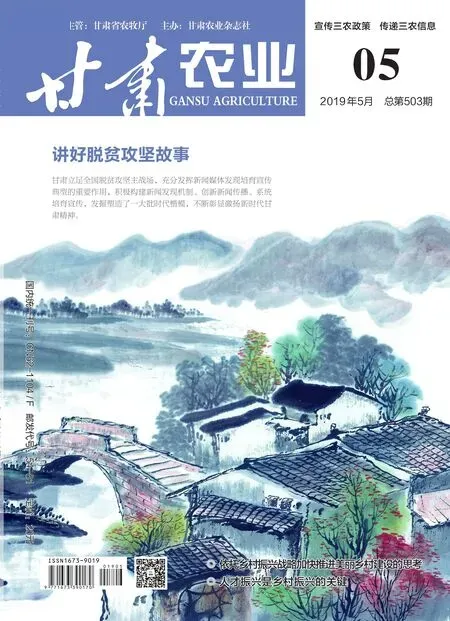叩拜一枚烤煙
師正偉

古語云:男兒膝下有黃金。但今天,我卻要對一枚烤煙頂禮膜拜。對我來說,可能沒有什么農作物比烤煙更值得感恩和敬重的了!確切地說,我是和烤煙一起成長的,它是構成我生命的骨骼和血液。
烤煙,當這兩個字從正寧人口中說出來的時候,如果烤煙能聽懂,它應該是感動的,也是自豪的。因為正寧人每每談及烤煙的時候,就像談到自己的父母或孩子,敬仰、感激,驕傲、期冀的心情都浸染在一片濃濃的鄉音里。人們對于任何一種農作物都沒有像烤煙這樣親切過,自豪過,感恩過。在正寧人心目中,烤煙和先人一樣值得懷念和敬重!以我跳出農門二十多年了,還對烤煙念念不忘為證;以本地民諺:“正寧烤煙甲天下,西北五省獨一家”為證。
總之,無論現在生活在農村,還是從正寧農村走出的城里人,對烤煙的感情,那是不銹鋼的感情,杠杠的!
一種作物的兒時記憶,為什么可以終生不忘?從祖父算起,我算個農三代,作為一個流著農民血液的游子,我對烤煙深深的情意,源于一顆虔誠的感恩的心。烤煙充實了我的童年,滋養了我和我的家庭。那些布滿煙草的歲月,就是立體的鄉愁,回想起來甜甜的暖暖的,不時在心底泛起一片濕潤,碎了心境,醉了心田。
烤煙是正寧隨處可見的農作物,每至秋夏季節,滿坳的、遍野的,一片連著一片的烤煙,夾著青草的芳香四處彌漫,豐富和潤澤了一代又一代正寧人的生活。這里的煙田,是以遼闊的大地為紙,以光亮的犁鏵為筆,春雨、烈日、酷暑、秋風,糅合煙農的汗水和微笑作為顏料,一天天一月月用一寸寸光陰精心細致描繪而成的。正是有了烤煙的碧綠,才有了莊稼人茁壯的力量;有了烤煙的芳香,才有了孩子閃亮的明眸;有了烤煙的金黃,才有了老人微笑的臉龐。
“不種煙吃風叭屁起都沒有”,農村人經常掛在嘴邊的這句口頭禪,聽起來有點粗俗,卻應了“話丑理端”的道理。在經濟匱乏年代。農民生活就像是一把生銹的槍栓,怎么拉都拉不開。那種困窘,用“舉步維艱”形容絕不為過。這時候,烤煙就成了農民的希望和念想,這種希望和念想,是物質層面的,更是精神層面的。母親經常念叨:“只要有煙種,我就有了心勁和盼頭”,“心勁”“盼頭”母親連用了兩個在農村人心中分量極重的詞,每一個都具有強大的穿透力和自信,可見欣喜之中難掩內心的激動。父親也常說:“種下了烤煙就種下了收成和光景”,“收成”“光景”與“心勁”“盼頭”意思相近,不過,父親表達的更含蓄,更文雅些。看來,在對生活的憧憬上,他們完全想到一塊了。記得那時,多數農村家庭秋季開學和播種時,幾乎都要去貸款,村上的信貸員只要在誰家煙田里一站,不需要任何抵押,就能根據長勢爽快地給他放出一定數額的貸款。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姊妹四個相繼考上了大學和中專,隨后又陸續結婚成家,集資樓房,家里來錢的路子少得可憐,對錢的需求程度只能用“迫切”來形容。母親經常為手頭不寬展愁眉不展,父親就會安慰說:“不了愁,有十幾畝烤煙擋著呢。”母親隨即滿懷信心的附和:“就是,不怕!只要年年種烤煙咱就有盼頭。”把兒女的前途,婚姻和生活寄托在一枚烤煙上,足以說明烤煙當年在農民心中的分量,那是期望和夢想,也是光明和力量。事實證明,幸虧有十幾畝烤煙撐起日子,父母親才帶領我們一家走出了人生最困苦的時期。
在正寧農村,人人都是務作烤煙的行家內手,一畝地種多少株烤煙,一株烤煙上留多少個葉子,一個成熟的葉子定什么等級,值多少身價,男女老少都心中有數。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畝好烤煙足足頂出一個干部一年的收入。因而,那時在農村,誰家烤煙務得好,誰就是村里的王,被烤煙擁戴而成的王。作為一個繁榮了幾代人的支柱產業,不光農村,城鎮也是如此:“財政收入的70%,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0%來自于烤煙”這句話曾連續多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也一度是政府和官員的驕傲!

身為農家的孩子,我深深知道農民一年四季在烤煙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是難以估量的,他們頭頂烈日,在煙田拋灑汗水的辛勤耕耘中孕育著一個碩果累累的豐收季節。烤煙要經過育苗、移栽、采摘、烘烤、分撿十幾個環節才能由“黃金葉”變成“金元寶”。一片葉子從育苗到繳售,農民至少要經手不下30遍,期間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精細管理并付出一定的勞動強度。首先,育苗就像繡花一樣是個非常講究的細密活。早春二月,風還在被窩里鉆著,田間地頭就一個接一個地搭起了小拱棚,農民整天爬在一畦畦田垅里,像小學生做填空題一樣在田字格里點種育苗,還猶如照顧嬰兒一樣隨時通風、澆水,并像給孩子檢查作業一樣一個格子一個格子的拔草取苗。無論三月的起垅覆膜,還是五月的大田移栽,都要起早貪黑和老天爺爭時間,搶墑情。開始,一家地綠了,接著,一坳地綠了,只有三五天的功夫就蔓延成一片,一村一舍的地都綠了。很快,厚實沉穩的烤煙就在黃土里扎根,生長成房屋,生長成村莊,然后再長出日子,長出歡笑,給生活錦上添花。
這些,僅是拉開農忙帷幕的序曲,真正的大忙是掰、系,烘烤和分撿。烘烤是煙農一年里頭最忙最辛苦的節骨眼兒。那時,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什么都可以耽擱,唯獨烤煙不能耽擱,耽擱一樓煙猶如耽擱土地一料子前程一樣令人惋惜和愧疚。每年烘烤伊始,母親既發愁又期待。發愁趕不上好年景難有好收成,期待“春種十畝煙,秋收幾萬元”。母親那種矛盾、復雜的表情,深深地烙進了我的記憶里,一生都無法抹去。
八月,烤煙進入采摘烘烤期,那是鄉村最繁忙,也是最熱鬧的季節,七天一個循環,一樓接著一樓,爐火不滅,人不停歇。而且還要兩天一打藥,三天一打杈。于是,整個家庭,整個村莊,都忙起來了,都變成了烤煙的臣民。這時,必須與老天爭陽光,與光陰賽跑,就怕冰雹突襲,就怕陰雨連綿,導致烤煙腐爛和黑曝。那個季節,莊稼人的精力永遠是充沛的,大田里的烤煙一直是幸福的!我家每年種著十幾畝烤煙,父親在外教書,我們兄妹都在上學,每逢星期天掰煙、系煙雷打不動。每次烤煙掰完、系好,裝進烤房的時候,都到凌晨兩三點鐘了。這時候,月光灑滿小院,樹影婆娑,一家人才能深深的喘口氣。雖然很累,但心理舒坦,臉上也洋溢出爽朗的笑顏和豐收的喜悅。現在回想,那時的勞動,像是煙田里生長的童話,瘦弱的身體從沒覺得累,反而和成熟的烤煙一樣,心情是碧綠的,快樂是金黃的,常常一邊勞動還一邊說笑。
烤煙就是土地結出的繭,包裹著鄉間生活的蛹。它始終帶著大地持久的芬芳,溫潤地把身子貼在鄉間,只要有一把泥土,一滴雨水,一束陽光,就能在歲月的大田里站成一尊佛,滋養著鄉村的軀體和靈魂,而父輩們則是它虔誠的信徒。記憶中,年邁的祖父經常以擁抱的姿勢摟著烤煙,以蒼老的手掌撫摩親近著烤煙,宛如翻閱著一本無字之書。父親常常一個人在煙田里行走,像一個將軍正在檢閱自己的一隊隊列兵。那一行行烤煙,就像大地上一行行的文字,寫著父親酸甜苦辣的晝夜,寫成了一部生命的百科全書。母親也會有事沒事就站在地頭凝望著碧綠的煙田,目光慈祥,就像凝望著快樂成長的兒女。微風輕輕一吹,整個煙田就掀起一片碧綠的波浪,母親也會隨著波浪露出會心的微笑。那笑,是最甜的。情,是最深的。
繳售烤煙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鄉間的大路上滿載黃金葉的大小車輛黑明晝夜絡繹不絕。收購站內技術員的叫號聲、庫房里的打包聲匯集在一起,奏響了鄉村最動人的交響曲。一個個煙農用干瘦的手指捏著一沓沓鈔票,喜上眉梢,高興的猶如兒女考上了大學。
正寧烤煙曾經無數次在新聞媒體上拋頭露面,面積最多的時候超過10萬畝,煙農在實踐中摸索創造的切塊育苗、劃行器、小推車、系煙車還被《隴東報》以《正寧煙農的“四大發明”》為題,在頭版頭條做過重點報道。如今,受國家政策限制,烤煙面積雖然大幅減少,但隨著嘉峪川煙水配套工程的實施,隨著智能烤房、飄浮育苗等新技術的引進和推廣,農民的勞動強度大大減少,收入卻成倍增長。
歲月倥傯,時光翩躚。正寧烤煙,縣以其聞名,地以其興盛,村以其改顏,人以其榮華,一片烤煙撐起了一片新藍天,托起了一個新夢想,永遠溫暖著農人的心!
我是一個十分懷舊的人,盡管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懷念兒時忙碌的烤煙季節,懷念那隨風搖擺的綠色波浪,懷念那激動人心的收購場面,那沁人心脾的縷縷煙香至今讓人倍感親切和舒暢。現在,我在父母辛辛苦苦栽種的煙田里長大成人,并在縣城有了自己的工作,已經多年沒種煙了。今年前季,我在兩個閑置的花盤栽了兩棵烤煙。母親看見后想拔掉它,我忙阻攔說:“媽,那是我種下的兩篇散文”。
對我而言,烤煙,已經成為一種鄉愁的符號,如同我的乳名,永遠珍藏在記憶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