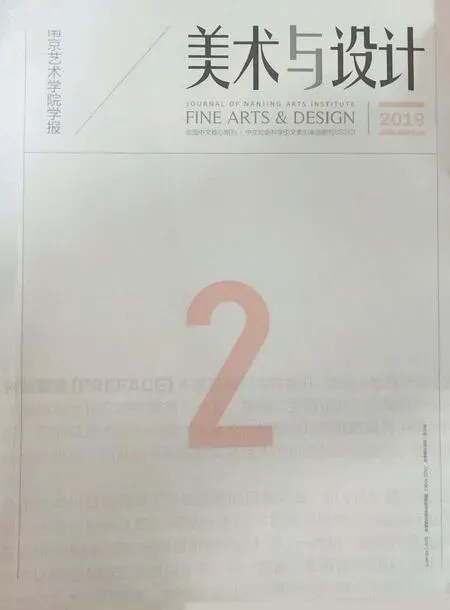犍陀羅佛傳藝術的多辯之源①
閆 飛(揚州大學 美術與設計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0)
李 勇(新疆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
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歐亞大陸間形成了一條以經貿為主導的政治、文化走廊,在往來的商貿中,中國的絲綢制品成為該商道西運貨物中的主流。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所著《中國——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一書中,稱其為“絲綢之路”。據史料記載,絲綢之路由張騫(西漢)出使西域開辟,一直沿用至16世紀。絲綢之路東起中國長安,途經河西走廊,在我國西域形成北、中、南三道,后形成多條分支覆蓋中亞地區,其中南道穿越蔥嶺,后匯合為兩條主徑向西亞、歐洲、南亞三大文明之地延伸:一條穿越西亞古波斯地區,抵地中海東岸西頓,終達羅馬;另一條從白沙瓦(犍陀羅首都)南下,到達伊斯蘭堡、拉合爾、新德里等古印度諸地。據學界考證,佛教藝術從印度傳向我國也有南、北二道,其中影響較大的北道,正是由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地區發源,沿絲綢之路北上途經古西域向東傳入中國,也被稱為“北傳佛教”。犍陀羅則被認為是印度佛教藝術和北傳佛教藝術的發源地。
一、犍陀羅藝術的多辯之源
犍陀羅因璀璨的佛教藝術而文明于考古學、人類學、宗教學和藝術學等領域,歷史的變遷和王朝的更替,使其在佛教造像上形成了許多復雜而難解的學術問題,一直處于印度、中國以及中亞等地區佛教藝術源流研究的焦點,究其原因總結為以下幾點:(一)犍陀羅佛教造像中的西方之源。亞歷山大的東征,迅速的把希臘文化播到以前從未到達的印度和中亞地區。此后的希臘人越過興都庫什山脈,在犍陀羅地區建立了印度希臘王國。[1]到貴霜王朝統治時期,犍陀羅地區已經深受希臘文明的影響,在佛陀造像的創作上多有效仿希臘藝術的痕跡,這一時間以阿波羅雕塑為范本的深目高鼻、身披波紋狀布衣的佛陀造像,在犍陀羅地區廣為興盛,這與中印度佛陀造像有明顯區別。富歇(A.Foucher)則認為,早于希臘人統治犍陀羅時期,即公元1世紀后半期,印度的佛教造像與希臘藝術彼此借鑒,產生了具有希臘風格的犍陀羅佛像②[日]宮治昭著,王云譯的《印度佛教美術系列講座—第二講犍陀羅佛教美術》中轉述觀點。,從考古發掘還無法證明此時已有佛像出現,但對犍陀羅佛教造像希臘風格的研究價值早已超越藝術領域,它是人們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典證。(二)印度佛教造像之源。早在富歇(A.Foucher)和庫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 Ananda Kentish)時期,就一直圍繞佛教造像起源犍陀羅還是秣菟羅,時間在貴霜朝以前還是貴霜朝以后進行爭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又有一批學者對佛像起源問題進行了周密而詳實的討論,如:[德]來烏(Louhuizen -deLeeuw)、[英]馬歇爾(J.Marshall)、[日]高田修等學者。雖然仍然沒有最終的結局,但越發活躍的學術討論凸顯了犍陀羅在佛教藝術史上的地位。(三)佛教藝術東傳之源。犍陀羅地處文化交融的要沖之地,憑借地緣優勢和古代成熟的商道線路,犍陀羅的佛教藝術成為佛教藝術北傳的重要來源,以絲綢之路傳入新疆地區的龜茲、焉耆、高昌等,甘肅地區的敦煌、武威、麥積山、炳靈寺等,山西的云岡等。對中國、日本等中亞地區的佛教藝術影響深遠。這些都為后人對犍陀羅佛教藝術的研究提供了多方向的切入點。
二、犍陀羅佛傳藝術中的中印度因素
與佛教造像的發源地爭論相關聯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早期佛教造像風格的源出。富歇(A.Foucher)認為佛像以希臘的阿波羅神像為模特,是由來到西北印度犍陀羅地區的希臘人創造出來的。并將犍陀羅佛陀造像與希臘化雕塑做了細致的比較分析,得出了犍陀羅佛像是“印度——希臘式”的結合。[2]然而在論述中強調了雕塑造型的希臘化藝術形式,但印度本土的影響只限于佛像創作中不同頭飾、配飾、服裝對人物身份組合的暗示。馬歇爾(J.Marshall) 在所著《犍陀羅佛教美術》一書中,論述了在呾叉始羅發掘的被稱為“裝飾盤”的石制浮雕陳設作品,被認為是佛像誕生前后的“犍陀羅藝術的發萌:塞克人時代”[3]的美術作品。這些石制作品的實用功能尚有不同推測,但從題材的辨識上多屬希臘化羅馬的藝術主題,如“阿波羅與達芙妮”“死者的宴饗”“乘海獸的人物”“酩酊大醉的狄俄尼索斯”“酒宴中的男女”等[1]。馬歇爾的研究成果又為早期犍陀羅美術堅定的打上了希臘化烙印。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佛教美術始于中印度的巴爾胡特、桑奇大塔,尤其是佛傳藝術。學術界普遍認為:“印度真正的佛教美術始自巴爾胡特以及桑奇大塔圍欄、塔門雕刻中的佛教故事(公元前 2 世紀末-公元 1 世紀初)。在這些浮雕中,不僅有各種各樣的釋迦前世的故事(本生故事),還有佛陀今生的一些偉大事跡。”[1]從意大利隊的斯瓦特佛教遺跡發掘成果來看,給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印度血統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如:布特卡拉1號出土的“三道寶階降下”圖對佛足的象征性表現與巴爾胡特、桑奇的此題材浮雕基于相同傳統;“梵天勸請”中佛陀左肩圓形重疊狀衣褶,與巴爾胡特的天人像的天衣表現相同。因此,宮治昭認為,“以往提到犍陀羅美術的誕生,就強調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但是,現在明確以巴爾胡特為代表的印度古代初期美術的影響更深。”[4]除以上學者的論述之外,巴爾胡特大塔、桑奇大塔還在佛陀造像、構圖形式、時空營造和讀圖方式上對犍陀羅佛傳圖像影響深遠,可稱得上為犍陀羅藝術中的印度血統。
(一)佛陀造像的同源性
佛傳圖像雖然興盛于犍陀羅地區,但始于中印度。約建造于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巴爾胡特大塔,就已經出現了單幅連貫性佛傳圖像①由于巴爾胡特大塔毀壞嚴重,保存的佛傳圖像多數很難辨識內容與順序。。桑奇大塔的雕塑中也有很多佛傳圖像,而這兩處佛教藝術遠早與犍陀羅地區。犍陀羅佛教造像雖繼承了西方藝術的真實性表現,但還不能概括佛教藝術的全部特征。以佛傳涅槃圖為例。如(圖 1),三組圖像皆為人物臥姿造像,a組為犍陀羅涅槃圖,b組造像為羅馬雕塑“死者饗宴”,c組為桑奇大塔“白象入胎”造像。a組佛陀造像為涅槃圖標準樣式,即佛陀右脅臥于床榻面朝觀者,右臂枕于頭下,左臂與身體保持一致;雙腿、足上下壘放,且上腿微曲;全身袈裟如同站姿,以此回避“釋迦之死”。b組上下兩個人物皆為左脅向下,人物半仰向上,上身動態慵懶,衣紋垂于床座之上,整體觀之與所塑造的“死者饗宴”主題基本一致。c組雕刻于桑奇東門正面右柱內側,描繪了佛傳“白象入胎”情節。圖中摩耶夫人動態與涅槃圖基本相似,即人物右脅臥右臂枕于頭下,正面觀者;雙腿、足上下壘放,且上腿微曲。
西方學者曾將b組希臘、羅馬的雕塑作品視為犍陀羅涅槃圖模式的原型,宮治昭也持相同觀點,如:“V.史密斯就曾經提到希臘、羅馬石棺浮雕中表現死者的場面對側臥于寢臺之上的佛陀涅槃圖所產生的影響……的確,常常出現在石棺上的‘死者饗宴’圖像,石棺上雕刻的側臥人物像等,都應該看作是為表現‘釋迦之死’的涅槃圖像提供了模型。”[5]94圖中可見,b組中兩個人物臥姿方向、雙手、雙腿姿態與a組涅槃圖佛陀造像決然不同,相同之處僅在衣紋的表現手法上有雷同之處。顯而易見,犍陀羅涅槃圖的程式化表現(特別是上腿微曲特征)源于中印的造像藝術,似乎因為白象入胎中的摩耶夫人是女性,使其與涅槃圖之間的造像關系被忽略。但兩者造型的相互借用存在一定的邏輯基礎:1. “白象入胎”刻畫了佛陀出生前菩薩化作白象進入摩耶夫人腹中的情節,“涅槃”為佛陀圓寂情節,用“生”來表現“死”,也正是佛教“涅槃”想要表現超脫六道輪回進入“無生無死”的永生境界;2.從佛傳圖像序列來講,如果將佛陀前生、后事情節去除,“白象入胎”和“涅槃”正好為佛陀傳記的首、尾兩個情節,兩個情節同時采用臥姿,雖有巧合,但不無關系。

圖1 三臥姿比較圖
(二)構圖形式的相似性
藝術作品通常是由造型、內容和構圖形式幾部分組成,佛傳藝術也無例外。古印度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相同佛傳圖中的人物造型、著裝都有著一定變化,但他們的構圖形式則相對穩定,特別是出生、降魔、說法、涅槃題材,更是形成了程式化的構圖形式。在中亞、東亞和中國地區,佛教造像都受到當地不同程度的洗禮,但構圖形式依然與犍陀羅佛傳圖像模一脈相承,這里所指的構圖形式包括圖像中所有造像布局、空間營造和敘事方式,具體如下:
1.對稱式構圖
犍陀羅佛傳美術對這一美學原理的應用較為多見,如:佛傳圖像二龍沐浴、初轉法輪、降魔成道、梵天勸請、舍衛城神變等題材,特別是說法、禮佛類、神變類佛傳場景都采用對稱試或次對稱試布局。宮治昭先生認為,犍陀羅佛像“三尊形式” (一佛二脅侍菩薩)有可能源于佛傳故事“梵天勸請”的演變,這種觀點尚在推論階段的原因是在佛教經文和相關文獻中欠缺推理依據。支持此猜想的條件是兩個題材的內在聯系,都是由一尊主佛左右兩側各有一個菩薩或天神構成,即對稱式構圖。然而,犍陀羅佛教藝術中的對稱布局又可追溯到建造于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巴爾胡特大塔、桑奇大塔,原因有兩點:1.以佛教故事為依據。桑奇大塔、巴爾胡特大塔的門梁和欄楯上多有佛傳“誕生”的故事畫面。如:巴爾胡特大塔欄楯(三處)、桑奇南門正面第一橫梁、二塔欄楯、東門正面第一橫梁左端下方矮柱、東門正面第二橫梁右端下方矮柱、南門正面第一橫梁、西門正面第二橫梁左端下方、北門背面第二橫梁左端下方短柱。[6]畫面中佛母通常手持蓮花或站或座于中間蓮花之上,兩側各有一頭象,長鼻卷起水罐為佛母灌頂①[日]宮治昭《桑奇大塔一號塔塔門雕刻》(王明增譯):“雖有人指出,‘二象為蓮花上的女性灌頂’是表現吉祥天女‘羅乞什密’的圖像,但這一圖像還意味著佛誕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否定的。”載《東方美術》,P73,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圖2)這是犍陀羅佛傳故事中“誕生”“二龍王灌頂”兩題材合一的原型。傳說:“悉達多太子誕生后,自己站立起來,向前跨出了七步并作獅子吼。于是,從天上流下溫涼不同的兩股清水,淋在太子的頭上(或稱二龍王灌頂)。”[7]在犍陀羅此題材中是由梵天、帝釋天二神為太子灌頂,秣菟羅地區是由龍神灌頂,這在佛經沒有統一的表述。(圖3)在早期佛教的無佛像時代,巴爾胡特、桑奇用佛母、蓮花、大象象征表現佛陀誕生、灌頂實為良策,這種對稱式佛陀誕生布局也隨之形成此類題材的表現傳統。2.以缺少希臘式對稱布局為旁征。故事圖與單體雕塑相比,其蘊含藝術創作的信息量更為龐雜,佛傳故事圖基于佛經的故事描述,將情節中涉及到人物、植物、動物、場景等按照故事論述的內在邏輯,進行組織再創作。據上文所述,馬歇爾(J.Marshall)在呾叉始羅發掘到的石制浮雕“裝飾盤”,如:“阿波羅與達芙妮”“死者的宴饗”“乘海獸的人物”“酩酊大醉的狄俄尼索斯”“酒宴中的男女”等,都未曾見到具有希臘風格的“對稱式”故事場景。在圖像的比對上多限于人物的體態、雕刻手法和一些細節處理上對犍陀羅的影響。而在桑奇大塔這種對稱式構圖的作品非常多見,如:成道(南門背面第一、二橫梁,南門正面)、龍王禮佛(西門左柱內側)、凈飯王禮佛(東門右柱)、初轉法輪(二號塔欄楯、南門正面左柱第一格、西門正面第二橫梁、三號塔南門背面)、竹林精舍(北門左柱)、涅槃(北門正面)等題材,都是已象征佛陀存在的圣樹、三寶標、法論、佛塔為中心的對稱式布局。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桑奇大塔中的對稱式佛傳故事構圖,是犍陀羅佛傳故事此類構圖的直接輸出地。

圖2 佛誕

圖3 龍王灌頂,約二至三世紀,巴基斯坦開伯而巴圖克瓦省,白沙瓦博物館藏

圖4 降魔成道(佛利爾美術館藏)
2.時空性構圖
桑奇大塔對佛經動態敘述的創作,造就了佛傳故事對場景與敘事的同時表現。場景的營造是一種空間上的概念,相對來說是靜態的,表現了某一時間點的故事內容,如佛傳故事初轉法論、梵天勸請、帝釋窟說法等,通過對故事情節中環境、人物、輔助角色等象征性信息載體的刻繪,表現了某一重要的故事情節。敘事性的則是指在佛傳故事中通過場景內容的變化,表現故事情節的動態發展。將場景與敘事相結合的表現模式,可以說是佛傳故事的創新之處,這種表現方式相結合的特點在于,畫面采用左右次對稱式布局。中間是對佛傳故事主題場景的營造,同時他在畫面上又成為故事敘述轉變的時間節點,左右兩側的故事情節圖像表面看是在此節點上產生戲劇性變化,其實是從整體上敘述了故事情節的發生、發展和結局。如佛傳故事中兩個描述戰爭的故事場景:降魔成道圖和八王分舍利。(1)降魔成道圖,(圖4)故事描述了釋迦佛陀坐于菩提樹下禪定,魔王波旬率眾多魔眾手持兵器前來阻撓。佛陀右手放置腿前施觸地印召喚天地女為其作證,攻克魔女誘惑和安撫魔王的情節。《普曜經》摘選:“爾時四部十八億眾,各各變為師子熊羆虎兕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虺蛇之身,黿鼉之首,一面六目,或一項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護戈矛戟,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8]犍陀羅降魔圖在構圖中以釋迦佛陀為中心,右側雕刻前來進攻的魔王和阻止魔王波旬的魔王之子,以及魔眾氣勢洶洶;左側描繪沮喪失敗的魔王波旬和魔王之子。同樣在桑奇西門背面第三橫梁降魔成道圖的壁畫中,位于中間塔廟內有象征佛陀存在的菩提樹和釋迦行將正道的金剛寶座。左側雕刻了護法天人、凈居眾天,做合掌、擊鼓、歡呼助陣降魔;右側則是魔軍陣營,魔軍眾手持戰斧、棍棒、叉、弓箭等各類戰具,靠近塔廟的個別魔軍成攻擊狀,但后部象軍、馬軍以及兵車等魔眾已經潰散敗逃。2.八王分舍利(桑奇一號塔南門上)(圖5),故事描述了八國發動戰爭求分佛陀舍利,最后通過調停,均分舍利回國起塔供養的故事。圖像中央刻畫拘尸那揭羅城池,近處城下戰爭與遠處城樓上下布局,兩側下層為軍隊沖向城池的進攻場面,上層為國王騎象帶舍利返回的場景。在犍陀羅此故事題材做了簡化,多表現城中婆羅門均分舍利場景。

圖5 搬運舍利,桑奇大塔

圖6 燃燈佛授記,高42.8cm,寬33cm,平山郁夫絲路美術館藏
佛傳故事圖還有一種“一圖數景”的構圖模式,是將同一故事在不同時間點、不同空間點發生的情節組織到一幅畫面中,如燃燈佛授記畫面將“買花獻佛”、“解發鋪地”等四個情節組合在一幅圖面中。(圖6)敦煌壁畫中的九色鹿王本生圖也是此類構圖。但桑奇大塔中場景與敘事相結合構圖方式,與“一圖數景”的方式還有很大區別。從內容分析其刻畫了相同地點不同時間的故事情節,從形式上則能是上文所述“對稱布局”的沿用與發展,是古代印度藝術家對上、下、左、右的空間方位與時間前、后關系相對應的視圖構建邏輯。
3.敘事性構圖

圖7 釋迦出游,桑奇大塔
遠景與近景相結合,是桑奇大塔佛傳藝術構圖的又一個組織秩序。與上文相反的是,這種秩序性反應的是同一時間節點中的不同場景。如:“尼連禪河渡涉奇跡”(桑奇東門正面左柱第三格),畫面用經行石代表釋迦,講述了釋迦為降服迦葉三兄弟在尼連禪河大顯奇跡的故事情景。畫面上除主人公以外,還借助樹木、動物、水蓮、水鳥等次要角色營造場景。其特點首先在于,故事場景的遠近關系轉化為上、下表現,并且沒有比例變化。其次,佛陀平步穿越、河水自然分開、騰空登傳、遠處河道迦葉三兄弟坐在船上與近處岸邊四位門徒合掌禮拜,這一系列不同場景但同一時間的故事情節,按照上、下序列匯集到一張畫面。又如:“四出城門”①桑奇大塔北門正面右柱第二格佛傳圖。,(圖7)畫面分上、下兩層,表現了故事中城內外兩個同時發生的情節。下層右邊由象征太子出家的馬車、傘蓋和高大的城門組成,左邊則以密集的侍衛和馬構成整體,將視覺體量感與右邊保持均衡。浮雕上層對宮廷內人物的刻畫顯然不符合現實的空間模式。從整體構圖來看,人物、動物是通過城門和象征建筑的欄楯圖案組合在一起。下部圖像有意將故事主角置于右側,通過由右向左的方向引導,從時間的動態表現了“出城”的過程,上半部分則以相對靜態的方式表現宮廷,構成了整個故事場景的完整性。類似巴爾胡特、桑奇浮雕中的密集“填充式”構圖,王鏞先生認為: “這種構圖方式體現了原先從事木雕的民間工匠充分利用有限板面的習慣,把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故事同時并置、組合在一起,從而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局限,獲得了表現的自由”[9]看似古代藝人為豐富畫面效果而刻意在壁畫中混合表現時空,確呈現出古代印度美術對時間、空間、方位三者之間非刻意的對應關系,并且從一系列佛傳故事的構圖中印證了這三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傳統,影響到犍陀羅佛傳藝術的再創作。比如“向右”與“向前”有某種對應關系,在犍陀羅佛傳故事中“逾城出家”情節,只要側面表現太子騎馬出城時的,釋迦太子基本都是向右方前進,有趣的是在“出家決定”中,坐在床邊決定出家的太子,頭部也是面向右方,盡管個別圖列太子身體朝左,但頭部都轉向右側。(圖8)這可能因為壁畫圍繞佛塔下壁裝飾,而順時針繞塔禮拜的路徑,產生了向右與向前的對應關系,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方向與左、右之間的內在聯系。
因此,如眾人所知,羅馬藝術對犍陀羅佛陀造像的影響主要鑒于對人物特征和衣褶的表現,但其原因是羅馬文化的直接干預,還是犍陀羅人種特征和寒冷氣候對本土人物造像的影響。②“人種特征”是指羅馬帝國對犍陀羅長期統治后,由于民族融合對當地人種在相貌、體態上的影響。“寒冷氣候”是指,犍陀羅位于古代印度西北部氣候相對寒冷,影響佛陀通身長衣的塑造。這兩點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成因在學術界雖非主流觀點,但也受到部分學者關注。然而,犍陀羅佛傳藝術與古代中印度美術相比,并不是趨于表面裝飾化和象征性的借鑒,而是顯現在藝術創作的思維邏輯上具有同根性。這是一個民族藝術創作中的文化內核,就算疊加不同的視覺元素,都很難以時代交替而轉移。

圖8 出家決定,白沙瓦博物館藏
結 語
近年來隨著眾多領域學者的參與,犍陀羅佛教造像起源的觀點受到質疑。但本文還未曾涉及對佛教造像起源的探討,只是從另一種角度介入,闡述佛教藝術的印度本土化問題。犍陀羅佛教藝術受西方美學影響這一點無可厚非,特別是與中印度早期的夜叉造像和秣菟羅佛陀造像相比,犍陀羅佛陀造像中的深目高鼻都與西方文化東漸有著密切關系。但從佛陀傳記圖像來看(文中簡稱“佛傳圖像”),犍陀羅佛教藝術受到中印度影響更為深刻,這一點主要因為佛傳圖像多為場景式構圖,其所包含的信息量要遠大于單尊佛像。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看出東西方在藝術營造方面的差異性,如文中對浮雕式佛傳圖像的構圖形式、空間營造和讀圖方式進行比較,此類與中印度藝術之間的近親關系顯而易見。如果就以佛陀造像為模本探討犍陀羅佛教的西方因素,其實也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如宮治昭先生對犍陀羅初期佛教藝術的風格劃分,以及佛陀造像起源于佛傳“梵天勸請”圖像來說,早期的犍陀羅佛陀造像,面部僵硬,很難看出有西方美學中的自然主義觀念。因此,是西方文化的注入,觸發了犍陀羅佛陀造像的初創,還是犍陀羅佛陀造像在不斷完善中融入了西方元素,還值得商榷。在此問題上,今后還會針對佛陀造像的具體形態著文論述,為此文觀點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