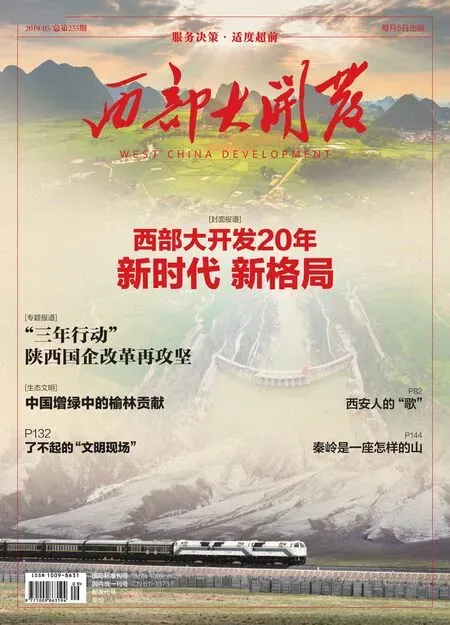西安人的“歌”
文 / 本刊記者 王薇
在《西安人的歌》翻紅之前,鼓樓、鐘樓、城墻、火車、高樓大廈、泡饃都可以被看做西安的一個側影,但當這一個個具體形象被同時寫進歌詞時,似乎又立即讓人產生了“只有西安人和在西安生活過的人才懂”的感受,既勾起了西安人的鄉愁,也讓許許多多沒來過西安的人萌生出“百聞不如一見”的旅行沖動。究竟是“城市的魅力”還是“音樂的魔力”在這其中作祟,我們竟不得而知。
曾有外地人說,在西安,仔細端詳秦俑的面孔,你會發現和路上的行人酷似。西安有著明顯不屬于現代漢語的地名,未央區,鳳鳴路,曲江路,下馬陵……也有古樸大氣的唐代建筑。在西安完全可以想象,人們正與一千甚至兩千年前的歷史共處,而音樂恰恰給了我們將過去與現在重疊的機會。
落寞的秦腔
呼喊一聲綁帳外,不由得豪杰笑開懷……單童一死陰魂在,二十年報仇某再來。刀斧手押爺在殺場外,等一等小唐兒祭奠某來。
——秦腔《斬單童》
很多人認為西安的音樂是從搖滾開始的,但在聽到嘶吼的秦腔之后,又有了“西安之所以出了很多搖滾音樂人,跟秦腔很有關系”的說法。
秦腔是戲曲,同進過宮廷的京劇相比,秦腔誕生在鄉野,甚至談不上講究。秦腔愛好者蘆笛曾在一次采訪中說:“京劇給人感覺就是一個特別矜持的人,坐在那里,跟你慢慢地聊,不會發怒,很少動氣,也很少傷心。”
但秦腔不同,蘆笛舉了《斬單童》(隋唐演義里的一段故事)的秦腔片段。單雄信在瓦崗寨占山為王,他仗義疏財,濟弱扶貧,是個英雄好漢。在和唐營的戰爭中,他被李世民俘獲。當年在瓦崗寨結拜的兄弟都已經在李世民帳下,于是他們來勸降,單雄信誓死不愿。李世民下令斬首,在受斬前,單雄信大罵李世民,罵徐茂,罵羅成……一個一個罵下去,每個兄弟交情不同,罵得也不同,最后,他跟程咬金交代后事。大家還在勸,你降了吧!人家說降!單雄信說殺!降!殺!降!殺!最后殺了。“就是這么強的設定,大段唱腔,情感層層遞進,秦腔的悲壯慷慨,是勝過京劇的。”
但在多數鮮少接觸秦腔的年輕人眼里,秦腔聒噪吵鬧,直扎耳膜,常伴有夸張的表情與凄厲的嘶吼。在我模糊的記憶中,秦腔是老者才能領悟的語言,但在諸多秦腔愛好者的講述中,我仿佛觸到了秦腔的“另一面”。
秦腔和大部分戲曲一樣,誕生在鄉村生活中。要在露天的戲臺上,唱給上萬觀眾,所以喧鬧,劇情生動,戲劇性強,合乎當地的倫理道德。秦腔充滿了地域特色,是本地人的特殊表達方式,承載著本地人飽滿的情感與獨特的秉性。

秦腔惠民演出
雖然在西北五省區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愛秦腔、聽秦腔、唱秦腔的人依然眾多,但與從前相比,秦腔已然難再輝煌,秦腔的沒落,是農村的沒落。
2018年,西安市周至縣劇團排演的《關中曉月》一度引起轟動。很多人看后直感嘆:“想不到一個縣劇團能排出這么好的戲。”但這種“轟動”對于秦腔來講,更像是“垂死的掙扎”。2018年,武功縣劇團只演了100多場戲,其中30場是來自于政府資助的惠民演出,除去所交的社保,演員在劇團的收入一年才5000元。而相比于陜西省其他的基層縣劇團,周至縣劇團竟還是佼佼者。
大部分秦腔從業者都在思考是否要繼續堅守在秦腔的陣地上,看得到艱難而看不到大紅大火的父母們,也不愿意把孩子再送進藝校學唱戲。陜西一半以上的縣劇團都處于半癱瘓狀態,有演出了才把大家聚一起,沒有演出演員就只能靠紅白喜事或者干點其他的小生意養家糊口。
蘆笛說:“戲曲回不到那個人人都喜歡的時代了,但是能有百分之十的人喜歡,就比今天好多了。”現代生活的變化,顯得秦腔愈發不合時宜,秦腔的程式、忠孝節義的價值觀,都在社會的快速蛻變中受到了挑戰。更極端的是,多數情況之下,人們將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截然對立起來,秦腔一類的戲曲甚至會被不假思索地判定為老舊的、保守的,難以被理解的藝術表達方式。
《當代陜西》在2019年第4期發表了特別報道《掙扎的秦腔》,在讀者中引發熱議。有人認為,秦腔需要傳承,傳承需要政府的政策傾斜;也有人認為,秦腔巨大的市場潛力應當來自于擁抱大眾、勇于革新的魄力;更有人認定,“活兒好”是秦腔安身立命之本。
曾有記者在周游了全國多數城市之后說道:“在有的地方,現實太活潑了,歷史可以暫放一邊。比如杭州,阿里巴巴足以使人忘記臨安暖風。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歷史無處不在。比如西安,城墻在上班的路上,墓穴在農田里,要想象一千年前的生活,似乎并不困難。”我想,不論“嘶吼”的聲音有多微弱,秦腔大概就是西安人與歷史共處的證據。
昨日的搖滾
遙望著殘缺,昨日的城樓,吼一句秦腔,你熱淚縱橫,娘親還守在城門外,妹妹在風雨中等待,她生來憂傷,但我讓她堅強,長安,長安。
——鄭鈞《長安 長安》
音樂人譚維維曾在某電視節目大唱陜西民俗搖滾《給你一點顏色》,身為推薦人的崔健激動不已,稱觀眾們看到的是一個教科書級的中國搖滾樂,一個真正將陜西傳統元素華陰老腔與搖滾樂結合的典范。
華陰老腔同秦腔并不相同,與秦腔龐大的受眾群相比,華陰老腔只是家族戲,與皮影結合,并且只在村里唱;而從表演上來看,華陰老腔還常常體現說唱特征,因此常有人調侃華陰老腔是“最早的東方搖滾”。華陰老腔是否是“最早的東方搖滾”,恐怕還需要很漫長的歷史考證。但不可否認的是,華陰老腔有西北人的粗糲與豪邁,并且具備了搖滾的表現形式與內容。因此,如果說20世紀末,在搖滾這種節奏強烈、歌詞新鮮的音樂發展史上,西安始終占有一席之位的話,也許跟這片土地孕育的戲曲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華陰老腔具備了搖滾的表現形式,因此被調侃為“最早的東方搖滾”
搖滾這一音樂類型,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末期的美國,其靈活大膽的表現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樂節奏,不斷征服著千萬年輕人的心。搖滾樂狂放不羈、直抒胸臆,性格豪放的西安人很容易從中找到靈魂的共鳴。
“搖滾”彰顯著上世紀末年輕人的熱血與生命力,是精神文化匱乏年代里年輕人汲取和創造精神“養分”的“土壤”。繼北京成為“搖滾之城”之后,曾有人將鄭鈞、張楚、許巍合稱為“西安搖滾三杰”。
關于西安“搖滾往事”的書——《昨日不辭而別:廢都搖滾記憶1990-2014》中曾提到:“這年頭,誰不知道許巍、張楚、鄭鈞是西安歌手?哪怕你從來不聽搖滾樂。提起西安搖滾樂,最常聽到的就是這三個名字。這三個名字總是同時出現,就像涼皮離不開肉夾饃,這兩者又離不開冰峰汽水,以至于成為經典,成為西安搖滾樂的三個代表,或者說,是‘西安搖滾三杰’。”
但在鄭鈞、張楚、許巍之外,人們卻對西安其他的搖滾樂隊乏人問津。事實上,除了“西安搖滾三杰”,西安本土的搖滾樂隊風格多樣,有新金屬風格的黏液樂隊、檢修坦克樂隊,朋克風格的妖蕊樂隊、潛樂隊……曾有人做了粗略統計,從1990年至今,西安可統計的樂隊至少有200支,沒有演出和發布組建消息的更是不可計數。
在漫長的搖滾樂路途中,無論如何輝煌的樂隊都承擔著鋪路石的角色。在音樂產業鏈還不夠完整的上世紀90年代,老一輩搖滾音樂人遠走他鄉,留下的則不得不另尋出路。如今在西安人眼里,更知名的是以方言為主的搖滾樂,馬飛、王建房、黑撒、以及范煒、程博智則成了西安搖滾音樂的代表人物。融合民謠、金屬、電子等諸多流行音樂元素的搖滾也呈現了西安音樂的新風貌。
永恒的吶喊
你說陜西木有啥,我們都在這兒長大。你說陜西木有啥,五千年的故事厚厚一沓。你說陜西木有啥,每寸土地都有時光一茬。你說陜西木有啥,每座城市都有那文化一大把。
——陜西群星《陜西木有啥》
深夜10點,某個地下車庫里,幾名衣著迥異的年輕人,左拐右繞鉆進走廊盡頭的門里。一個10平方米不到的房間里,音響上的煙頭、酒罐子零散一地,他們視若無睹,不緊不慢地調試起樂器,準備開始日常排練。這支年輕的重金屬搖滾樂隊,組建于2014年,白天樂手們各自忙碌,晚上相聚練習,偶爾有演出,有沒有演出費也不在乎。這間小小的排練室,就是他們最固定的舞臺。沒有觀眾,沒有喝彩,他們就是自己的觀眾。
與曾經諸多將音樂作為職業的音樂人不同,如今很多熱愛音樂的人都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對于他們來講,音樂是愛好,是調劑,是宣泄,是快速而又平淡的生活中的英雄夢想。
2017年夏天,一檔叫《中國有嘻哈》的綜藝節目聒噪了整個暑假,無數人通過這個節目知道了這個起源于黑人的特殊音樂形式原來在中國一直有如此龐大的市場基礎,無數優秀的地下歌手在這個暑假成了“大明星”。在中國星羅棋布的城市中,以西安、成都、烏魯木齊、北京為代表,一群熱愛說唱音樂的年輕人飽含生命力,真誠而野蠻地表達著自我。
嘻哈音樂曾因低俗與暴力長埋“地下”,于是嘻哈中文說唱也同樣在中國默默無聞發展十幾年,直到2017年被資本洪流的注入。在2018年《中國新說唱》節目中被淘汰的派克特,是NOUS廠牌的前輩級人物,依靠詩一般充滿思辨的歌詞和批判精神,被西安說唱圈稱為“西安之子”。在西安這個地方,嘻哈文化的興盛很難被解釋為“巧合”,而更像是西安搖滾的多元化“變種”。

在永寧門洞演出的年輕音樂人
凌晨一點半,當車輛駛過鐘樓和古城墻,沉寂的十三朝古都似乎進入了夢鄉,而此時,與鼓樓幾條街之隔的酒吧街里,年輕人喧囂的夜場才拉開帷幕。DJ打碟、蒸騰的干冰與晃眼的霓虹燈,這群身著潮牌T恤和帆布鞋的年輕人,正沉浸在嘻哈的世界里,盡情釋放著自己的青春和活力。酷、個性、小眾,已然成為這群年輕人們趨之若鶩的標簽。隨著音樂輕輕搖晃著身體,對于他們來說,中國沒有哪座城市比西安更能讓他們感到自由。
如今,每周三、周五、周六晚上的10點半,永寧門的城門洞人行道總是被來聽音樂的觀眾圍得水泄不通,東邊是“長安里”廠牌的歌手輪番上陣,西邊是“聽南門說”的固定班底,這里已經成為全國來西安游玩的年輕人的網紅打卡景點。
結語
城市是多重身份與多副面孔的聚合體,對外來游客而言,小吃、名人、風景名勝都為游客提供了一個城市的基本判斷,而音樂則為一座城市的對外宣傳充當了“民間使者”,彰顯著“脾氣”,透露著“秉性”。音樂文化在城市里流淌,嘻哈不能代表西安,民謠不能代表西安,搖滾不能代表西安,秦腔不能代表西安,然而它們也都代表著西安,都能稱之為西安人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