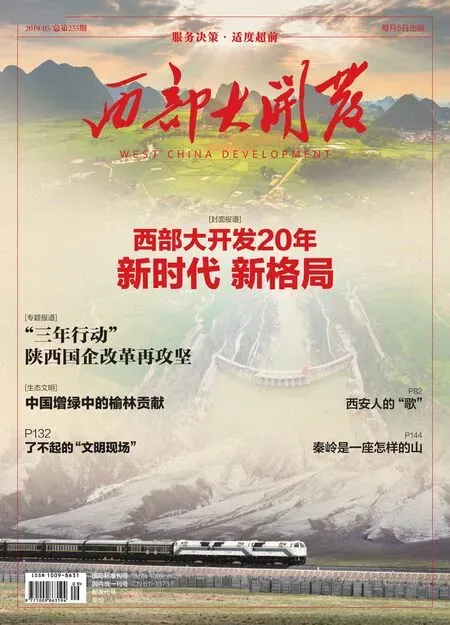石峁城囈語
文 / 雷濤
我又一次站立在陜北高原起伏的群山之中,站在突兀神奇的石峁城的正門高處。此時的東方已經通紅通紅,萬道霞光從那遠處的山山峁峁的尖頭射向天空,又向四下里散落下來,大地的金色與初春的嫩綠渾然一體,讓人感受到自遠古以來就存在的那種神秘而輝煌的自然氣息和文化氣息。
從這里眺望石峁城中的皇城臺,遼闊、奇異而高大。那拔地而起的山峁,用那石條砌壘而成的皇宮,在霞光的撫摸和哺育下,既雄壯奇偉,又柔媚虛幻。在這春回大地,萬物勃發的晨曦之中,銀白色的宮殿和金黃的天宇交相輝映,愈加顯現出其恒古的歷史風貌和發人幽思的獨特魅力。
在當地專家的陪同下,我沐浴著這春的陽光,春的明媚,徒步由城的正門走向皇城臺。眼前是一片開闊地,一條“S”形的小道蜿蜒延伸。這是一條多么古老、多么讓人遐思的路喲!當年有多少被強征的役夫們,肩扛石塊、石條或者不堪負重的原始器械,川流不息地緩慢的穿梭在這條山道上。其中多少人在發出痛苦的呻吟中倒下,又有多少人在工頭的呵斥和鞭擊下跌倒又爬起,艱難地向前移動;又有多少人在思念家室和兒女的心痛之中默默地發出詛咒和呼喚。“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這是后世人的哀嘆。而此前的情景必定會更加悲壯和慘烈。
在路邊,我隨手從已經返青的野草叢中撿起一個石塊,它顯然是被打磨過的。打磨它的主人雖然已經化作泥土,而他的作品還留在這讓萬人注目的古遺址之內。它也許沒有感知,但卻見證著人類由荒蠻到文明的發展變遷史。他和千千萬萬的勞作者一樣,用鮮活的但卻短促的生命換得了這段歷史,蝶化成這座至今不知年代,不知由誰修筑的城池。
行走間,我的腳步慢慢沉重起來。不是我的體能虛弱,也不是因為身上所攜帶的物品的累贅。而是一股莫名的惆悵和思古的幽情。我駐足沉思:一部厚重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怎么就沒有這個偌大的石頭城堡的任何記載,是史學家的疏漏,還是由于地理偏遠而失憶;是北方漢民族的歷史遺跡,還是其他某個民族群落的建樹?如此宏大的城郭,怎么就會躺在地下而不被世人所知曉呢?
伴隨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歷史疑團叩門,我來到了皇城臺根下。
腳下是石塊鋪就的地面,圖案嚴密,布局精巧。由于年代的久遠,兩側的高大建筑已經嚴重破損,但蘊含的恢弘氣質依然呼之欲出。由低向高望去,皇城臺的入口處呈鍋底形,緩緩向前延伸。再舉目仰視,兩側的石條所壘的宮城城墻在懸崖邊拔地而起,直上云霄,展現著至高無上的威嚴與神圣不可侵犯的氣度。忽然間,我回想到曾經光顧過的墨西哥國的瑪雅石頭城。兩座城在設計理念上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在長長的海岸線上,一個則在黃土高原的深處。此刻,一種猜想戛然而至:是先期瑪雅文明的創造者來到了這里,和當地的氏族部落一起建造這座城,還是祖國北方的某個部落在建造了這座城后,又因戰敗或其它原因而鬼使神差地去了遙遠的拉丁美洲,為那里的文明貢獻了人類的智慧。
在皇宮廣場的中央,我仔細查看刻有神秘符號和圖案的兩塊四方形石塊。似乎感受到了不屬于漢民族古老部落的社會氣息和文化氣息。恕我學疏才淺,才有這種井底之蛙的偏見。而再向上邁進,右側石墻的下部中,鑲有一塊較大的平行四方形石塊,上面所刻的一幅雕像,引發了我極濃厚的興趣。我先俯下身子觀看,又蹲在地上細細觀賞。畫面似乎是一個獸類,一個大寫意的獸類,面部碩大,而雙臂緊緊湊在頭的兩側。既有無比的神威,又有憨厚的善意;既有原始圖騰的強烈表現,又有部落獨有石刻藝術的傳承意蘊。我敢妄加直言,它不屬于中原古代石雕藝術風格,而是較為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和北漠其他遠古部落的文化特征。不知為何,我又回想起我在寧夏歷史博物館內所目睹的那尊典型的反映夏文明的大石雕,繼而又想起在靖邊統萬城遺址看到的某些遺存時的感受。于是我在心里發出囈語:這石峁城也許不是中原史前部落所為,而是北部“五胡”的祖先中的某一個族群所營造。而破敗的原因很多:或被另一胡所滅,或被中原的聯合部落所趕走,或是因為天災原因而棄城遠走……

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表明:這座城堡的建造年代并不十分遙遠,大約就在仰韶文明與紅山文明之間,亦即炎黃文明階段。這又使我回想起“釜山合符”的典故:炎黃二帝為了天下一統,召喚天下東南西北的部落首領在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地區的釜山會盟。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議定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圖騰。而此前,不同部落有自己的崇拜物,比如:熊、羆、貔貅、貙、虎、豹、狼、鷹、羊、朱雀、玄武等等。經過商討,大家最后認定了“龍”。釜山合符或曰釜山會盟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從此華夏大地各個部落有了共同崇尚的徽標即新圖騰。而有關資料表明,參加此次會盟的一個北方部落就叫鬻,鬻即獫狁。戰國后鬻、獫狁稱為“匈奴”。從此來看,“獫狁”族群興許是這石峁城的建造者和統治者。古河南的地理概念主指河套地區,今日的河南省的稱謂是后來的事。傳說黃帝生在靖邊的古陽城一帶,即古河南地,這里就有橋山。若真如此,司馬遷大人是否犯錯了。可以遙想,當年的鬻即獫狁部落,盤踞在石峁城,憑借著該城的堅固和游牧習性,經常南下侵擾中原的其他部落,并掠奪了大量的象征著實力與尊貴的玉器。石峁城中發現的大量的實物便是一個佐證。《史記·匈奴列傳》中提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司馬遷認定鬻、獫狁皆是一族,是匈奴的祖源之一。而王國維則認為“鬼方”“昆夷”“混夷”“獫狁”“董育”皆為同詞轉音。倘若如此,那石峁城大有可能就是古匈奴人所建。
匈奴人對中原的侵犯的占領企圖,從未停止過。后來的大夏、西夏政權,族群的名稱又有變化,但其屬性卻不變,是匈奴的后裔或曰分支。而為何稱“夏”,就是因為都承認是華夏子孫,都認夏啟為祖。石峁城的主人是否也這樣認為,不得而知,只有待考古專家的深入研究的成果了。
夕陽西下,石峁城又沐浴在晚霞的夢幻之中。走下山來,眼前的禿野河床寬闊而平坦,暮色漸漸籠罩著河流兩邊的山塬,隨著夜幕的降臨,高家堡古城內的燈光慢慢多了起來。我的腦中又一次出現幻覺:這高家堡就是高,高就高在它與石峁城同生共榮。甚至,它還早于石峁城。當年的高家堡只是占領者的一個小山寨。占領者出于長遠的目標和統治天下的雄心,才產生了在山上建造石峁城的念頭。這一切決策和設計都在這高家堡內。繼而,這里成了建石峁城的總指揮部和物資原料的集散地。而強征來的役夫們也都在這里押解,并派上用場。




兩次往返于高家堡和石峁城之間,走的就是那條唯一可以相互通達的山間之道。如今,高家堡已成為祖國北方著名古鎮的佼佼者,每年吸引著數以千萬計的旅游觀光者。石峁城的出現,無疑大大提升了這塊風水寶地的含金量和知名度。慕名而至的游客猛增,高家堡真正紅盛了。步入燈火璀璨的街頭,再回望那漆黑幽暗的通往石峁城的山路,我的思緒更加綿長,囈語也如同開閘的流水,不可阻止。那山路著實是一條血色的路,亦是一條文明之路。那路途中上演了一幕幕生命的悲歌和壯美的贊歌。在悲歌和贊歌的交響之中,石峁城聳立起來了,一篇文明的史詩出現了。
可贊可頌的石峁城喲,你的再現,將繼續改寫著中華民族的史前史。這是我們民族大家庭共同擁有的宏大記憶和巨大財富。我堅信,總有一天,你的“謎”會被完全解開。那時,我的囈語和夢幻一定會化為具象,化為我心中永遠的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