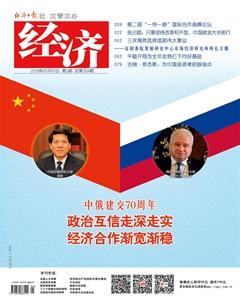常州石墨烯產業八年取經路
黃芳芳
江蘇省常州市是中國石墨烯產業發源地之一。從常州市武進區西太湖科技產業園驅車向北,抵達石墨烯小鎮不過10分鐘。路兩旁新栽的樟樹則四季常青,不像市樹廣玉蘭每到冬季會變得光禿。從2011年至今,常州的石墨烯產業之路歷經8年之久,未來它能否如樟樹一樣四季常青呢?
“明知山有虎”
石墨烯在落地常州前,相關人士預判石墨烯產業化是一件遙遙無期的事。
2011年,時任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在參加清華百年校慶活動時,偶遇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原院長馮冠平。范燕青對石墨烯興趣頗濃,向其詢問石墨烯的情況,馮冠平回應道:“石墨烯是一個好材料,但仍在實驗室階段,產業化可能需要7-8年甚至更長時間。”盡管如此,范燕青仍然表示常州愿意培育這類新興產業。隨后,常州吸納了馮冠平推薦的兩個石墨烯創業團隊。
“這兩個團隊只有‘腦子(技術),沒有票子(資金),沒有房子(創業場所),更沒有其他創業條件。當時,為了幫助這兩個團隊專心推進石墨烯的研發和產業化,常州專門成立了江南石墨烯研究院為這兩個團隊提供公共配套服務,并利用常州‘龍城英才計劃等政策提供一系列政府扶持,同時還成功推薦了社會風投、創投機構為其提供創業資金。”江南石墨烯研究院院長、常州西太湖科技產業園管委會副主任張銘向《經濟》記者講述當年二維碳素和第六元素兩家企業“落戶”西太湖科技產業園的緣起。
“當年我到常州,曾有人說石墨烯離產業化很遙遠,建議政府不要投了。當時范燕青書記卻說:‘產業升級不要說是8年、10年的事情,就是20年-50年能做好也實屬不易,政府不做長期投資,誰來做?”江蘇省石墨烯創新中心總經理、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瞿研向《經濟》記者回憶當年的情景。“中國中小企業居多,無力支撐長期性產業的發展。江蘇省是集體經濟和蘇南模式的發源地,政府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引導上起了很大作用。”
2012年初,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江蘇省原省委書記李源潮調研西太湖時,建議在此建一座以集聚高科技企業為目標的科技新城。此后,經過多輪研討,常州市和武進區兩級政府提出了建設常州西太湖科技產業園的設想,并將園區的特色產業定位為先進碳材料產業,它包括石墨烯、碳纖維、碳納米管、人造金剛石等,旨在打造一個與美國硅谷相媲美的“東方碳谷”。
2013年是令張銘記憶猶新的一年。二維碳素和第六元素分別做出了石墨烯產業化中試線,前者是全球首條年產3萬平方米的石墨烯透明導電薄膜生產線,后者是全球首條年產100噸的石墨烯粉體生產線。因為當時全球在規模化制備石墨烯方面還都在摸索階段,但是規模化制備的問題,常州率先給出了解決方案。
此后,常州西太湖科技產業園圍繞碳材料產業規劃進行產業招商,大量集聚以石墨烯為代表的先進碳材料產業項目。到2018年底,園區引進了各類石墨烯相關企業150多家,形成了覆蓋制造裝備、原材料制備和下游應用于一體的較為完善的產業鏈。
“2013年-2014年,我們重點招引不同制備方法制備石墨烯原材料的團隊,引進了包括二維碳素、第六元素、碳世紀、墨之萃、國成科技和瑞豐特科技等6家原材料制備工廠,它們的原材料制備方法齊全。當時石墨烯價值2000元/克,我告誡大家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沒有人會把鉆石當作工業材料。2014年后,隨著石墨烯原材料制備更加成熟,我們進一步圍繞石墨烯應用引進項目,涉及涂料、電纜、加熱、散熱、環保、生物、能源等領域,產品種類多達上百種,形成了一個十分豐富的石墨烯應用圈,也給石墨烯帶來了令人期待的市場空間。”張銘表示。
“8年了,我們嘗試了很多應用方向。今年我終于不焦慮了。”瞿研將第六元素定位為氧化還原石墨烯供應商。為了推進石墨烯產業化進程,它參股了7家下游公司。其中,參股最多的一家名為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烯科技”),入股1500萬元。富烯科技目前為全球前五的手機廠商提供石墨烯散熱膜。這也曾是2018年最令瞿研焦慮的事情之一。
“該手機廠商要在全球發布這款有石墨烯散熱膜的手機,但當時我們的產能跟不上。那陣子我每天熬到凌晨兩三點,生怕把握不住石墨烯應用在大廠商產品上的機會。”瞿研認為只有進入世界五百強的供應商采購清單,石墨烯產業才有希望。“2019年可能是石墨烯的爆發年。石墨烯防腐涂料、石墨烯散熱膜等銷售額有可能讓我們實現盈利。”
石墨烯創新的未來在何方?
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石墨烯行業每個從業者都渴望走在正確的產業道路上。
2017年底,常州市委、市政府啟動江南石墨烯研究院改制工作,目的是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和企業主體”的全新研發體系,期望用全新的體制機制激發石墨烯創新創業人員的活力。圍繞這一目標,常州打造“三位一體”的全新發展模式,江南石墨烯研究院作為公共服務平臺為石墨烯產業提供基礎條件,江蘇省石墨烯創新中心則重點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石墨烯行業關鍵共性技術難題,江蘇江南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則為石墨烯技術成果轉化提供資本支撐。
通過改革并構建研發體系,常州希望將最大的利益賦予創業團隊,政府則將精力集中于優化產業生態上,同時通過市場化的有效機制,多方撬動社會資本,以多元化的研發投入進一步增強常州創新研發實力。未來3-5年,常州希望打造一條由政府平臺做支撐、社會資本做資金投入、好的市場機制做創新動力的常州新模式。
同時,產業聯動也在探索新模式。今年瞿研的新身份是江蘇省石墨烯創新中心總經理。目前國內類似的石墨烯創新中心有四個:北京、江蘇、浙江、廣東。
瞿研認為,石墨烯制造業創新中心要為產業長期發展做準備,首先要實現自我造血、自我循環。“只有優秀的企業賺錢了,才能支撐起整個產業,制造業創新中心作為服務機構才能生存。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過,目前制造業創新中心還在探索新的商業模式。
一直以來,石墨烯企業都在單打獨斗。江蘇省石墨烯創新中心將成為連接基礎科學研發和產業的橋梁,填補實驗室技術到產業化技術之間的空白,也就是解決中試問題。“我們希望能成為科研與市場的橋梁,讓石墨烯成果迅速走向市場。”瞿研說。
共同的困境如何突圍?
石墨烯市場魚龍混雜,缺乏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虧損狀態的科技企業融資難,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不多等是常州石墨烯產業界普遍反映的難題。
據中國石墨烯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統計數據,我國石墨烯產業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6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70億元。但是70億的數據是如何構成的呢?行業人士猜測,石墨烯加入電纜或汽車中,統計者可能將整個電纜或汽車的價格算作石墨烯產業的市場規模,但是,石墨烯的用量可能只有一點點。這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石墨烯在這類產品中到底占多少比例?起了多少作用?是否是真的石墨烯?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結論。石墨烯產品的規范性、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公正性都因為缺乏標準而受到質疑。因而,行業人士呼吁應盡快出臺石墨烯國家標準。
“太理想無法生存,太現實沒有未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忠范指出,常州在石墨烯產業發展具有先驅性和先導性,在產業探索上走得很遠。然而,不可復制的石墨烯產品還不多,產業缺少核心競爭力。這不僅是常州面臨的難題,更是擺在中國制造業面前的難題——我們的核心產業均被國外公司壟斷。另一方面,石墨烯產業鏈缺少精細的技術分工,“高大全”的小作坊難與國外大巨頭競爭。
高科技產業若想可持續發展,需要長期的投入。時間越長,成功的概率越高。他建議,構建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產業鏈生態。同時,在組織機制、模式上進行創新,解決研發投入大、企業資金不足等共性問題。對此,劉忠范建議采用“研發代工”模式來解決上述問題。“研發代工”模式的產學研協同創新采用從基礎研發到產業化落地的全過程捆綁制,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負責市場導向的技術研發,用企業的錢做企業的事,合作伙伴企業負責產業化落地,雙方按約定的比例分享成果轉化帶來的市場利益。
最后,石墨烯產業發展不僅要體現國家意志,也要以市場為牽引,石墨烯不僅要有邏輯性應用,也要多嘗試非邏輯性應用。也就是說,石墨烯用得出其不意。“舉例來說,常州瑞豐特科技公司研發的石墨烯光柵讓人眼前一亮,這有可能是未來卡脖子的技術。我們應該多探索這樣的應用。”劉忠范說。
在通往石墨烯小鎮的路上,新栽種的樟樹在春風中抖落老葉,就如石墨烯產業中星星點點的企業,生死往復,卻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