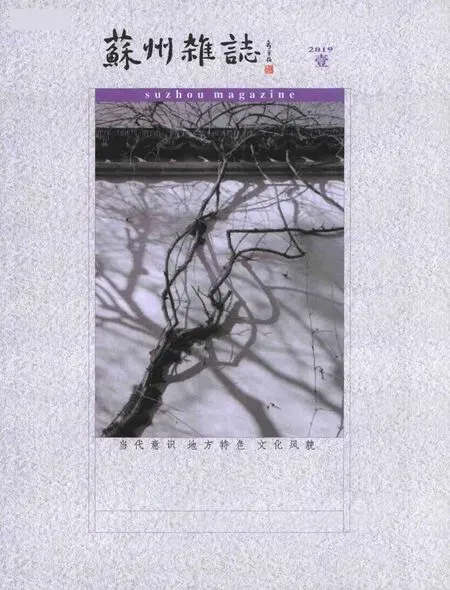話說大運(yùn)河

蘇州寶帶橋
常相伴
荊歌
我這個(gè)自小至今都生活在運(yùn)河邊的人,對于運(yùn)河,卻一直都并沒有產(chǎn)生審美疲勞。
上初中的時(shí)候,夏天我們幾乎天天都泡在運(yùn)河清澈的水里。有大船駛過,我們就會游過去,拉住船舷掛著的大輪胎,讓船拉著我們走。我們的身體,被船拉得幾乎要飛起來,在水里飛,要飛離水面,飛到空中。經(jīng)常有人因?yàn)榇倏炝耍澴佣嫉袅讼聛怼K悦看稳ミ\(yùn)河里游泳,我都會選一條有褲帶的田徑褲,把褲頭牢牢系緊。
船兒把我們帶得很遠(yuǎn),然后,我們又抓住一艘往回開的船,讓它把我們帶回家。
當(dāng)了中學(xué)教師之后,有一年暑假,我和一位同事騎自行車,從震澤一直騎到蘇州城區(qū)。這段公路,似乎始終貼著運(yùn)河。我們騎行在陸地上,眼睛里看到的,卻大多是水上的風(fēng)景。有很長很長的船隊(duì)出現(xiàn),我們就向它們揮手致意。船上的人,于是高聲喊著什么,還有人唱了起來,唱的好像是京劇吧。我們試著回敬他們,也拉開嗓子唱起來。同事是音樂教師,他學(xué)美聲的,他的嗓子從來都不需要話筒。他唱起了《桑塔洛琪亞》。他的歌聲真是響亮啊,輪隊(duì)上的人聽到了,他們一定自慚形穢,不再唱了。等我們唱完,他們熱烈地鼓起掌來。
我們騎到寶帶橋,有點(diǎn)騎不動了,同事說,他的腿抽筋了。于是我們停車,在古樸的寶帶橋上坐了下來。一坐下來,似乎就更累了,于是就躺下了。仰面躺在寶帶橋上,橋縫里的青草,除了清香,竟還有花的香味。我們看著云,看它們在藍(lán)天上飄,它們在微風(fēng)的推動下,輕輕地移動。這給了我們這樣的錯覺:仿佛我們是躺在一艘船上,這船在緩緩行駛,行駛在古老的運(yùn)河上,它從何處而來,又將向何處駛?cè)ィ坎蝗菸覀兌嘞耄覀兙投妓恕T趯殠蛏虾莺莸厮艘挥X,我們最后是被曬醒的。
后來,我長年居住在吳江縣城,雖然通往蘇州市區(qū)有高架更為便捷,但是更多時(shí)候,我還是愿意沿著國道524走。這條公路,從松陵到蘇州南門,幾乎是貼著運(yùn)河走的。開車走在這條路上,撲面而來的,是運(yùn)河的柔美風(fēng)景,一江滿滿的水,有時(shí)候滿到似乎要漾上公路,而那些河里的大小船只,都好像浮到了空中,好像是和我們的汽車在同一個(gè)高度上的。
打開車窗,風(fēng)是濕潤的,是帶著水的清涼的。
我們生活在運(yùn)河邊,我們隨處都會與它相見。無論是走在蘇嘉杭高速公路上,還是沿G50走,不經(jīng)意就會駛上一座橋,然后看到橋下常流常新的流水,是運(yùn)河的水啊!
曾經(jīng),一個(gè)在航運(yùn)公司當(dāng)領(lǐng)導(dǎo)的朋友,想安排我在運(yùn)輸船上住一個(gè)月,從松陵出發(fā),一路北上,他把這個(gè)計(jì)劃,稱為“荊歌大運(yùn)河采風(fēng)”,他說,你住在船上,天天就在船上,天天都在運(yùn)河上,船就是你的家,運(yùn)河就是你的家。
是的,沒錯,要是當(dāng)初我聽從了他的安排,那將是一次多么有意義的經(jīng)歷啊。天天都在運(yùn)河上,運(yùn)河就是我的家,只是,我的家竟是那么長么?
夜航船
朱文穎
我一直認(rèn)為,對于這條“大運(yùn)河”最真摯和隱秘的情感,我已經(jīng)把它全部寫進(jìn)了我的一個(gè)長篇小說的開篇部分——
“我的外公出生在京杭大運(yùn)河蘇杭段的一艘木船上。在中國最美麗最富裕地區(qū)的一個(gè)大霧之夜,外公哭叫著來到了這個(gè)漆黑一片、景色不明的世界上。多年以后,我乘坐夜航船穿越這一段并不漫長的航程。當(dāng)熟悉的城市景致已經(jīng)被清理歸類變得毫無個(gè)性以后,我發(fā)現(xiàn),夜航船上的午夜仍然漆黑一片。運(yùn)河兩岸的田野、村莊、散落在田野和村莊中間的草叢樹木,即便在安靜遲緩的月光下面,它們?nèi)匀伙@得面目不清、景色不明。仿佛正有一種難以辨明的危險(xiǎn)和憂傷藏匿其中……”
我知道,關(guān)于這條河,同樣可以用極其客觀和理性的語調(diào)來闡述它——
大運(yùn)河蘇州段水道最早開挖于春秋時(shí)期,是江南運(yùn)河的雛形……大運(yùn)河蘇州段通過山塘河、上塘河、胥江、環(huán)城河以及盤門、閶門等水門與蘇州內(nèi)城水系連為一體……以及,2014年6月,中國大運(yùn)河申遺成功。蘇州成為運(yùn)河沿線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遺的城市……等等,等等。

京杭大運(yùn)河蘇州段
然而,關(guān)于大運(yùn)河,無論我站在山塘河邊、上塘河沿、甚至吳江運(yùn)河古纖道旁,最觸動我情感、最讓我感受真切的部分,卻永遠(yuǎn)是這樣一幅場景、同樣的一幅場景:
遠(yuǎn)遠(yuǎn)地一艘夜船開過來,船的速度很慢,就像一個(gè)懶人在大運(yùn)河當(dāng)中散步。天上有彎月,甚至滿月,在這么慢的船上,自然是想賞月的,但那是一個(gè)霧夜,周圍都是煙水的氣息,月亮是一點(diǎn)也看不見。雖然看不見月亮未免遺憾,但在煙水的氣息中緩慢地航行,也是不錯的。不知什么時(shí)候,霧忽然散開了,在霧的空缺處,靜靜地懸著一輪圓月,運(yùn)河兩岸的田野、村莊,田野和村莊中間的樹,漸漸地也隱約可見了。我長久地佇立在船尾,仰著頭,看這月下的江南緩緩地從身后退去,那感覺是妙不可言的,而心中分明又有著說不出的憂傷……
就是這樣,于我,這條運(yùn)河是有故事和情感的;并且,它的畫面是恒定的:河水流淌,遠(yuǎn)處有亮著夜燈的夜航船緩緩駛過。
就像一位評論家對于這篇小說的評述——“我想特別指出大運(yùn)河是小說中的一條血脈。”是的,在這個(gè)城市里面,我們經(jīng)常被河、水、或者雨包圍著。這是一個(gè)與水有關(guān)的城市。河的很遠(yuǎn)處則是水面開闊、潛流湍急的京杭大運(yùn)河的一段。但是就這樣看起來,那條大河單調(diào)沉悶地獨(dú)自流淌著,完全看不到與這城市里任何暗流相匯合的可能。
然而,“如果沒有運(yùn)河,這部小說和小說中的人物就沒有夢想。城市把一切敞開了,內(nèi)心的秘密沉潛在水之下。”
沉潛在大運(yùn)河河水之下的,當(dāng)然不僅僅是小說人物的內(nèi)心秘密,還有,更多的,則是歷史的泥沙、城市的倒影,以及被夜航船點(diǎn)亮的整個(gè)南方的寓言與夢想。
運(yùn)河老家
燕華君
關(guān)于運(yùn)河記憶,都與年紀(jì)有關(guān),說出來蠻驚詫。
與小姐妹沿運(yùn)河騎腳踏車去吳江震澤,聽說那里的寶塔半夜會唱歌。駁岸古老,我們下車摸一下,果然清涼,據(jù)說它是宋代遺物。
東說葫蘆西說瓢。
在運(yùn)河里坐船,去杭州,這兩樁風(fēng)雅的事連一起,被稱作蘇杭夜班輪船。甲板被河水拖得蠻干凈,木頭紋路清晰如昨天。一個(gè)男人上船摸出一把笛子就吹,漸漸,他眼睛里汪起一攤水。
說過葫蘆再說瓢。
趴在獅山橋上看運(yùn)河上南來北往的船只,是黃昏里最大的喜悅。駁船吃水很深,從遠(yuǎn)處看,人、狗、雞、面盆均像水上漂,他們玩的是輕功嗎?船上人家的日常無非淘米,擇菜,做飯、和我們一樣。碰巧看到“射陽xxx”船,一定會貼耳細(xì)聽他們的土話,那才有趣。
所以關(guān)于運(yùn)河的記憶,連起來是我的成長史,打碎了則是震澤寶塔梵音,夜航船上的兩支光燈泡,這塊那塊的射陽駁船……唉,道路且阻長,折梅寄江北。有了運(yùn)河,我們仿佛依舊生活在詩意盎然的唐朝或古意森森的宋代;隔河相望,我們與高貴的靈魂隔河相望。
早晨,喝小米粥,搭配正宗甪直蘿卜,透明,清新,醬黑色里有故事。空穴來風(fēng)地想,隋煬帝某天也許和我一樣吃粥搭蘿卜干,突然想到煙花三月下?lián)P州,從北京到揚(yáng)州飛流直下三千尺,于是動了開鑿京杭大運(yùn)河的念頭。平常人這么想是搞事情,皇帝這么想就成了偉大壯舉,共長天一色與日月同暉。
我假裝在寫運(yùn)河,但一如既往,我寫的是時(shí)間流走,宿命里的時(shí)間漫流。史記一,開挖大運(yùn)河第一鍬的人是春秋時(shí)吳王夫差;史記二,當(dāng)時(shí)的勞動場面“舉鍤如云”,聲勢浩大;史記三,大運(yùn)河開掘于春秋時(shí)期,完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
眾口鑠金,大運(yùn)河,它既不泛濫也不渾濁,更無意當(dāng)?shù)铮鲎约壕秃茫f。福樓拜說,人們通過裂縫發(fā)現(xiàn)深淵。是的,一切都已昭然若揭,通過運(yùn)河我們看見躲藏著的自己,一道耀眼白月光。
拙政園荷花一天比一天艷麗,碗荷、缸荷、塘荷競相開放。遠(yuǎn)香堂、香洲、荷風(fēng)四面這些經(jīng)典處的經(jīng)典;還有,你以為大閘蟹、白蝦、雞頭米這些東西長在運(yùn)河里嗎?軟綿水系里的江南才會彼此相通。茉莉那么開,蘇州這么好,我們的運(yùn)河老家。
若干年后,看過瓊花的隋煬帝更老了,聽聞京杭大運(yùn)河已是世界歷史文化遺產(chǎn),心有所動,慢慢睡迷糊過去。皇帝一念之想,讓南北兩座城市相聯(lián)接,融會貫通,水系發(fā)達(dá)。其他不表,身在蘇州的我們,與大運(yùn)河朝夕相處,唇齒相依,憑空里感到朗朗乾坤,元?dú)鉂M滿。
2500多年中國漕運(yùn)史上最重要通道的大運(yùn)河,每天依然繁忙,船只日行千里不是神話。繁忙中的古老,古老里的傳說,傳說中的青春,青春里的羞澀……沒有你在,讓我如何承受這個(gè)世界的不完美?…——突然看到這么一句,算是我獻(xiàn)給大運(yùn)河的默默情歌吧。
長河日夜流
潘敏
黃昏旖旎的光影里,大運(yùn)河水顯得有點(diǎn)厚實(shí)。湊近了看,河水是灰綠色的,也算得上清澈。船過時(shí),水波蕩開,長時(shí)間看著河面,令人有恍惚感。
這是京杭大運(yùn)河從楓橋流向橫塘的一段。河里,大船一只接一只突突地開來開去。吃水淺的船,船身高高在上,船速快,顯然是一只空船。那些裝滿貨物的船,據(jù)說大多是黃沙、水泥、石子,船體半沉在水中,顯得低矮,有的看上去甚至像要沉沒了。幾乎所有的船身上都掛著黑色的汽車輪胎,那是用來防止碰撞的。天還沒黑,看不到船上有燈光,也看不到人,好像都是無人駕駛的船在來來往往。
也就一眨眼,明亮的天空轉(zhuǎn)為喑啞的灰藍(lán),河岸上的燈,一齊亮了起來。除了河面上燈火的浮光,河水的顏色比天空深多了。烏沉沉中,深不見底的河里仿佛埋藏著無數(shù)的秘密。許多年前,我住在礱糠橋的河邊,知道小河水往西通向大運(yùn)河。我曾想過什么時(shí)候能坐上船沿大運(yùn)河去滸墅關(guān)就好了,我的大舅舅在蠶種場工作,聽說那里有好多的桑樹,有桑樹就會有桑葚。小孩子的心里,吃是多么重要的事。再說,幾十年前,吃對大人來說也是重要的事。但我始終沒有坐上在大運(yùn)河里航行的船,直到今年七月的一天。
坐船的那天我正感冒,頭昏沉沉從滸墅關(guān)文昌閣邊的運(yùn)河上船,一路往南:白洋灣、楓橋、上塘河……我琢磨,礱糠橋下的水是從白洋灣還是楓橋流過來的呢?算算距離,應(yīng)該是白洋灣。可知道了又有什么意義呢?我的大舅舅早已不在人世,大運(yùn)河邊也不栽種桑樹了。

蘇州大運(yùn)河盤門段
在船上看河,感覺比在岸上看要寬得多,河邊有白色的鳥和灰色的鳥貼水飛行或者停留片刻,不知道是不是鷺鳥。船過獅山橋,看見了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十年前,我搬到了運(yùn)河邊居住,穿過那條名叫運(yùn)河路的路,三分鐘,我便可以站在大運(yùn)河的水邊。這些年來與大運(yùn)河越挨越近,但一點(diǎn)也說不上了解。比如,那些灰黑的大船全是鐵船,沒有一只是我以為的木船。還有那些黑色的汽車輪胎,從前我怎么一直以為是救生圈呢,讓人笑話。不過,這些都只是皮毛,上下千年,大運(yùn)河的秘密多之又多,誰能都知曉啊。知道一點(diǎn)是一點(diǎn)吧,鬧笑話也無妨。
再往南,看到了橫塘驛站,還在老地方,邊上的彩云橋是從別處移來的。古驛站與老橋,兩兩相對,看上去倒也相配。凌波不過橫塘路。坐船的這一天,恰好有風(fēng)有雨,風(fēng)時(shí)而斜,雨點(diǎn)子很大,是臺風(fēng)帶來的。我們坐著船快速地越過橫塘繼續(xù)往南,一點(diǎn)不妨礙我們在古人的詞里沉醉。
始于春秋的大運(yùn)河蘇州段,河兩岸的景、物、人,川流不息地變換著。難得大運(yùn)河的水,和從前一樣,它在無風(fēng)的日子平靜地流逝,在狂風(fēng)暴雨天里波瀾起伏。如同人的內(nèi)心,今人與古人是相似的:水一樣柔軟,水一樣堅(jiān)硬。
山塘故道
朱紅梅
一座新民橋像個(gè)逗號,將東西兩邊的山塘街?jǐn)嚅_了,斷出了兩種不同的語境:往東向通貴橋,一百八十米的山塘街試驗(yàn)段中規(guī)中矩地展示著老蘇州曾經(jīng)的“盛世繁華”,而西去則是市井,自東向西在橋下走過,頗有點(diǎn)從“天堂畫卷”一腳踏回人間的穿越感。
今日目光所及的山塘,早已不是當(dāng)年蘇州刺史白居易鑿河筑路時(shí)候的景象,山塘河也不再承擔(dān)水利與交通樞紐的功能。2014年6月,大運(yùn)河申遺成功。山塘河作為運(yùn)河故道,山塘歷史文化街區(qū)作為遺產(chǎn)點(diǎn)段,一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山塘街與山塘河,從吃苦耐勞的勞動人民,轉(zhuǎn)型成為旅游文化大使。
大概三四年前,如果你站在新民橋上,向左看過去,一眼就能看見水閣外壁上那個(gè)醒目的警示牌:慢行!這是沈松濤老人家的水閣。這個(gè)水閣是沈老伯的岳父年輕時(shí)建的,民國建筑,距今百來年了。據(jù)說是山塘街上保存時(shí)間最長,也是最大最完整的一只水閣。
當(dāng)時(shí),為了收集寫作素材,我曾專程探訪了沈老伯。將近立冬節(jié)氣,我和沈老伯坐在靠窗的飯桌兩邊。地板翕開了縫,我聽到腳下流水的聲音,寒意一絲絲穿透地板裹將上來。環(huán)顧室內(nèi),水閣長約四米,寬不足一米,是沈家的廚房兼客堂。坐在吃飯的方桌前,可以看到外面山塘河上的船只往來。
我一邊看著窗外的船只往來,一邊聽沈老伯講述水閣的故事。
游船撞擊水閣的事故曾不止一次地發(fā)生:2012年的冬天,支撐水閣的兩根木樁被游船撞斷;過了一年,木樁再度遭游船撞擊……水閣年代久了,經(jīng)不住折騰,這成了老人的一塊心病。也就在這一年,為了配合大運(yùn)河蘇州段申遺,山塘歷史街區(qū)環(huán)境綜合整治工程啟動。沈老伯家水閣的修繕事宜,終于得到了有關(guān)方面的重視。3月初,山塘河風(fēng)貌整治一開始,施工隊(duì)就上門來了,不僅對水閣進(jìn)行了加固,還將其修葺粉刷一番,讓老水閣恢復(fù)了精氣神。
這幾年,偶爾也會想起沈老伯和他的老水閣。前些天從朋友口中得知,沈老伯和他的老水閣依然安在,我倒是放心了。他們只是山塘街千余年歷史中的小人物和小細(xì)節(jié),然而正是這樣瑣碎日常的生活,構(gòu)成了姑蘇繁華圖細(xì)碎而綿密的針腳。對于舊器物的修繕與保護(hù),更多時(shí)候是在“保持生活的延續(xù)性”,也是將讓這座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精神與理念繼承下來。千余年來,山塘河就是這么不舍晝夜地流淌著,看似老樣子,其實(shí)每一刻又都是嶄新的。
橋堍望水來
聶夢瑤
記憶像極了抽象的照片,在不經(jīng)意到壓根沒有意識到“咔嚓”聲響的一瞬間,它便留下了抹不去的映象。而且不會讓你即刻發(fā)現(xiàn),往往要在光陰的顯影水中充分浸泡,它才會透過粼粼的紅光水影讓你隱隱看上一眼。在童年和少年的記憶映象里,我似乎常常糾結(jié)于大運(yùn)河與護(hù)城河的模糊邊界。
無論愿不愿意,蘇州人都要和水打一場幾十年的游擊,任憑你如何搬來搬去,總能在身邊找到一條河。每去到一個(gè)地方,看到某一段河水、某一座橋,時(shí)間長了,蘇州的河道就以這樣一個(gè)個(gè)碎片化的映象在我自己的地圖上標(biāo)志出來。其實(shí)我的方位感不算太差,但仍然經(jīng)常會把這些片段在拼圖時(shí)拼錯,不過我倒也沒覺得這樣不好,在自己繪制的地圖里,探索地塊連接整合的奧秘,朦朧中發(fā)現(xiàn)錯缺,接著再恍然大悟,也是相當(dāng)有趣。
我在護(hù)城河的南面住了二十多年,除了念大學(xué)的那幾年,幾乎每天都要橫渡護(hù)城河兩次,早上向北,傍晚往南。開始是人民橋,后來到南園橋和覓渡橋,現(xiàn)在由于修建地鐵封路改道,便又回到了人民橋。讀小學(xué)的時(shí)候,班里同學(xué)從住在鄉(xiāng)下的爺爺奶奶家?guī)Щ貛资畻l蠶寶寶,分給大家。我興奮地領(lǐng)了五六條小蠶,裝在用紙折成的小盒子里,一路托在手里帶回家,神神秘秘獻(xiàn)寶似地拿給大人們看。養(yǎng)蠶自然是好事,可是要到哪兒去幫我弄桑葉呢?外公想了半天,說有個(gè)地方有桑樹,但摘不摘得了要去看了才知道。為了跟著去摘桑葉,那一天我作業(yè)做得飛快。九十年代人民橋兩側(cè)的人行道上還沒有廊橋,南堍東邊,野草野樹長得桀驁不馴,這其中竟有一棵桑樹,站在橋上稍稍探出去一些就可以摘到桑葉。從此我小心翼翼地把這棵桑樹像秘密一樣種在心里,從不對人言說,直到幾年之后我又一次得到幾條蠶寶寶,去尋便再也尋不著了。
人民橋的北堍似乎總揚(yáng)著沙塵,像是透著夢境一般。我的確是夢到過北堍的樣子,或許我的北堍就是由不真切的記憶和不真切的夢幻共同構(gòu)筑而成,但它之于我卻是最真的真實(shí)。九十年代初,那兒還是兩輛公交車的終點(diǎn)站,一到發(fā)車的時(shí)刻,汽車便慢慢鉆進(jìn)橋底的涵洞,不一會兒又從對面鉆出來。在那個(gè)對什么都充滿好奇的年紀(jì),我時(shí)常會跑去河邊,聞著河水中夾帶的沙土氣息,爬在欄桿上看那寬闊泛著光亮的河面,還有高船矮船,和對岸黑壓壓一片低矮的房屋。記憶中小時(shí)候看到的風(fēng)景總是比實(shí)際要宏大得多,因此我渺小的視野無法向更遠(yuǎn)的河面延伸,以至于沒有發(fā)現(xiàn)西邊還有兩座不一般的石橋,從而少了許許多多孩童的遐想。
說把大運(yùn)河與護(hù)城河“混淆”,是因?yàn)檫\(yùn)河公園旁那條大河的緣故。光是運(yùn)河公園,學(xué)校組織的春游秋游,加上自行前往游玩,去了不下七八次,那條大河上來來往往的輪船早就駛?cè)胛业挠洃浝锪恕N抑来筮\(yùn)河,也知道護(hù)城河,我看到過運(yùn)河公園旁的大河里連成一串的輪船,也看過人民橋下的大河里駛過輪船,所以它們是同一條河。“混淆”就是這樣開始的。我住在大運(yùn)河旁邊,這河水能流到北京,流到杭州,對此我曾甚是驕傲。可后來,環(huán)古城游的旅游項(xiàng)目讓我意識到,家門口的那條河名叫護(hù)城河,好一番失落。
直到最近翻閱資料才知道,我的記憶沒有出錯,我小小的驕傲也還可以繼續(xù)保留。九十年代初,大運(yùn)河雖然已經(jīng)開辟新航道,不由胥江入古城,而是南下東折改走澹臺湖,但尚處過渡時(shí)期。所以我的運(yùn)河依然還是運(yùn)河。其實(shí)蘇州水脈交錯,運(yùn)河之水流到哪里都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