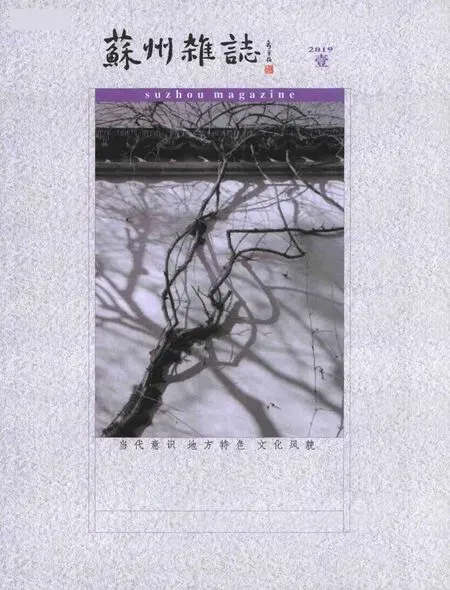一個人的出走
奔跑

顧炎武故居
一
“近臘月下,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仆靜默,多思曩者,攜手賦詩……”
1682年臘月二十八,山西曲沃縣韓村的一座安靜的宅院里,墨已經磨好。70歲的顧炎武先生來到案前,沉吟片刻,揮毫書寫了一幅流傳至今的立軸,內容是唐代詩人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中的一段。
句子戛然而止,情景歷歷在目,帶著淡淡的感傷。老先生抄寫王維的文字,是在懷念哪位朋友呢?
沒有預兆,十天后,正月初八,顧老先生前往參加朋友聚會,上馬時失足,摔倒在地,一時舊病并發,不幸于次日去世。
至此,顧炎武離開昆山千燈鎮故里已經整整25年,其間從未回去過。關山萬里,留給我們一個意味深長的背影。
二
“千燈的人不會太多”,在嘈雜的上海,我收到江南文旅作家應志剛先生這樣的回復,我的千燈之旅終于成行。而讀到王維的這段話時,我已經下榻在古鎮河邊的一家民宿里。我的所在,地理上距顧氏老宅不過百步之遙。時間上,距離那個曲沃小除夕卻已是300余年了。

王維的這封信約寫于唐開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那時,王維隱居在陜西藍田的輞川別業。一封閑信,經歷一個人的抄寫,在一個閑人的追蹤下,不覺間完成了一次跨越1300多年的傳遞。多么奇妙地穿越!
客棧老板、青年雕塑家天佑先生以他上好的紅茶招待我。天佑來自上海,像很多藝術家一樣,腦后扎著小辮。他與夫人一道,打理著一個主營城市園林雕塑的公司。
現在的生意不好做,他說,如何安頓自己,很困惑。他是否與我一樣,年紀尚未老,在努力打拼的間歇卻常不自禁地考慮退休后該怎樣生活。
天佑的眼光很獨到,他認為顧炎武是這里的一張名片。這些年來,江南水鎮的開發潮對顧炎武似乎是一個不經意忽略,以至于在這古鎮水邊連一個像樣的旅館也難以找到,直到天佑的到來。
他的項目得到古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個包括住宿、茶道、工作室和畫廊的復合型文化空間已經初具規模。
在江南俊杰中,顧炎武最不應被忽略。尤其是他45歲時離家出走、遠游華北的漂泊歲月,頗具特立獨行的意義。
顧氏為江東望族。顧炎武于1613年7月15日誕生于千燈鎮,在這里度過優渥的讀書生活。他屢試不中,27歲時斷然放棄科舉,轉而遍覽群書,輯錄研究有關農田、水利、礦產等記載。
清兵入關后,顧炎武被南明朝廷授兵部司務,但尚未赴任,南京即為清兵攻占,遂與好友歸莊、吳其沆投筆從戎。吳其沆戰死,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斷右臂,兩個弟弟被殺,嗣母王氏絕食殉國。國難當頭,家難并起。因家族財產紛爭,1657年,顧炎武被迫變賣家產,揖別故鄉,掉頭向北。
在長達25年的游歷生活中,顧炎武游歷考察了河南、河北、山東、京師、山西、陜西等地,自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而且著述等身,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漂泊江湖的士人多了,但像顧炎武這樣的恐怕絕無僅有。人屆中老年時期,他一不做官,二不依附權門,三不接受饋贈,而是自食其力,堅持獨立的學術活動。即使是現代來看,這都值得驚嘆!
三
榮格說,“人是一個事件,它是無法自性判斷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壞,得由他人來作出這種判斷。”
而對顧炎武這個“事件”做點“判斷”,很困難,也很有趣。
多年來,他在世人眼里是一個“遺民”、一個處心積慮“反清復明”的“愛國者”,而我首先關注的,則是他在游歷中的經商。
一個讀書人如何實現財務獨立,才是他首先要面對的最大人生挑戰。
與我在古鎮石板路上想象的不一樣,顧炎武沒有做貿易。在江南仇家逼迫期間,他“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販賣過布匹和藥材。北游期間,他將家產變賣的部分資金用來放貸,這恐怕是他最便于操作的理財方式了。也因此他進入了農墾領域,并成為他最重要的經營事業。
在山東章丘,顧炎武放貸給田主謝長吉,謝因故無力償還,顧炎武最終獲得了其抵押品,十頃莊田。這里成為顧炎武北游后的第一個墾殖基地。此事大約發生在1665年,顧炎武時年53歲。
此處田產為他帶來一筆穩定的收入。由于顧炎武四處出游,他采取了“委托管理”的方式。他曾給受托人的信說到:“……此莊向日租銀每年一百六十兩,若安排莊頭辦課之外,尚可寬然有余,此為久策。”
他的農墾與其遺民、學術活動交織在一起。1666年,他與山西學者傅山等二十余人集資,于雁門關北墾殖。他親自策劃,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并從南方聘來能工巧匠,引進水車、水磨等生產工具,教會農民開展水利灌溉。在給弟子潘耒的信中,他說:“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畜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澤中有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這個墾殖項目的經營績效據說“累之千金”,頗為成功。
1679年遷居陜西華陰后,顧炎武購置了田產。清代學者全祖望記述:“先生置五十畝田于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按全氏的解讀,顧炎武將章丘、雁門墾殖收入作為其學術、遺民活動的專項基金,將華陰田產收入供日常生活所需。不難看出,此時的顧炎武同時經營了章丘、雁北、華陰3個大小不一的墾殖項目。
這些項目支撐了顧炎武較為龐大的生活與學術開支,包括日常花銷、旅行盤費,尤其是投入較大的購書、刻書等等投入。
也可見當時資本借貸是有保障的,土地可以私有和買賣,事業經營似乎也較自由。沒有這樣的條件,顧炎武將寸步難行,更遑談萬里北游。
四
千燈之行后,我一度為顧炎武的矛盾所困惑:
他十多次拜祭明陵,窮極“刁遺”行狀,但他的摯友中不乏清政府官員,他甚至愿意為他們在工作上提供某些指導。
他多次斷然拒絕到清廷任職,甚至以死相抗,但并不反對他的外甥徐乾學等近親參加科考和擔任政府要職。
他尊經,倡導回歸“六經”,但并不為其章句所累,而是堅持了“六經皆史”的傳統,并用以指導自己行走山河、觀察歷史,在篳路藍縷中開一代實學風氣。
他復古,謳歌堯舜“三代”理想社會,所倡議的社會治理方案夾雜著宗法色彩,但他又石破天驚地重釋“周室班祿爵”內涵,認為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平等,他們之所以得到俸祿,是他們因承擔服務民眾事務而無暇耕種。他承認“人之有私,情固不能免”,主張保護私人財產,鼓勵經商,藏富于民。在一個專制政治極度腐朽的時代,他的思想與近代政治學說不謀而合,達到十七世紀中國知識者思想的巔峰。
他有家仇國恨,四處漂泊,反復“圖謀”,但他所提方案的實現途徑卻不是武裝斗爭,而是進行分權制衡的漸進改革,包括了重新調整君與臣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刑法與教化的關系,尤其在鄉村自治和庶民議政方面,給予了濃墨重彩的論述。
他的超越理性一直不被人所真正認知。他對歷史的觀察和提出的社會主張,遠遠超越“刁遺”的狹隘視野,而具有三千年的歷史縱深。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口號,超出“政府”、“國家”的范疇,上升到了社會、文化的高度。
他的腳踏實地一直難以被人所真正仿效。他依靠事業經營獲得經濟來源,保持了獨立的學術品格。他常常用兩匹騾、兩匹馬馱著書卷資料旅行,一路實地考察、訪問土著和親歷者,對已有的記錄進行核對與更正。《日知錄》、《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都是經過這樣反復考證而寫成的巨著。
也許因為他身處巨變的時代,使他本身色彩斑駁。也許其實沒有一個時代不是各種矛盾糾葛,他的觀察者往往被自己的時代焦慮所蒙蔽。
顧炎武,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就被懂得的靈魂。
五
顧園有一副對聯給我印象深刻:莫放春秋佳日過,最是風雨故人來。
古鎮一夜無夢,我因此聯,次日一早再次游覽顧園,對顧炎武與山西曲沃的緣分一度好奇,終究在此聯中感悟到個中滋味。
曲沃過潼關,距離華陰約二百余公里。從記載看,顧炎武因講學與訪友,前后五次訪問曲沃。居住時間最長的一次正是他生命的最后時光,1681年8月至1682年1月9日。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馬世情疏。”顧炎武一路向北再向西,是他的治學規劃所致,實際上無形中也為他的友人蹤跡所牽引。
1662年,顧炎武自河北游山西,在太原三晉書院結識著名理學家、曲沃人衛蒿,此后便與曲沃結下不解之緣。顧炎武有《贈衛處士蒿》詩云“與君同歲生,中年歷興亡”,可見兩人的相知并非泛泛而言。
定居華陰后,1679年來曲沃訪衛蒿,下榻在其主持的絳山書院,后因嫌城內嘈雜,搬到縣城南五里的東韓村韓宣的宜園。韓宣,字旬公,進士。在宜園,顧炎武與傅山、衛蒿、李二曲等名士暢談切磋,撰寫了大量研究講稿,并在此完成其扛鼎之作《日知錄》。
1681年2月,顧炎武再次來到曲沃訪問老友們,受到新任縣令熊僎的熱情款待,相處甚歡。熊僎,江西新淦人,進士,勤奮好學,對顧炎武非常敬仰。當年秋八月,顧炎武再次來到曲沃,熊僎相迎到縣城西三十里的侯馬驛。至曲沃后,顧炎武未料“大病,嘔泄幾危”,于是在宜園長住下來養病,與老友們的相見倒是更為方便了。
1682年正月初八,先生早起參加朋友們的聚會,上馬失足墜地,病情惡化,“竟日夜嘔泄不止,初九丑時捐館”。朋友們為他辦理了喪事,并護送靈柩歸葬昆山。至此,一代大儒終于魂歸故里。
再偉岸的靈魂,也似乎只有在柔軟的友情中才能真正回歸安寧。